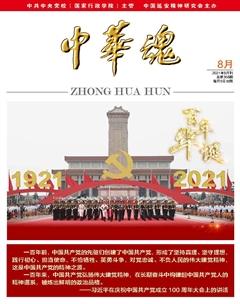調查研究與決策信息傳遞
張學兵
1960年至1961年之交,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八屆九中全會等重要場合,多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fā),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隨后,他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先后深入基層,以處境最為困難的農村為重點,展開一系列調查研究。中央黨政部門以及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黨政負責人,也紛紛深入縣、社、隊,進行重點調查。
通過大調研,全黨對農村的真實情況、農民的迫切需求,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認識不斷深化,開始以更大的決心和氣力糾正1958年公社化以來農村工作中的錯誤。認識深化和政策調整的成果,集中體現(xiàn)在《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俗稱“農業(yè)六十條”)之中,其中最為突出的政策調整有兩項,一是取消農民強烈反對的公共食堂;二是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相當于原來初級社的規(guī)模。這些調整沒有突破人民公社的政策和體制框架,但解決了農民意見最大、反映最強烈的一些緊迫問題,對遏制“平調風”“共產風”,恢復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這是當代中國史上一次較為典型和成功的大調研,它直接為決策者傳遞了豐富的農村信息,決策者以此為據(jù),作出部署,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實現(xiàn)農村政策的調整。和這次大調研大致可比的,是1955年底到1956年春的大調研,當時,為了準備中共八大的召開和迎接大規(guī)模的經(jīng)濟建設,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他們先后聽取幾十個中央和國務院部委的匯報。在調研中,毛澤東形成了一些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思想,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也因此有了一個良好開端。
不過,歷史地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調查研究與決策信息傳遞之間,并不總是像1956年、1961年那樣,呈現(xiàn)正向的良性關系。信息的獲取、承轉、分辨、反饋和處理,經(jīng)常受到諸多主觀客觀、直接間接因素的影響。
首先,調查研究要能夠全面、真實反映情況。一般而言,沒有人否定調查研究本身,不同層次和類型的調研,在不同時段、不同環(huán)境下總是有的。某些情況下,決策者對情況不摸底,固然是缺乏調查研究所致,但已有的調查研究不能反映真實情況,或許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事實上,“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之后,各地出現(xiàn)了大量的調研報告,比如《初升的太陽——北京市郊區(qū)九個人民公社調查報告》《人民公社的光芒——廣西人民公社調查》《初升的太陽——遼寧省人民公社調查選編》等,此類謳歌“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的調研,或者夸大成績、拔高經(jīng)驗,或者遮蔽問題、掩蓋矛盾,無法承擔有效的信息傳遞功能,反而可能干擾領導人的判斷和決策。人們熟知,鄧小平多次說,家庭承包經(jīng)營的“發(fā)明權”歸農民,其實,1958年到1959年間,毛澤東也不止一次地表示過,人民公社是農民“自發(fā)搞起來的”,他“無發(fā)明之權”。毛澤東或許也看到了部分事實,但呈遞給他的各級、各類信息匯集和調研報告中,有的顯然缺乏對農村情況的全面和深入反映。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中提到:調查研究實際上并不缺乏,“大躍進”時期,上至中央領導,下至縣委書記,是下基層最多的年份之一,當時很多部的部長都到基層去了,以至周恩來下令每個部必須留下一個部級干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可見,是否調研是一回事,調研能否反映真實情況,則是另一回事。1961年3月,中共中央就調查工作問題發(fā)出一封信,其中分析了最近幾年工作中出現(xiàn)缺點錯誤的原因,并明確指出:在一段時間內,根據(jù)一些不符合實際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斷和決定,這是一個主要的教訓。

其次,較為客觀的調研信息要能反映上去。“大躍進”中,一些地方糧食畝產“放衛(wèi)星”,假造超高畝產場景,這在當時,參觀、考察者也不是沒有人發(fā)現(xiàn),但在反“右傾保守”“拔白旗”的壓力下,看破又說破,并往上反映,是要冒很大風險的。薛暮橋回憶:1958年8月全國統(tǒng)計工作會議期間,有五六個省的統(tǒng)計局長來看他,說省委要統(tǒng)計局報假賬,不報就要受處分,如照省委的意圖報,又違反統(tǒng)計紀律,怎么辦?薛暮橋說:現(xiàn)在“大躍進”,勢不可擋,只能聽省委的話,將來總有一天中央會問你們真實數(shù)字,你們仍要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把實際數(shù)字拿出來。薄一波回憶:廬山會議后期,他接到通知參會,他原先準備的發(fā)言稿中列舉了“大躍進”以來“比較嚴重的缺點和錯誤”,在得知會議風向轉變后,他沒敢拿出稿子,而是按照要求表態(tài),并對彭德懷進行“過頭的”“言不由衷的”批評。薛暮橋、薄一波的回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許多老同志、老干部的回憶中,或明確、或含蓄地指出,他們對“大躍進”,當時也有疑惑,感覺到有問題,只是限于認識水平或政治壓力,不敢指出來。
面對經(jīng)濟全面緊張的局面,毛澤東和黨中央深切認識到,“現(xiàn)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為著糾正錯誤,調整政策,遂有1961年的大調研。1961年大調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規(guī)避了上述的局限。最高層領導人全部深入基層調研,避免了科層體系傳遞信息時難免出現(xiàn)的延遲和過濾,從而掌握了即時的、全面的情況。為獲得真實、可靠的信息,中央明確規(guī)定:“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jīng)作出的判斷和決定。”此外,毛澤東多次做自我批評,說“自己也曾犯了錯誤”,“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xiàn)在就做得很少了”。劉少奇在湖南寧鄉(xiāng)縣和長沙縣調研時,一開始農民不敢講真話,他懇切地說:“我是向大家求教的。這次中央辦了錯事,我們對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錯誤要了解真實情況,希望大家?guī)椭遥蛭姨峁┱鎸嵡闆r。”他不讓社隊干部陪同,直接到生產隊,多次與社員座談,社員們終于打消顧慮,紛紛反映公社化以后對公共食堂、集市貿易等問題的真實看法。可以說,在這樣的工作原則、思想方法和政治氛圍中,大調研才能直面真問題,向上反映問題時也才能較少顧忌,才更容易被接受。
進入改革年代,黨和國家的決策日益成為一個集思廣益的、有科學根據(jù)的、有制度保證的過程。決策咨詢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全,為調查研究有效服務決策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關于農村改革發(fā)展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的形成過程,就是調查研究服務決策的典范。隨著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推進,黨對調查研究與決策過程的認識也不斷深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更沒有決策權”,并倡導把調查研究“貫徹于決策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