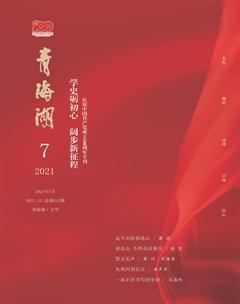第四集 《定鼎昆侖》
第四集 《定鼎昆侖》
【解說】
1949年,剛剛解放的青海,地廣人稀,交通不便,出行艱難,為了快速、有力、徹底地剿滅流竄在青海各地的股匪,第一野戰(zhàn)軍第1軍決定組建一個騎兵團(tuán)。12月19日,經(jīng)過一番緊張的挑兵選將和物資準(zhǔn)備,騎兵團(tuán)如期組建起來。1950年1月17日,騎兵團(tuán)進(jìn)駐湟中縣上五莊。
1950年1月28日,第1軍政委廖漢生來到上五莊,在興致勃勃地檢閱了騎兵團(tuán)后,他命令部隊長途跋涉,盡快進(jìn)入柴達(dá)木地區(qū),配合兄弟部隊,剿滅從新疆流竄到柴達(dá)木盆地的烏斯?jié)M、胡賽因等殘余股匪。
【同期采訪:青海地方史專家? 程起駿】
烏斯?jié)M在新疆南北部都有點勢力,他是堅決反對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他就帶著他的人跑到新疆南部發(fā)動叛亂,當(dāng)時聲勢相當(dāng)浩大,但是解放軍還是把他打垮了。打垮以后,他就帶領(lǐng)幾百人骨干,跑到了都蘭的西部,靠著昆侖山。
【解說】
早在1940年,烏斯?jié)M部便已成為新疆不可忽視的一支武裝力量。1944年底,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區(qū)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蓬勃發(fā)展,進(jìn)逼迪化,駐新疆的國民黨軍節(jié)節(jié)敗退。蔣介石出于無奈,征得馬步芳同意,調(diào)馬步芳的外甥騎兵第5軍軍長馬呈祥進(jìn)駐新疆。1949年,為追隨馬步芳出逃國外,得到陶峙岳將軍的首肯之后,馬呈祥把騎兵第5軍軍長職務(wù)交給其部下騎兵第7師師長韓有文將軍代理。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鮑爾漢、韓有文等人通電新疆和平起義,宣告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10月,第一野戰(zhàn)軍第2軍、第6軍浩浩蕩蕩進(jìn)入新疆,烏斯?jié)M內(nèi)心十分矛盾,面對復(fù)雜、多變的局勢,他一方面忌憚“三區(qū)”革命;另一方面,又對多次積極爭取他的人民解放軍抱有疑懼和不滿情緒。
1950年3月,韓有文屬下的騎兵第7師部分起義官兵叛亂,烏斯?jié)M、堯樂博斯等人認(rèn)為時機(jī)已到,遂公開反對新疆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此時的烏斯?jié)M擁有槍支千余、兵力3000人。經(jīng)過幾次交鋒,他們都敗給解放軍,烏斯?jié)M部內(nèi)部隨即出現(xiàn)了嚴(yán)重的分化現(xiàn)象,烏斯?jié)M率殘部逃往新疆南部后,為躲避駐疆解放軍部隊的追剿,便一直向南逃竄到了青海的柴達(dá)木盆地。
1951年2月初,從新疆逃至柴達(dá)木盆地的烏斯?jié)M、胡賽因等股匪,與甘、青、新交界地區(qū)的包卜拉等小股匪徒勾結(jié)在一起,負(fù)隅頑抗,茍延殘喘。解放軍西北軍區(qū)當(dāng)即組織甘青新騎兵部隊進(jìn)行聯(lián)防圍剿。
【同期采訪:青海地方史專家? 程起駿】
(烏斯?jié)M)是一個死硬派,在(新疆)和解放軍打仗,打了很長時間不愿意投降。解放軍實際在新疆就把他爭取過,他不投降。
【解說】
柴達(dá)木盆地,廣漠遼闊,地形復(fù)雜,氣候惡劣。在這里剿匪,不僅要與敵人斗智斗勇,而且要戰(zhàn)勝大自然帶來的種種困難。由于昆侖山麓高寒缺氧,戰(zhàn)馬一到這里,只是喘氣吐白沫,不要說騎,牽著它走都走不動。過察爾汗鹽湖時,戰(zhàn)馬的蹄子全被鹽漬浸爛了,指戰(zhàn)員們舍不得騎,便拉著馬走。戈壁荒漠上找不到柴草燒開水,大家就用冷水拌炒面充饑。沒有鍋灶,就在青石板上烙餅吃。硬是憑著吃苦耐勞的頑強(qiáng)和堅韌,進(jìn)入柴達(dá)木盆地的第1軍騎兵,配合2、3、4軍騎兵團(tuán)和新疆軍區(qū)的一個駱駝大隊,克服重重困難,打了幾次勝仗,于2月29日在柴達(dá)木與甘肅交界處俘獲匪首烏斯?jié)M,取得了柴達(dá)木剿匪斗爭的完全勝利。
被解放軍俘獲的烏斯?jié)M,于1951年4月29日在新疆迪化被執(zhí)行槍決,宣告了禍害新疆多年的叛匪被徹底消滅。
柴達(dá)木剿匪斗爭的勝利,穩(wěn)定了新疆、青海交界處的局勢,確保了昆侖山下各族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yè)。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莊嚴(yán)宣告成立,西寧各族人民歡欣鼓舞、聚會同慶。然而,當(dāng)時,與青海同處青藏高原的西藏,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授意下,西藏反動勢力策動西藏反動上層搞“西藏獨立”,同時加緊擴(kuò)軍備戰(zhàn),妄圖武力抗拒人民解放軍進(jìn)藏。
為粉碎中外反動派分裂中國西藏的陰謀,完成祖國大陸的統(tǒng)一,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根據(jù)解放戰(zhàn)爭的進(jìn)程,從1949年下半年開始著手解決西藏問題。毛澤東明確表示:解放西藏的問題要下決心了,進(jìn)軍西藏宜早不宜遲。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最終確定向西藏進(jìn)軍及經(jīng)營西藏的任務(wù)由西南局擔(dān)負(fù),西北局給予配合和支援,并決定于1950年4月中旬開始組織向西藏進(jìn)軍,10月之前解放全藏。
與此同時,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電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來北京商談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然而,圖謀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西藏噶廈政府,對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倡議及采取的相應(yīng)行動并未作出積極的回應(yīng),相反,卻集結(jié)藏軍8000多人分布于昌都周圍和金沙江以西地區(qū),企圖憑借金沙江天險,阻止人民解放軍入藏。
為了配合西南軍區(qū)進(jìn)軍西藏,按照西北局的部署,青海方面,一是組織部隊趕修青海通往西藏的道路,對進(jìn)藏部隊給予后勤保障;二是組織騎兵支隊南下玉樹,準(zhǔn)備參加昌都戰(zhàn)役;三是護(hù)送第十世班禪返藏。
就在趕修青藏公路的同時,第1軍抽調(diào)騎兵團(tuán)700多名干部戰(zhàn)士,組成了青海騎兵支隊,由孫鞏任支隊長,冀春光任政委。1950年6月18日,青海騎兵支隊與玉樹干部大隊及班禪行轅的10余名工作人員共計900多人從西寧出發(fā),向玉樹開進(jìn)。
歷經(jīng)一個月的艱苦行軍,隊伍來到了玉樹通天河畔。在直門達(dá)渡口,當(dāng)?shù)厝罕娪门Fご瑤退麄兌珊印?/p>
到達(dá)玉樹后,青海騎兵支隊駐扎在水草豐美的巴塘草原。他們每天堅持騎馬射擊、斬劈等技術(shù)訓(xùn)練,為向西藏進(jìn)軍做好準(zhǔn)備。
1950年10月2日,青海騎兵支隊由巴塘草原出發(fā),配合解放軍西南軍區(qū)部隊直插昌都以南,阻止藏軍南竄,出色地完成了解放昌都的戰(zhàn)斗任務(wù)。昌都的解放,打開了人民解放軍進(jìn)軍西藏的大門,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礎(chǔ)。
同年11月,青海騎兵支隊撤回玉樹。青海騎兵支隊以快速、堅決、有力的行動,為維護(hù)祖國統(tǒng)一作出了自己的貢獻(xiàn)。直到今天,這支在解放青海、西藏戰(zhàn)斗中屢建奇功的騎兵部隊依舊駐扎在玉樹的巴塘草原。他們不忘初心、繼承發(fā)揚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tǒng),和當(dāng)?shù)厝嗣袢罕娨黄穑瑘远ǖ厥刈o(hù)著三江源頭這一方美麗而神奇的土地。
從青海省省會西寧出發(fā),沿青藏公路西行約500公里有一個小鎮(zhèn),它叫“香日德”。這里是歷代班禪在青海的香火地。屬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管轄。
1949年青海解放前后,我國藏傳佛教的著名宗教領(lǐng)袖——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在這里棲身。
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出生在青海循化縣的一個牧民家庭,按照歷史定制和宗教儀軌,1944年,他被確認(rèn)為九世班禪的轉(zhuǎn)世靈童,1949年8月10日在青海塔爾寺舉行了坐床大典。隨后,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政權(quán)要他去臺灣的脅迫和控制,而轉(zhuǎn)移到了都蘭香日德寺。
【同期采訪:青海地方史專家? 程起駿】
當(dāng)時國民黨想挾持班禪去臺灣,但是班禪不愿意去,他那時還年幼,就去了香日德。那時候他還有一部分武裝力量,二三百人的衛(wèi)隊。當(dāng)時國民黨的特務(wù)、西藏的一些分裂主義者、蔣介石都在爭取他。
【解說】
西寧解放后,黨中央要求設(shè)法找到十世班禪。青海省軍政委員會通過喜饒嘉措大師與班禪堪布會議廳官員、政治代表計晉美取得了聯(lián)系。
【同期采訪:青海地方史專家? 程起駿】
當(dāng)時班禪隨員內(nèi)部有這樣幾股勢力,一部分說我們到西藏去,另一部分說去新疆,還有人說到臺灣去。當(dāng)時班禪派了兩個僧人過來視察,到甘肅這里,看看共產(chǎn)黨到底什么情況。兩個僧人進(jìn)行一番偵查后,親自來給他匯報,說共產(chǎn)黨是好人。
【解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班禪那里時,他立即指定專人起草一份電文,以班禪大師的名義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致敬:“西北已獲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氣,同聲鼓舞。今后人民之康樂可期,國家之復(fù)興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禪謹(jǐn)代表全藏人民向鈞座致崇高無上之敬意,并矢誠擁護(hù)愛戴之忱。”這封電報,是十世班禪同黨中央、毛澤東建立直接聯(lián)系的第一個正式文件。
1951年4月,正當(dāng)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與中央代表舉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時,班禪及其堪布廳的全體官員抵達(dá)北京, 5月23日,統(tǒng)稱為“十七條協(xié)議”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guān)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舉行簽字儀式。在第二天晚上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的盛大歡慶宴會上,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和阿沛·阿旺晉美相繼作了講話。
西藏和平解放協(xié)議簽訂之后,十世班禪希望結(jié)束自九世班禪以來流落祖國內(nèi)地及青海的歷史,返回駐錫地西藏日喀則。1951年12月18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xí)仲勛受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澤東委托,專程來西寧為班禪送行,青海軍區(qū)派出由騎兵組成的獨立支隊護(hù)送班禪返回西藏。
班禪一行渡過通天河、翻越昆侖山和唐古拉山,歷經(jīng)4個月的艱難跋涉,終于抵達(dá)拉薩,而后回到日喀則。此后,十世班禪大師為維護(hù)祖國統(tǒng)一,促進(jìn)民族團(tuán)結(jié)、社會穩(wěn)定和宗教和諧而奮斗了一生,成為了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負(fù)責(zé)保障十世班禪進(jìn)藏安全的慕生忠將軍,此行之中同時完成了測繪、記錄未來青藏公路線路的地質(zhì)水文氣象資料的工作,為隨后修建青藏公路這條神奇的天路打下了基礎(chǔ)。
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全國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lǐng)》明確,各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地區(qū),應(yīng)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
1951年12月25日,青海省第一個專區(qū)級的自治政權(quán)玉樹藏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五星紅旗從此在三江源頭高高飄揚。
大力培養(yǎng)和選拔少數(shù)民族干部,是推行民族區(qū)域自治、促進(jìn)青海長治久安的一項重要工作。
【同期采訪:青海地方史專家 程起駿】
當(dāng)時的話,蒙古族和藏族里面文化缺失,只有少數(shù)的活佛、阿卡(僧人)掌握一點點的文字。再個別的頭人也掌握著一點點文字。大多數(shù)人都是文盲。
【解說】
毛澤東早在1949年12月就作出過如下重要指示:“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shù)民族出身的共產(chǎn)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遵照毛澤東的指示,青海省在建政之初,就十分重視培養(yǎng)民族干部的工作,大力舉辦青年訓(xùn)練班,選拔、培訓(xùn)少數(shù)民族干部。
【同期采訪:青海地方史專家 程起駿】
縣委其中的一個工作,就是召開短期的有針對性的民族干部訓(xùn)練班。
【同期采訪:青海省達(dá)日縣政府原工作人員 更知布 86歲】
漢族同志學(xué)藏語,藏族的話學(xué)漢語,干部里面的話就這樣輪流著學(xué)習(xí)。
【同期采訪:青海地方史專家 程起駿】
選派一批優(yōu)秀的人到青海省民族公學(xué),再選派一大批人到中央民族學(xué)院進(jìn)行學(xué)習(xí)。
【同期采訪:青海省達(dá)日縣政府原工作人員 更知布 86歲】
一個縣(派遣)一個人到青海民族師范,現(xiàn)在的師大,在那里學(xué)習(xí)的時候,達(dá)日縣是我去的。
【解說】
經(jīng)過短期學(xué)習(xí)培訓(xùn),再把他們充實到各縣領(lǐng)導(dǎo)班子中去。這些同志通過實踐鍛煉,很快成為青海各項事業(yè)的中堅和骨干,其中不少同志后來擔(dān)任了青海省、州級黨政領(lǐng)導(dǎo)。截至1953年底,僅青海牧區(qū)即培養(yǎng)出了少數(shù)民族干部1796人,占牧區(qū)干部總數(shù)的30%以上。
解放初期,黨中央對青海的工作極為關(guān)懷,對加強(qiáng)民族團(tuán)結(jié)和正確執(zhí)行民族政策作過很多重要的指示。青海各級黨的組織和人民政府始終堅持從青海多民族聚居的實際出發(fā),采取慎重穩(wěn)進(jìn)的方針,努力把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內(nèi)容與青海的民族特點結(jié)合起來,開展工作。
加強(qiáng)民族統(tǒng)戰(zhàn)工作,首先要做好各少數(shù)民族中與人民政權(quán)聯(lián)系密切的上層人士的工作,發(fā)揮好這些在本民族中有較大影響的上層人士的積極作用。
昂拉鄉(xiāng),位于青海省尖扎縣東南部,距縣政府所在地9公里,人口以藏族為主,還有少量的漢族、回族等。如今的昂拉,山川秀美,民族和睦,一派歡樂祥和的景象。20世紀(jì)50年代,這里曾上演了一幕充分展現(xiàn)黨的民族政策威力的活劇,至今依然流傳不衰的昂拉千戶的往事,感動并啟迪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來人。
這座千戶府的主人,是昂拉部落的第12代頭人,名叫項謙,27歲承襲其父蘭宮太的千戶之職。昂拉千戶是清朝康熙年間獲得冊封的藏族世襲頭人,統(tǒng)治和管理著貴德、同仁一帶的大片藏族地區(qū),形成了強(qiáng)大的地方武裝勢力。
項謙繼任千戶后,面對馬家軍無休止的敲詐盤剝,于忍無可忍之中曾憤然組織部落民眾與之抗?fàn)帲R步芳三次武力攻打昂拉均告失敗。攻之不克則進(jìn)行籠絡(luò),馬步芳對他許以高官厚祿和物質(zhì)利誘。幾經(jīng)周折,馬步芳終將項謙邀至西寧,與其結(jié)為兄弟,并委他以青海省政府參議。
1949年9月初,人民解放軍從循化渡過黃河進(jìn)至化隆縣時,項謙即派人帶著禮品向解放軍致敬,表示歡迎解放。青海解放后,昂拉劃歸貴德縣管轄(屬貴德六區(qū))。黨和政府考慮到昂拉地區(qū)的民族關(guān)系和歷史傳統(tǒng),承認(rèn)了項謙的千戶職位,讓他繼續(xù)管理昂拉地區(qū)。
1949年12月至次年3月,青海連續(xù)發(fā)生了多起針對新生政權(quán)的武裝叛亂,這在項謙心里不免激起陣陣波瀾。1950年1月下旬,經(jīng)不起反動組織三番五次的煽惑利誘,項謙參加了由臺灣國民黨操控的“中國國民黨西北革命委員會”,擔(dān)任委員并兼任“反共救國軍”第2軍軍長。從此,昂拉地區(qū)的叛亂活動便此起彼伏,接連不斷。
1951年9月1日和7日,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北軍區(qū)分別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請示,主張用軍事手段解決項謙問題。9月18日,中共中央電示習(xí)仲勛和青海省委“應(yīng)該推遲進(jìn)剿時間,而加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充分準(zhǔn)備”。9月21日,習(xí)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多次電示青海省委后,又一次發(fā)電指示,要求省委、省政府領(lǐng)導(dǎo)人繼續(xù)說服項謙,同時組織藏族上層人士寫信,加強(qiáng)政治爭取工作。但青海省委、省政府仍堅持軍事進(jìn)剿的意見。習(xí)仲勛立即給青海省委領(lǐng)導(dǎo)人打電話,說:“決不能打,萬萬不可擅自興兵,只有在政治瓦解無效以后,才能考慮軍事進(jìn)剿”;同時,把青海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前后四封電報一并上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習(xí)仲勛的意見。習(xí)仲勛對項謙問題的考慮,并不是單純局限于爭取昂拉一個部落,而是著眼于廣大藏族地區(qū)的工作。作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西北軍區(qū)政委的習(xí)仲勛多次指示:對于項謙,必須“反復(fù)爭取,特別寬大”。為此,他先后委派青海統(tǒng)戰(zhàn)部長周仁山、藏傳佛教大師喜饒嘉措、藏族部落頭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與項謙接觸談判,先后多達(dá)17次。
【同期采訪:青海民族大學(xué) 教授 羋一之】
對于少數(shù)民族這個工作,就要一事一報,不能隨便處理,要經(jīng)過中央批準(zhǔn)。
【解說】
習(xí)仲勛自始至終關(guān)心和指導(dǎo)著對項謙的勸降工作,青海省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之間為此來往電報多達(dá)20來封。
終于,昂拉部落內(nèi)部也難以容忍項謙的一意孤行,其參謀長、隆務(wù)寺經(jīng)師誠勒活佛逃出昂拉,請求人民政府出兵征討。中共中央西北局請示中央,1952年4月13日,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經(jīng)十七次爭取,仍怙惡不悛,應(yīng)堅決予以殲滅。”同時指出,“軍事清剿還是為了進(jìn)一步政治爭取項謙,只要項謙懸崖勒馬與匪徒脫離關(guān)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寬大處理,保護(hù)其生命財產(chǎn)和千戶職位。”
習(xí)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于4月22日和25日兩次致電青海省委:“在進(jìn)剿中仍應(yīng)力爭項謙與其他特務(wù)土匪分化,只要項謙到時能轉(zhuǎn)守中立,就力爭他中立,這樣更有利。目前繼續(xù)積極經(jīng)過多方面進(jìn)行政治爭取,仍很必要,不可放松。”習(xí)仲勛的這些指示為爭取項謙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
1952年5月2日清晨6點半,青海軍區(qū)部隊10000余人在第1師師長羅坤山的指揮下,對昂拉地區(qū)盤踞的叛亂武裝展開圍剿。
【同期采訪:項謙兒子 昂秀 78歲】
黃河過來打得多。那邊在打,這邊也在打。我們到外面去的時候,在這邊打的,河那邊也打了。
【解說】
經(jīng)過4個小時的戰(zhàn)斗,各路匪徒基本被擊潰,慘敗后的項謙丟下家人,帶著幾十個隨從逃到了同仁縣南乎加該的森林中。習(xí)仲勛指示,抓住時機(jī),盡速派出使者再次爭取項謙。
【同期采訪:項謙兒子 昂秀 78歲】
活佛們寫的信,中央領(lǐng)導(dǎo)們寫的信。你回來,你沒什么問題。寫的信蓋了章拿去的。我家里的人派人去的。
【解說】
在黨和政府的感召下,經(jīng)多方共同努力,項謙終于于1952年7月11日帶著隨從下山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后來,項謙歷任尖扎縣縣長、黃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長,為增進(jìn)民族團(tuán)結(jié)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先前對項謙的勸降工作做了17次,加上進(jìn)剿后又1次勸降,共18次。后來,毛澤東見到習(xí)仲勛時說:“仲勛,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
【解說】
在爭取項謙的時候,青海省境內(nèi)還流竄著一支對新生人民政權(quán)危害極大的政治土匪——馬元祥股匪。
馬元祥是甘肅臨夏縣人,曾在馬步芳部任過連、營、團(tuán)、旅長,第82軍少將高參、玉樹專員,因其狡猾、殘暴、兇悍,頗受馬步芳器重。青海解放后,馬元祥假意投誠,被送至解放軍官訓(xùn)練班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結(jié)束遣返回鄉(xiāng)不久,他便利用與上層人物和部落頭人之間的舊有關(guān)系,潛藏在青海東南部地區(qū),四處搜羅收攏反革命分子和敵偽軍官,組織反革命武裝。
馬元祥股匪初期僅有25人,到1953年2月發(fā)展到170多人。他們以河南蒙旗李恰如山為基地,直接接受臺灣指示,不斷向青海省農(nóng)業(yè)區(qū)派遣特務(wù),進(jìn)行反革命串聯(lián),妄圖再次掀起大規(guī)模武裝暴亂,以配合臺灣反攻大陸。蔣介石對這股土匪寄予很大希望,委為“中華反共救國軍第102路”,馬元祥任司令,曾任湟中實業(yè)公司副經(jīng)理、國民黨青海省黨部委員的馬得福為副司令,臺灣國民黨先后5次為其空投電臺、槍支等物資,還空投了“西北地區(qū)聯(lián)絡(luò)專員”程毓杰、“西北情報處長”劉紹琴等特務(wù)對其進(jìn)行控制和指揮。此時,在與青海南部毗鄰的甘肅省甘南地區(qū)盤踞著馬良股匪,1100余人,自稱“中華反共救國軍第103路”,與馬元祥股匪互為策應(yīng),相互配合。
1952年12月19日,根據(jù)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關(guān)于“在加強(qiáng)民族團(tuán)結(jié),特別在做好被欺騙的部落、宗教頭人及其他準(zhǔn)備工作下,采取堅決軍事清剿的方針”的指示精神,青海省委發(fā)出了消滅馬良、馬元祥股匪的指示。
1953年5月3日,戰(zhàn)斗打響。5月16日,匪首馬元祥帶傷倉皇逃至黃河岸邊時,被截?fù)舻墓碴爲(wèi)?zhàn)士張萬福隔河一槍擊斃。此役一舉全殲馬元祥股匪,消滅了殘存于青海境內(nèi)的最后一支政治土匪。從平息反革命武裝暴亂到剿滅馬元祥股匪,一場持續(xù)三年零七個月的斗爭,至此畫上了句號。
在參與剿滅馬元祥政治股匪的過程中,有這樣一支特殊的民間隊伍也得到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嘉獎,他們就是來自果洛阿什羌本·康賽部落的武裝力量。
【同期采訪:康萬慶之孫 康扎西】
這是以前部落的一種方式。發(fā)生一些緊急戰(zhàn)爭的時候,有一個專門傳達(dá)的人,他拿著一個旗子,去說一聲,每家每戶要出兩個人或者一個人,然后集中以后再出去。當(dāng)時是和共產(chǎn)黨一起去的。
【解說】
史料記載,這次康賽部落頭人康萬慶主動帶領(lǐng)250多名騎兵,跟隨剿匪指揮部配合剿匪長達(dá)半年之久。
康萬慶,果洛地區(qū)唯一的世襲千戶,是阿什羌本·康賽部落第六代第七位頭人。1949年9月,西寧解放、新中國成立前夕,甘肅夏河和平解放。康萬慶即刻前往曾任拉卜楞保安司令、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少將,而后率部起義的黃正清處了解形勢。黃正清向他介紹了共產(chǎn)黨解放青甘川等地區(qū)的情況以及共產(chǎn)黨的政策主張。
【同期采訪:康萬慶之孫 康尕藏成利】
最初的所有的淵源是起源于黃正清,他是黃正清的妹夫,黃正清是舅哥。他倆不但是這個關(guān)系,而且黃正清也非常器重他。他們互相之間感情特別好,互相之間非常信任。
【解說】
黃正清,這位曾率領(lǐng)甘南草原牧民同反動馬家軍進(jìn)行殊死搏斗,拯救了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甘南人民的藏族領(lǐng)袖,早在1925年至1927年間就與共產(chǎn)黨人宣俠父結(jié)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在西北少數(shù)民族,特別是在藏族群眾中擁有很高的威望。
【解說】
1950年3月,時任青海省民委副主任的扎喜旺徐帶信給康萬慶和果洛各大部落頭人,向他們宣傳共產(chǎn)黨的民族統(tǒng)戰(zhàn)政策;1951年5月,青海省政協(xié)副主席扎喜旺徐以省委省政府的名義邀請康萬慶等各大部落的頭人派代表來西寧共商解放果洛事宜;同年10月,康萬慶親自到西寧同省委省政府聯(lián)系,表示歡迎共產(chǎn)黨和平解放果洛。
果洛地處青甘川交界地區(qū),山川險峻,交通閉塞。歷代封建王朝,包括國民黨和馬步芳的反動勢力都沒有真正統(tǒng)治過這個地區(qū),因此果洛在歷史上沒有正式建立過政權(quán)。
1952年2月,西北軍政委員會組建果洛工作團(tuán),扎喜旺徐任團(tuán)長,馬萬里任副團(tuán)長兼工委書記。果洛工作團(tuán)在扎喜旺徐、馬萬里的率領(lǐng)下,于7月1日向果洛進(jìn)發(fā)。
就在果洛各部頭人對新生的人民政權(quán)依然抱有戒備心理,依然持觀望態(tài)度之時,康萬慶從久治出發(fā),偕其胞弟康萬明、長子尕藏才旦和門堂寺主活佛桑杰及康賽部落大小頭人20余人趕到拉加寺迎接工作團(tuán)。
【同期采訪:康萬慶之孫 康扎西】
我爺爺和父親帶來300多個人幫助共產(chǎn)黨渡黃河,在拉加寺一帶。
【解說】
康萬慶與其周邊部落頭人大多沾親帶故,也正因為如此,他在促成這些部落與共產(chǎn)黨建立關(guān)系、擴(kuò)大我黨合作共事的范圍和基礎(chǔ)方面,作出了他人無法企及的突出貢獻(xiàn)。
【同期采訪:康萬慶之孫 康尕藏成利】
首先就是講這個共產(chǎn)黨和這個馬步芳的區(qū)別,兩黨之間的這種區(qū)別,各方面的區(qū)別,用他自己聽到的見到的這些來做工作。當(dāng)時畢竟還是一種部落制,頭人們的工作做通了,大一點部落的下面有小部落,小部落的工作做通,下面的各個家長們的工作做通,整個也就通了。
【解說】
1952年8月4日,果洛工作團(tuán)經(jīng)過一個月的艱苦跋涉,抵達(dá)果洛中心腹地查朗寺,果洛宣告和平解放。
工作團(tuán)進(jìn)駐果洛后,按照“更加慎重穩(wěn)進(jìn)”“只許做好不許做壞”“對一切有代表性人物均采取團(tuán)結(jié)爭取教育不許冷淡拋棄”的工作方針,經(jīng)請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同意,于1952年8月24日至9月1日在查朗寺附近召開了果洛區(qū)首屆頭人代表聯(lián)誼會。會上,馬萬里作了《關(guān)于加強(qiáng)民族團(tuán)結(jié)的報告》、扎喜旺徐作了《關(guān)于恢復(fù)和發(fā)展生產(chǎn)的報告》,康萬慶帶頭在會議決議——愛國公約上簽字蓋章,表示一定信守承諾,與共產(chǎn)黨真誠合作。
【同期采訪:原果洛工作團(tuán)工作人員 張斌 99歲】
一個貿(mào)易隊伍,兩個組織起來一起下鄉(xiāng)。到老百姓帳篷里,到寺院里,到處去宣傳政策,都給他們買東西,給他們看病、聯(lián)系群眾,過了一年多以后,才參加政權(quán)。
【解說】
1954年1月1日,果洛藏族自治區(qū)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正式成立了專區(qū)級的果洛藏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自此,果洛實現(xiàn)了從封建農(nóng)奴制向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跨越,歷史的豐碑從此聳立在廣袤的果洛大草原。
【字幕】
1953年9月30日,黃南藏族自治區(qū)成立;1955年5月22日,改為黃南藏族自治州。
1953年9月30日,海南藏族自治區(qū)成立;1955年6月5日,改為海南藏族自治州。
1953年12月31日,海北藏族自治區(qū)成立;1955年5月20日改為海北藏族自治州。
1954年1月1日,果洛藏族自治區(qū)成立;1955年7月2日,改為果洛藏族自治州。
1954年1月25日,海西蒙藏哈薩克族自治區(qū)成立;1985年5月21日,改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解說】
截至1954年,青海省農(nóng)業(yè)區(qū)的各級人民政府和牧業(yè)區(qū)的民族區(qū)域自治政權(quán)先后建立,在黨中央和青海省委的領(lǐng)導(dǎo)下,邊剿匪、邊建政,在社會民主改革和生產(chǎn)建設(shè)中,人民民主政權(quán)深深扎根在各族人民心中,巍然屹立在青海大地。
回顧青海解放那一段風(fēng)云激蕩、激情燃燒的歲月,緬懷為西北解放、青海平定,為維護(hù)祖國統(tǒng)一、民族團(tuán)結(jié)、人民幸福安康付出巨大犧牲、作出歷史性貢獻(xiàn)的革命先烈和各族各界干部群眾的豐功偉績,必將激勵我們更加堅定地聽黨話、跟黨走,以習(xí)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登高望遠(yuǎn)、自信開放、團(tuán)結(jié)奉獻(xiàn)、不懈奮斗的精神狀態(tài),奮力書寫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青海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