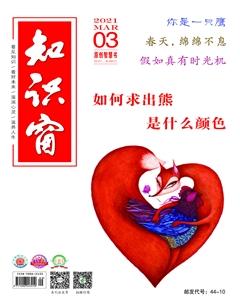人要保持對自己的憤怒
蔣方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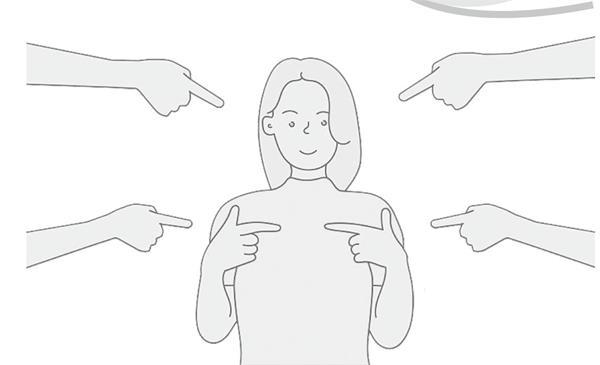
前段時間,我跟一個做媒體的朋友聊天,聊起各自面臨的境況,都很喪氣。
朋友說現(xiàn)在媒體的選題貧瘠,報道網(wǎng)紅城市、網(wǎng)紅建筑、網(wǎng)紅現(xiàn)象——一個盲盒,幾乎所有媒體都在寫。報道的人物幾乎都是網(wǎng)紅,思路也都一樣:草根,因為做好了一個點,觸發(fā)了大眾狂歡,然后呢?然后就沒有了。類似的稿子,無論是看多了,還是寫多了,都很沮喪。
我說我最近的狀態(tài)也很喪氣,因為前段時間工作比較多,漫長地化妝,在攝像機前漫長地表演知性,絞盡腦汁地回答:“你認(rèn)為閱讀寫作和美/時尚/科技/小型家用電器/高性能智能電動汽車有什么關(guān)系?”在另一些非工作的時刻,我也面臨著一些被“廣泛熱議”但毫無意義的問題,如“你是怎么治愈討好型人格的?”“你是怎么看待中產(chǎn)焦慮和年輕人的低欲望社會?”“你是救貓還是救藝術(shù)品?”
當(dāng)交換了彼此的沮喪,我和朋友發(fā)現(xiàn)了問題的根源:我們都覺得自己的工作喪失了價值感。然而就和大部分工作一樣,它并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只是當(dāng)你回顧自己傾注的時間和精力時,會忍不住感慨:“可以,但沒必要。”
當(dāng)我把自己喪失價值感的沮喪分享給另外的親密朋友,得到的反饋如一盆冷水澆下:“大部分人都無法從工作中獲得價值感,工作就是工作,你追求價值感是你的病,你要治。”而當(dāng)我再次微弱地表演自己的崩潰,朋友則憂心忡忡地說:“你看你,心態(tài)都不好了。”
的確,我的心態(tài)并不總是好的。之前,別人問我:“你有什么特別的能力?”我想了想,說:“我自我厭惡的能力特別強。”
在自我厭惡的經(jīng)驗里,我簡直是一個豌豆公主——當(dāng)感覺到自己不夠真誠了,感覺到自己不夠勇敢了,感覺到自己貪婪了,感覺到自己愚笨不靈敏了,我就會被自我厭惡長久嚙噬,輕則自閉,重則跑路。之前,我到異國生活了一年,就是覺得自己在環(huán)境中隨波逐流一路下沉,再不逃跑人就廢了。
也許人年輕的時候都是這樣,覺得自己與世界格格不入,認(rèn)為夢想是對的,生活是錯的。但隨著年歲漸長,生活嘲弄美夢,人生緩慢受錘,于是那種膈應(yīng)逐漸消退,就像是一種熱病被治愈。
我小時候曾經(jīng)采訪過一位搖滾歌手,他說自己早年對自己和他人都很憤怒,并且在憤怒下寫了很多首歌,現(xiàn)在過上了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不憤怒了。我驚訝地問:“你為什么不憤怒了?”他驚訝地反問:“我為什么要憤怒?”然后我們驚訝地重復(fù)了好幾遍上述對話,最后他找到了一個完美答案:“因為我和自己和解了。”
“和解”這個詞現(xiàn)在出現(xiàn)的頻率越來越高,我當(dāng)然相信有真正與自己和解的人——誠實地面對命運的感召,在追求永恒事業(yè)時平靜而勇敢,但大多數(shù)時候,我聽到人們說“和自己和解”時,往往說的是“我放棄了”。
我原諒,我感受到能力與目標(biāo)之間差距的時候選擇放棄;我默許,我從自己看不起的事物中花費時間且獲得快樂;我放棄,對自己和他人負(fù)責(zé)任,是因為“我太難了”而不是“我太軟弱了”。大部分時候,我們說“我和自己和解了”,是受不了自己內(nèi)心深處一遍又一遍的反問,想終結(jié)對話。
我還不想這樣。
我以前的文章里談到過樹木希林的紀(jì)錄片,在片子中,她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人要保持對自己的憤怒。”
對自己的無能、懶惰保持憤怒,這是一種能力,而不是一種疾病。就像喝酒會嘔吐,是一種帶有保護性的應(yīng)激反應(yīng),當(dāng)有一天你不會嘔吐了,不是因為你身體變好、酒量變大了,而是因為你的耐受性變強,失去了這種自我保護的機制。
嘔吐很痛苦,就像是憤怒、拷問、追尋,都很痛苦。世上總有一些人,他們對生活要求很高,對自己的愚蠢和粗野又不甘心。當(dāng)我還能感覺到痛苦,我就知道,自己還在這些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