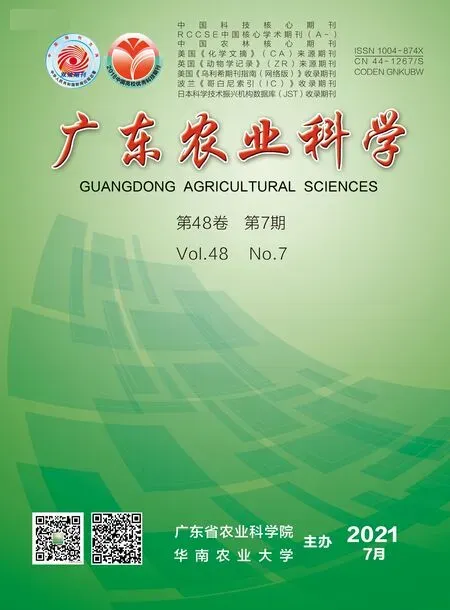廣州郊區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重金屬污染及生態風險評價
梁敏靜,熊 凡,曾經文,余偉達,張苑鈴,周樹杰
(1.廣東省廣州生態環境監測中心站,廣東 廣州 511400;2.生態環境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廣東 廣州 510655;3.廣州尚然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廣東 廣州 510030)
【研究意義】隨著生態文明建設深入推進和新發展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國家對土壤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城市郊區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污染狀況,評價其潛在生態風險程度,有利于為污染工業企業周邊土壤污染防治和風險管理提供科學依據,同時也是有效控制土壤污染、保障環境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前人研究進展】在我國,早期工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工業三廢”的不合理排放給土壤環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重金屬污染是其中一個突出的方面。采礦、制革、紡織、金屬冶煉等行業的廢料中含有高濃度的重金屬[1-3],這些重金屬污染物從土壤中滲透進入到地表水和地下水系統中。而農業生態系統的重金屬污染往往是由廢水灌溉、固體廢物處理、車輛尾氣、施肥和工業活動等引起的[4],工業活動是工廠附近地區重金屬的主要來源。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城市工業企業逐步向郊外農村轉移,給城郊土壤帶來生態危害風險,尤其是城郊農田重金屬污染問題亦日益引起重視。根據2014 年國家環境保護部和國士資源部聯合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農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點位超標率為19.4%,以Cd、Ni 和Cu 等重金屬污染最為突出[5]。重金屬污染物在農田土壤的累積,不僅影響土壤的理化性狀和養分供給,還通過食物鏈的富集,將直接或間接對人群健康造成威脅。
【本研究切入點】據調查,重金屬在印染、電鍍、采礦、醫藥、紡織、石油加工、防腐等工業生產中廣泛存在。本研究選取了廣州郊區比較典型的三類工業企業(某電鍍工業區、某印染紡織企業和某五礦稀土公司)周邊農田土壤進行布點、采樣和分析,了解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重金屬含量,采用污染負荷指數法確定土壤中重金屬的污染程度,采用潛在生態風險指數法對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程度進行評價,并分析工業企業周邊土壤重金屬累積、差異和成因。【擬解決的關鍵問題】潛在生態風險指數法在評價過程考慮了各重金屬元素的毒性,有利于從生態系統和人文的角度評價土壤潛在生態風險,為有效提高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加強廣州郊區部分工業企業周邊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和修復提供參考依據[6-8]。
1 材料與方法
1.1 樣品布點與采集
對某電鍍工業區周邊采用800 m×800 m 網格法均勻布點,沿企業廢水排放水道400 m 內加密布點,現場共布設13 個采樣點,同時在距排污口約1.7 km 處設置1 個對照點。對某印染紡織企業周邊采樣點布設主要考慮廢水排放對土壤的污染,污水排放按水流方向自納污口起400 m 內,由密漸疏布設,共布設13 個點位,在距納污口約1.6 km 處設置1 個對照點。對某稀土公司周邊采用300 m×300 m 網格法均勻布點,按廢水排放方向自納污口起1 000 m 內,由密漸疏布設,同時考慮到調查企業廢氣的影響,在主導上、下風向上,距廠界100、300、600、1 000 m 處各布設1 個采樣點,共布設13 個點位,在遠離企業納污口約1 km 的排水道上游清潔區布設1 個對照點。
對照點及采樣點各挖取0~20 cm 的表層土壤,采用梅花布點5 點取樣,各分點混勻后用四分法取1~2 kg 混合土樣裝入樣品袋為1 個樣品。
1.2 樣品制備及預處理
主要包括“風干-粗磨并分樣-細磨并分樣”3個環節。在風干室將土樣放置于風干盤中,除去土壤中混雜的磚瓦石塊、石灰結核,根莖動植物殘體等,半干狀態時,用木棍壓碎或用兩個木鏟搓碎土樣,置陰涼處自然風干。用瓷制研缽手工研磨或瑪瑙球磨機研磨后,過孔徑2.00、0.250、0.150 mm 尼龍篩,裝瓶備用。
土壤樣品組分復雜,污染組分含量低,且處于固體狀態,需要處理成液體狀態和將欲測組分轉變為適合測定方法要求的形態、濃度,消除共存組分的干擾。Cd、Cu、As、Cr、Zn 和 Ni 前處理用HCl-HNO3-HF-HClO4消解,Hg、Pb 前處理用1+1 王水消解。
1.3 分析方法
Cd、Pb采用石墨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測定,Hg 采用原子熒光光譜法測定,As 采用原子熒光光譜法測定,Cr、Cu、Zn、Ni 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測定,質量控制按照《土壤環境監測技術規范》(HJ/T 166—2004)有關技術規定的要求進行。
1.4 評價標準
為更準確反映廣州郊區地區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重金屬生態風險程度,本研究以1990年廣州市土壤背景中的重金屬含量作為參考值。土壤環境質量評價執行《國家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2018)中的農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
1.5 評價方法
1.5.1 污染負荷指數法 污染負荷指數法(PLI)用于確定土壤中重金屬的污染程度。污染因子(Cf)計算公式為Cf=Ci/Cni,其中Ci為土壤重金屬i實測濃度,Cni為重金屬i背景值。PLI=(Cf1×Cf2×Cf3×…Cfn)1/n。PLI為某點的污染負荷指數,n為參加評價的重金屬種類數。PLI分為7 個等級:背景濃度(PLI=0)、無污染(0<PLI≤1)、輕度污染(1 <PLI≤2)、中度污染2 <PLI≤3)、中到高污染(3 <PLI≤4)、高污染(4 <PLI≤5)和極高污染(PLI>5)。
1.5.2 潛在生態風險指數法 潛在生態風險指數法是評價重金屬污染及生態風險的方法,由瑞典科學家 Hakanson 提出該指數不僅反映某一特定環境中各種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及多種污染物的綜合效應,且用定量的方法劃分出潛在生態風險的程度。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RI為潛在生態風險指數,Eri為潛在生態危害單項系數,Eri為某一重金屬的毒性相應系數,Cd、Hg、As、Pb、Cr、Cu、Zn、Ni 的毒性相應系數分別為30、40、10、5、2、5、1 和5,為單項污染系數,為表層土壤重金屬含量實測值,為土壤背景參考值。重金屬污染潛在生態風險系數和潛在生態風險指數分級標準見表1。

表1 潛在生態風險系數和指數分級標準[9]Table 1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coefficient and index grading criteria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壤重金屬含量分析
通過對廣州郊區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重金屬含量進行統計分析,以探討重金屬的污染程度,并為土壤生態風險評價提供數據基礎,監測結果見表2。結果顯示,三類工業企業周邊土壤局部監測點位重金屬含量均有不同程度超過1990 年廣州郊區土壤背景值,其中Cd 在三類工業企業中超出背景值較為突出。電鍍工業超過背景值的重金屬類型居多,除Hg、Pb 外,Cd、As、Cr、Cu、Zn 和Ni 等6 類重金屬超出背景值,點位數占90%~100%。總體來看,印染紡織業、稀土工業周邊土壤重金屬含量相對較低。印染紡織業周邊土壤Cd、Cu、Zn 污染均較為明顯,稀土工業周邊土壤點位的Cd、Pb 污染較明顯。電鍍工業周邊土壤各類重金屬(Hg、Pb 除外)污染較明顯,符合電鍍企業特征污染物的特征。

表2 土壤重金屬監測結果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soil heavy metal monitoring results
綜合考慮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程度,電鍍工業和印染紡織業的PLI平均值>1,表面周邊農田土壤為輕度污染;稀土工業的PLI平均值<1,表面周邊農田土壤為無污染。PLI顯示的3 個地點的不同重金屬污染水平與不同污染源有關。電鍍工業對周邊農田重金屬含量的影響最大,印染紡織業次之。
2.2 單因子潛在生態風險評價
廣州郊區三類工業企業周邊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系數統計結果見表3,生態風險系數均值比較見圖1。由表3 和圖1 可見,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中Cd 潛在生態風險最高,風險系數均值在48.20~61.24 之間。Hg 潛在生態風險次之,風險系數均值在25.46~59.42 之間。Zn 潛在生態風險系數最小,潛在生態風險系數均值在1.13~2.73 之間。各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程度由強到弱依次為Cd >Hg >As >Cu >Ni >Pb >Cr >Zn。

圖1 土壤重金屬生態風險系數均值比較Fig.1 Comparison of mean values of ecological risk coefficients of soil heavy metals

表3 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系數統計結果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coefficients of soil heavy metals
廣州郊區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程度見圖2,結果表明,所有監測點位中,三類工業企業周邊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程度存在一定共性:各類型周邊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程度均為低風險到較重風險之間,As、Pb、Cr、Cu、Zn、Ni 風險程度均為低風險,各單因子潛在生態風險程度未出現重度及以上;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程度最高均為Cd,風險等級最高均為較重。各類型周邊土壤中較重風險點位數如下:電鍍工業為Cd 共1 個;印染紡織業為Cd 3 個、Hg 2 個,共5 個;稀土工業為Cd 共2 個。

圖2 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程度Fig.2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degree of soil heavy metals
2.3 綜合潛在生態風險評價
根據潛在生態風險指數法,統計了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綜合潛在生態風險級別,結果見表4。統計結果顯示,廣州郊區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狀況處于輕微生態風險和中等生態風險。電鍍工業中12 個為輕微生態風險,1 個為中等生態風險;印染紡織業中8 個為輕微生態風險,5 個為中等生態風險;稀土工業中11 個為輕微生態風險,2 個為中等生態風險。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綜合潛在生態風險程度依次為電鍍工業>稀土工業>印染紡織業。表明所選取廣州郊區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狀況存在一定生態風險,為抑制農田土壤向較重風險轉變,提升農田土壤環境質量,確保農田土壤環境安全,應采取相應措施和建立健全監督體系促進土壤綜合治理和修復,尤其應加強對土壤Cd 和Hg 的污染治理。

表4 綜合潛在生態風險程度Table 4 Integrate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degree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表明,電鍍工業和印染紡織業周邊農田土壤均存在輕度重金屬污染,以Cd 和Hg污染較為突出。相關研究表明,Cd 主要來自冶煉、電池、電鍍、顏料等工業排放,Hg 主要來自于汽車尾氣、燃煤降塵、建筑揚塵等,經過大氣沉降進入土壤,對周邊土壤環境造成累積。根據監測結果和現場情況分析,早期工業活動不合理排放,工業排放的氣體污染物經過大氣沉降進入土壤,對周邊土壤環境造成累積。
土壤中的重金屬污染物具有劇毒性、不可降解性和生物累積性等特點[10-11],容易隨工業排放進入到農業生態系統中,對生態系統造成不利影響[12]。雖然Zn、Cu 等重金屬是動植物身體中蛋白質和生物酶等組織的組成成分,但是其中絕大多數重金屬沒有任何有益的生理功能[13-15],在人體中的過量積累會導致許多疾病[16]。Cd 在人體內的積累可導致腎臟、骨骼和肺損傷;Pb 可損害中樞神經系統、腎臟和血液系統等[17-21]。而食物鏈是人體接觸重金屬的主要途徑。如日本20 世紀30 年代的“痛痛病”和50 年代的“水俁病”[22-26],就是典型的重金屬中毒案例。土壤中重金屬污染通過以農作物為主要環節的食物鏈進入人體后,對人類健康安全及生態系統平衡潛在危害極大,應提高預防重金屬對農田土壤污染的公眾認識和土壤治理能力[27-28]。
所選取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中,各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程度由強到弱依次為Cd >Hg>As >Cu >Ni >Pb >Cr >Zn。其中,各類型周邊土壤Cd、Hg 存在較大潛在生態風險,其他重金屬(As、Pb、Cr、Cu、Zn、Ni)為低風險。各類型周邊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程度均為低風險到較重風險之間。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綜合潛在生態風險程度依次為電鍍工業>稀土工業>印染紡織業。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狀況處于輕微生態風險和中等生態風險。表明所選取廣州郊區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狀況存在一定生態風險,應加強預防土壤污染和修復治理,防止向較重風險轉變,確保農田土壤環境安全和人類生命安全健康。
4 結論與建議
所選取廣州郊區三類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狀況均存在中等生態風險,為抑制農田土壤向較重風險轉變,提升農田土壤環境質量,確保農田土壤環境安全,應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環境監測和污染風險管控,尤其應加強對土壤Cd 和Hg 的污染治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土壤污染來源廣泛、復雜,工業“三廢”是重金屬的重要輸入來源,與農田化肥施用、機動車尾氣排放、早期生活垃圾堆積等構成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復雜系統,是造成廣州郊區工業企業周邊農田土壤重金屬污染不容忽視的源頭。可見,進一步優化能源結構、發展低碳循環經濟、強化污染源排放監測以及監督、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是從源頭減少和遏制土壤重金屬污染的重要措施。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如下建議:
(1)進一步加強從源頭控制污染仍然是重中之重,優化能源結構,大力發展低碳循環經濟,合理調整工業布局,加強“工業三廢”排放的污染監督和控制,尤其是加大力度扭轉對村鎮污染企業疏于監管的局面,依法清理整頓生產工藝落后、二次污染嚴重企業,嚴格企業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是有效控制污染物的無序排放,從源頭控制重金屬污染的根本途徑。
(2)農藥化肥的不合理施用是造成農田土壤污染的主要來源之一,需要加強先進農業生產技術研發和推廣,積極推廣無害生物綜合防治技術,防止濫用農藥化肥,加大農產品種植生產管理過程的監督檢查力度,杜絕使用劇毒、高毒農藥,減少農藥化肥對農田土壤的污染。
(3)保護土壤環境離不開公眾的共同參與,土壤污染與大氣、水污染不同,具有高度的隱蔽性,難與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應加大對公眾開展保護土壤資源,防止土壤污染的宣教力度,加強土壤污染防治科普工作,將土壤環境保護知識編入大、中、小學及成人教育環保教材,提高公眾土壤環境保護意識,加強土壤資源及土壤安全信息的公開程度,引導公民踐行低碳、綠色生活方式,讓社會全體共同參與生態環境保護。
(4)以《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等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為重要保障,加強農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力度,逐步改善土壤環境質量,保障生態環境安全。在廣州建設用地、農用地環境管理機制不斷強化的大背景下,深入推進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為有效保障廣州市土壤環境安全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加強工業企業周邊土壤環境污染的監測監控能力建設,建立健全土壤生態風險評估體系,提升城市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和治理成效,進一步為深入打好廣州“凈土”保衛戰,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求、推進廣州市生態文明建設發展提供重要技術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