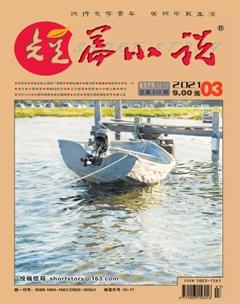當你老了
岑燮鈞
當你老了,頭白了,睡意昏沉,
爐火旁打盹,請取下這部詩歌,
慢慢讀,回想你過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們昔日濃重的陰影;
……
雖然,葉芝的本意跟我的主人公的本意并不相同,但是,誰都有一個優雅老去的夢想。我的主人公生活在城鄉接合部,她有一定的文化,丈夫曾是當地的一個學者。作為遺孀,她卻遭遇了許多尷尬,致使她的精神突圍以失敗告終。
我在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可她到底還是個女人,難道年紀大了,連女人都不是了?”也許,這句話可以稱得上是文眼。就像她生活在城鄉接合部一樣,她是學者的遺孀,但她本身不是學者;她有對體面生活的向往,但在孩子們的眼中,她只是一個接近于老媽子的媽而已;她的周邊都是念佛老太,她也曾努力想從這種氛圍中掙扎出來,可是沒有一個人幫她,甚至還把她重新推向這種生活。這就是魯迅所謂的“幾乎無事的悲劇”。于是,她只能緬懷丈夫的“拯救”,她在“舊雜志”中尋覓丈夫的身影。自然,當她一旦知道了丈夫曾經的情感外遇時,她內心的崩潰顯而易見。但是,因為她老了,她就被“設定”為不應該再“作”了。
在生活中,我們看到許多人在孤獨地老去。有的內心處于麻木的狀態,而有的依然在苦苦掙扎,想從泥淖中突圍出來。他們的痛苦,很多時候不為人知道,就是身邊的親人,也不一定能理解。我的這個故事的原型,源于朋友的傾訴。她在講述她母親的故事時,對于母親異于常人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或者說,即使有所理解,也很不耐煩。我知道,她在傾訴的時候,把自己當作了普通人,自然,她也把母親當作了普通人。我在傾聽她的故事時,我深深理解她作為女兒的無奈和煩惱,我也把自己當作了一個普通人。但是,一旦“小說作者”的靈魂附體之后,我理解的就不僅僅是朋友了,而更多的是朋友的母親。作為一個老去的母親,或者更確切一點說,作為一個老去的女人,她的所作所為一旦超越了母親的身份限定之后,她的不被理解的痛苦,她的精神掙扎和突圍,難道就沒有意義嗎?這就是我要把它寫出來的原因。
當然,小說是虛構的,故事是假設的。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但是,老年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值得深入其中的。這是一片老去的森林,枯藤老樹昏鴉,讓人避而遠之。但其實,它并不是一潭死水,也不是一口枯井。老根虬臥在地下,依然尋覓著清泉……
讓我們對老年人多一點精神的安慰吧。
責任編輯/董曉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