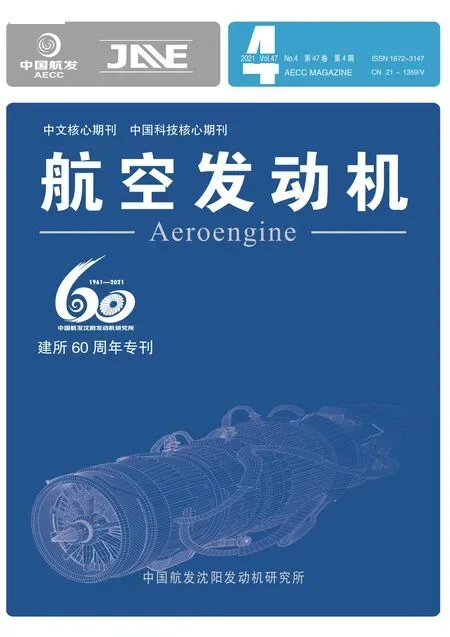基于快速預(yù)測模型的輪盤瞬態(tài)變形影響
馬曉健,黃敬杰,徐如雪,智紹強
(中國航發(fā)沈陽發(fā)動機研究所,沈陽110015)
0 引言
為了達到設(shè)計點的工作狀態(tài),航空發(fā)動機需要優(yōu)化加速或減速路徑,從而引入了瞬態(tài)性能的概念。在瞬態(tài)條件下,主流道參數(shù)急劇變化,氣體與固體之間發(fā)生劇烈熱量交換,稱為熱浸潤。例如從慢車到最大狀態(tài)的瞬態(tài)加速,發(fā)動機機體必須適應(yīng)新的穩(wěn)態(tài)工作溫度,通常會吸收30%的燃料能量[1]。熱浸潤的作用結(jié)果之一是使發(fā)動機結(jié)構(gòu)尺寸如葉尖及封嚴(yán)間隙發(fā)生瞬態(tài)變化[2],進而影響發(fā)動機性能。例如,高壓渦輪葉尖間隙增加1%會導(dǎo)致其效率降低2%,進而導(dǎo)致發(fā)動機燃油消耗率增加。此外,與穩(wěn)態(tài)相比,在瞬態(tài)加速過程中發(fā)動機工作線更容易接近喘振線,帶來了較大的喘振風(fēng)險[3-4]。轉(zhuǎn)子在離心力作用下,通常加速時更容易與機匣涂層發(fā)生碰摩,而過度碰磨會造成葉片開裂、涂層脫落等故障,增大發(fā)動機失效風(fēng)險[5]。可見如果能夠獲得瞬態(tài)葉尖間隙變化規(guī)律,可以為優(yōu)化發(fā)動機性能特性和降低發(fā)動機故障風(fēng)險提供一種途徑[6]。
獲得葉尖間隙變化規(guī)律的方法包括實時監(jiān)測法和數(shù)值計算方法,前者主要應(yīng)用于發(fā)動機產(chǎn)品研制后期,后者則多用于研制中前期。數(shù)值計算方法中功能最為強大的是NASA的NPSS計劃[7],該計劃基于準(zhǔn)確的3維部件模型以及完整的CFD和FEA數(shù)據(jù)資源,缺點在于需要劃分網(wǎng)格、添加載荷和熱邊界條件,因而費時費力;有些則不基于物理模型,直接根據(jù)FEA模擬結(jié)果、間隙實測數(shù)據(jù)等,利用公式擬合發(fā)展出經(jīng)驗性預(yù) 測方 法[8];Fiola[9]、Kypuros等[10]和Melcher等[11]則采用簡單幾何模型以及經(jīng)驗公式,模擬換熱過程及機械變形,達到快速預(yù)測葉尖間隙變化的目的。
航空發(fā)動機研制經(jīng)驗表明,在發(fā)動機方案設(shè)計過程中發(fā)現(xiàn)葉尖間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可以大大減少發(fā)動機設(shè)計后期試驗投入[12]。為了在方案階段實現(xiàn)對葉尖間隙的快速評估,本文根據(jù)高壓渦輪的結(jié)構(gòu)特點,吸收了現(xiàn)有快速預(yù)測方法的優(yōu)點,改進了渦輪盤瞬態(tài)變形快速預(yù)測方法。
1 方法改進及模型假設(shè)
1.1 方法改進
針對E3-GE-FPS發(fā)動機第1級高壓渦輪建立了考慮換熱作用的葉尖間隙模型[13],如圖1所示。該模型中高溫燃氣流經(jīng)葉片、輪盤盤緣以及機匣內(nèi)襯內(nèi)表面,引自壓氣機出口的空氣用于冷卻輪盤側(cè)面以及機匣,自機匣外側(cè)垂直引入的沖擊氣流用于實現(xiàn)主動間隙控制[14]。

圖1 E3-GE-FPS第1級高壓渦輪[13]
從圖中可見,影響渦輪盤變形的形式有熱變形和離心力帶來的變形。通過對Kypuros和Melcher模型[10]輸入?yún)?shù)進行修正,基于有限體積法發(fā)展了輪盤變形預(yù)測模型。具體改進如下:
(1)原模型采用等厚圓盤表示輪盤,為了更接近真實的等強度設(shè)計輪盤剖面,本文采用參數(shù)化模型定義變厚度輪盤。
(2)原模型只考慮溫度及轉(zhuǎn)速影響,實際不同冷熱氣流量對于輪盤換熱也有影響,本文據(jù)此對換熱模型進行改進,增加流量考慮。
(3)原模型對于輪盤外緣進行絕熱處理,為接近真實情況,本文增加了高溫燃氣對輪盤盤緣的加熱考慮。
(4)原模型將輪盤看作單一單元,本文采用有限體積法對輪盤分網(wǎng),并按次序?qū)Ω鲉卧M行換熱計算,模擬換熱過程。
(5)原模型任意時刻輪盤具有惟一溫度及材料屬性(彈性模量及熱膨脹系數(shù)),本文增加了不同單元不同屬性的考慮。
改進后的輪盤模型如下:通過8個半徑(R1~R8)以及4個寬度(W1~W4)定義參數(shù)化模型,如圖2(a)所示。對輪盤進行分網(wǎng):軸向分為3列,徑向分成n行,從而獲得由3n個圓環(huán)組成的輪盤離散模型。定義冷熱氣溫度、流量以及對流換熱路徑從而建立輪盤熱浸潤模型,如圖2(b)所示。

圖2 輪盤模型
1.2 模型假設(shè)
本文研究策略既不同于需要龐大數(shù)據(jù)資源、費時費力的NPSS計劃,又不同于靠數(shù)學(xué)擬合形成的經(jīng)驗方法,而是基于輪盤模型,遵循傳熱學(xué)、力學(xué)定律,針對發(fā)動機方案設(shè)計特點和需求,通過合理假設(shè)發(fā)展一種輪盤變形快速預(yù)測方法。所做假設(shè)如下:
(1)在發(fā)動機方案設(shè)計階段,尚未形成完整的輪盤特征,因此不考慮葉片安裝槽以及前后連接結(jié)構(gòu)等細節(jié)特征是合理的。
(2)事實上輪盤表面的對流換熱系數(shù)受流體類型、環(huán)境以及離心力作用而呈現(xiàn)區(qū)域各異分布,但真實的對流換熱系數(shù)有賴于試驗數(shù)據(jù),為簡化計算,本文參考Kypuros和Melcher模型,采用恒定的對流換熱系數(shù)。
(3)在真實發(fā)動機中,對流換熱與熱傳導(dǎo)同時發(fā)生,本文為適應(yīng)程序算法需要,將其假設(shè)為:在1個時間間隔內(nèi),對流換熱先進行,穩(wěn)定后再進行熱傳導(dǎo)直到穩(wěn)定。
(4)任意時刻輪盤沿軸向均存在溫度梯度,本文假設(shè)對于相同半徑的3個圓環(huán)單元,取均值作為等效溫度,用于機械變形計算。
(5)為簡化計算,假設(shè)任意時刻,溫度在各單元圓環(huán)內(nèi)部均布,因而材料屬性(彈性模量及熱膨脹系數(shù))對于各圓環(huán)只有單一值。
2 渦輪盤瞬態(tài)模擬方法
2.1 輪盤溫度計算方法
2.1.1 熱傳導(dǎo)機理
固體的1維熱流由傅里葉傳導(dǎo)定律給出[15]。將此方法擴展到多個維度,可模擬1個單元同時受四周所有單元的熱傳導(dǎo)作用。基于虛擬穩(wěn)態(tài)溫度假設(shè),提出了單位時間Δt內(nèi)某單元受四周單元傳導(dǎo)的熱量變化[8]

式中:K'為單元與某一相鄰單元綜合傳導(dǎo)率;Tn、Tv分別為相鄰單元或目標(biāo)單元溫度;SumKT為相鄰單元溫度與傳導(dǎo)率乘積之和;SumK為相鄰單元傳導(dǎo)率之和;m為固體質(zhì)量;Cpf、Cps、Cp為固體等壓比熱容。
2.1.2 對流換熱機理
液體流經(jīng)固體表面的對流換熱模型如圖3所示。假設(shè)單位時間內(nèi)液體質(zhì)量由流量Wf確定。考慮固體表面至中心發(fā)生的熱傳導(dǎo)作用,可以獲得單位時間Δt內(nèi)液體與固體中心發(fā)生的熱量交換[8]

圖3 熱對流

式中:Z為整個系統(tǒng)的熱特性

式中:A為接觸面積;h為對流換熱系數(shù);k為固體熱傳導(dǎo)率;X為固體表面距中心距離;Cpf,、Cps分別為液體、固體的等壓比熱容;Tf0、Ts0為液體、固體初始時刻溫度。
2.1.3 瞬態(tài)溫度計算流
將上述方程應(yīng)用到渦輪盤熱浸潤模型(圖2(b))中:式(1)用于輪盤所有單元熱傳導(dǎo),式(2)用于模擬氣流與輪盤外部單元的換熱。
基于此可以建立輪盤的熱浸潤計算流程。對于某一瞬態(tài)操作,冷熱氣與輪盤之間產(chǎn)生溫差,輪盤外部單元吸收或釋放,溫度變化,在輪盤內(nèi)部形成1個新的溫度場;由于輪盤內(nèi)部單元之間存在溫差,必然發(fā)生熱傳導(dǎo),最終獲得新的溫度分布。將各單元溫度傳遞給下一時刻,從而建立瞬態(tài)條件下的輪盤溫度計算命令流。
2.2 輪盤變形預(yù)測方法
2.2.1 應(yīng)力計算
在方案設(shè)計階段,輪盤應(yīng)力分析仍然可以在有限等厚圓環(huán)近似模型上進行,2個相鄰圓環(huán)A和B的定義如圖4所示。圖中:σ為應(yīng)力;r為半徑;w為圓環(huán)厚度;下標(biāo)i和o表示內(nèi)、外表面,r和h表示徑向和周向。

圖4 輪盤簡化計算模型
在相鄰圓環(huán)公共面,根據(jù)力的平衡及周向變形協(xié)調(diào),徑向及周向應(yīng)力差值分別為

對于已知尺寸的自由旋轉(zhuǎn)圓環(huán),其內(nèi)、外表面應(yīng)力存在固有關(guān)系。因此如果輪盤盤心或盤緣應(yīng)力已知,利用式(4)、(5)可逐步計算各圓環(huán)公共面應(yīng)力值,獲得輪盤應(yīng)力分布。
基于此建立輪盤應(yīng)力的迭代運算流程。假設(shè)盤心應(yīng)力(盤心通常是自由表面,因此徑向應(yīng)力為0),逐級向外計算應(yīng)力直至盤緣,對比計算的盤緣徑向應(yīng)力與由于葉片離心力帶來的徑向應(yīng)力是否一致,否則調(diào)整盤心周向應(yīng)力,反復(fù)迭代直到找到最佳值。
2.2.2 變形計算
假定輪盤材料為彈性材料,不考慮塑性變形,同時不考慮輪盤沿軸向變形。根據(jù)輪盤近似模型可知,將各圓環(huán)的變形量從最小半徑處累加直至最大直徑圓環(huán),即可獲得輪盤累積半徑變化,即盤緣徑向變形,表示為

對于最小直徑的圓環(huán)單元,已知內(nèi)表面徑向應(yīng)力為0,外表面由于受輪盤其他部分的離心作用而產(chǎn)生向外的拉應(yīng)力。其外表面變形的計算可以通過計算自由旋轉(zhuǎn)圓環(huán)的變形疊加外部受載的靜止圓環(huán)變形獲得[16]

式中:ρ為密度;ω為角速度;ν為泊松比;E為彈性模量;q為外部壓力。
對于其他圓環(huán),徑向應(yīng)變可表示為

式中:ε為應(yīng)變;T為圓環(huán)等效溫度;α為某溫度下的熱膨脹系數(shù)。
假設(shè)單個圓環(huán)的徑向應(yīng)變沿半徑方向呈線性變化,對半徑進行積分,則單個圓環(huán)徑向的變化為:

式中:Ac,Bc為描述圓環(huán)應(yīng)變線性變化的常數(shù)。
3 計算結(jié)果及分析
3.1 計算流程圖
根據(jù)前述分析,結(jié)合渦輪盤熱浸潤以及變形的主要要素,形成了渦輪盤瞬態(tài)變形計算流程,如圖5所示。其中,棕色模塊代表性能分析,需要定義基準(zhǔn)發(fā)動機以及瞬態(tài)歷程并輸出氣動參數(shù)及轉(zhuǎn)速;在熱浸潤模擬(藍色模塊),通過建立數(shù)學(xué)物理模型模擬換熱作用,獲得輪盤上的不同區(qū)域溫度分布;綠色模塊表示力學(xué)計算過程,輸入轉(zhuǎn)速、溫度、材料屬性以及葉片離心力,通過不斷迭代計算應(yīng)力分布獲得最優(yōu)解,進而預(yù)測輪盤盤緣變形。

圖5 渦輪盤瞬態(tài)變形流程
基于該流程,在Matlab中編制了預(yù)測代碼,通過設(shè)定模型參數(shù)、氣動輸入可以快速獲得溫度、應(yīng)力、變形的預(yù)測結(jié)果。
3.2 發(fā)動機基準(zhǔn)模型
引用文獻s[10]中輪盤、葉片的相關(guān)參數(shù)用于本文模型算法。為適應(yīng)算法特點,對部分參數(shù)進行了調(diào)整:在保持盤緣寬度、內(nèi)外徑不變的條件下,將等厚剖面改為典型輪盤剖面;初始輪盤溫度為高壓排氣溫度θ3的1/2;考慮材料屬性隨溫度的變化,所采用的Inco?nel718材料屬性隨溫度的變化趨勢[17]及其線性表達如圖6所示;此外根據(jù)算法定義計算時間間隔為0.5 s,假設(shè)葉片數(shù)量為50。綜合上述參數(shù)假設(shè)為基準(zhǔn)參數(shù)設(shè)定。

圖6 In718材料彈性模量E和熱膨脹系數(shù)α隨溫度變化
建立以該渦輪盤為對象的單軸發(fā)動機性能基準(zhǔn)模型,其設(shè)計點轉(zhuǎn)速對應(yīng)狀態(tài)性能參數(shù),見表1。利用性能設(shè)計軟件Gasturb[18]模擬油門由慢車保持(換算轉(zhuǎn)速為0.7),然后增大到設(shè)計點轉(zhuǎn)速對應(yīng)狀態(tài)(換算轉(zhuǎn)速為1.0)并繼續(xù)保持的瞬態(tài)過程,獲得關(guān)鍵位置氣動數(shù)據(jù)隨時間的變化關(guān)系。

表1 單軸發(fā)動機設(shè)計點轉(zhuǎn)速對應(yīng)狀態(tài)主要性能參數(shù)
3.3 變形預(yù)測結(jié)果
采用等厚空心輪盤模型和基準(zhǔn)參數(shù)設(shè)定,相應(yīng)的輪盤盤緣變形歷程如圖7所示。分為3個變化階段:在慢車和設(shè)計點的穩(wěn)定狀態(tài),輪盤變形緩慢增加,由于轉(zhuǎn)速并未變化,變形來源于輪盤溫度升高,表明本文方法模擬了輪盤不斷從環(huán)境中吸收熱量;當(dāng)轉(zhuǎn)速增大時(計算步長150起始),輪盤在離心力作用下變形加快,瞬態(tài)歷程結(jié)束時變形值最大,為1.45 mm,與文獻[11]所采用方法獲得的結(jié)果(最大2.11 mm)對比可知,初始變形相同,整體變形趨勢相似,而本文方法預(yù)測的變形結(jié)果較低;將時間間隔從基準(zhǔn)(0.5 s)調(diào)整到1.5、2.5 s,變形趨勢保持不變,而變形數(shù)值增大,接近或超過文獻[11]的預(yù)測結(jié)果。

圖7 輪盤變形計算結(jié)果對比
可見利用本文改進的方法可以較好地預(yù)測變形趨勢,而通過定義合理的參數(shù)如時間間隔,可以進一步對變形預(yù)測結(jié)果進行優(yōu)化。
3.4 參數(shù)影響分析
對于渦輪盤熱浸潤模型,影響換熱的主要參數(shù)包括對流換熱系數(shù)、熱傳導(dǎo)率、時間間隔以及初始輪盤溫度,不同參數(shù)設(shè)定影響換熱效果,進而決定輪盤溫度。直接影響應(yīng)力應(yīng)變的參數(shù)則包括葉片數(shù)量、輪盤剖面以及材料屬性。在基準(zhǔn)參數(shù)設(shè)定上,調(diào)整參數(shù)數(shù)值或類型(見表2),利用單變量法分析各參數(shù)對換熱及應(yīng)力應(yīng)變的影響。

表2 輪盤換熱及變形影響因素
3.4.1 換熱分析
設(shè)定基準(zhǔn)參數(shù),瞬態(tài)歷程結(jié)束時輪盤徑向溫度分布如圖8所示。從圖中可見,盤緣溫度較高,盤心溫度較低,中間呈現(xiàn)漸變的溫度梯度[19],證明了模型中燃氣加熱輪盤盤緣的有效性。

圖8 對流換熱系數(shù)對溫度分布影響
從圖中還可見,在不同的對流換熱系數(shù)下獲得的溫度水平也不同。較低的換熱系數(shù),表明流體對輪盤較難傳遞熱量,輪盤溫度水平較低,反之亦然。
對不同熱傳導(dǎo)率的換熱過程模擬結(jié)果如圖9所示。從圖中可見,高熱傳導(dǎo)率使溫度更高的盤緣更易于向溫度低的盤心傳導(dǎo)熱量,降低了徑向溫度梯度,使其變得更平。

圖9 輪盤熱傳導(dǎo)率對溫度分布影響
假設(shè)時間間隔變化時發(fā)動機單位時間間隔瞬態(tài)氣動參數(shù)保持不變。在此基礎(chǔ)上,將模型換熱的時間間隔從0.50 s調(diào)整為0.25 s和0.75 s,對溫度的分布影響如圖10所示。

圖10 計算時間間隔對溫度分布影響
從圖中可見,隨時間間隔的增大,溫度水平升高。這是由于在1個大的時間間隔,換熱更充分,進而導(dǎo)致溫度升高,反之亦然。
對流換熱是由流體與金屬固體之間的溫度差驅(qū)動的,因此固體的初始溫度對傳熱過程有很大影響。本文分析了不同初始溫度(壓氣機出口溫度θ3、θ3/2、以及ISA室溫(θ0=15℃))對溫度分布的影響,如圖11所示。

圖11 輪盤初始溫度對溫度分布影響
從圖中可見,輪盤初始溫度可以決定輪盤(尤其是盤心位置)的溫度水平,改變溫度梯度。在工程實際中,造成這一情況出現(xiàn)的主要源于發(fā)動機的起動時機,即是冷起動或是熱起動。
3.4.2 應(yīng)力應(yīng)變分析
本文在建立的方法中引入了葉片離心力作用。通過調(diào)整葉片數(shù)量(25、50、75)定義不同離心力,相應(yīng)的應(yīng)力分布如圖12所示。

圖12 葉片數(shù)量對周向應(yīng)力分布影響
從圖中可見,不同葉片離心力使輪盤周向應(yīng)力發(fā)生偏置,但差別較小。且葉片越多,離心力越大,周向應(yīng)力也越大,反之略微降低。
典型剖面輪盤與等厚輪盤周向應(yīng)力分布的對比如圖13所示。從圖中可見,典型剖面使輪盤周向應(yīng)力水平顯著降低,尤其是在盤心處,降低比例為44%。

圖13 輪盤剖面類型對周向應(yīng)力分布影響
模型采用的輪盤材料屬性(彈性模量和熱膨脹系數(shù))具有溫度相關(guān)性。應(yīng)變計算結(jié)果如圖14所示。與恒定的材料屬性設(shè)定對比可知,徑向應(yīng)變整體有所降低。

圖14 材料屬性對徑向應(yīng)變分布影響
4 變形預(yù)測與結(jié)果分析
4.1 不同換熱參數(shù)導(dǎo)致的輪盤變形
將表2中參數(shù)對應(yīng)的輪盤溫度、應(yīng)力應(yīng)變計算結(jié)果作為輸入對輪盤變形進行預(yù)測,采用相同油門(轉(zhuǎn)速)變化歷程、考慮不同換熱參數(shù)(表2中第1~4項)獲得的輪盤變形結(jié)果如圖15所示。

圖15 不同換熱參數(shù)導(dǎo)致的輪盤瞬態(tài)變形
結(jié)合表2和圖15具體分析如下:
(1)與基準(zhǔn)相比,改變輪盤初始溫度θi(4A,4C),使輪盤初始變形出現(xiàn)約±65%變化,原因是將初始溫度賦值給輪盤,自盤心到盤緣累積的熱變形導(dǎo)致初始變形發(fā)生改變;隨計算步長增加這種偏差逐漸減小,至瞬態(tài)歷程結(jié)束時變?yōu)椤?3%,主要是由于換熱受溫度差值影響,較低的初始輪盤溫度反而具有較高的熱量交換,結(jié)果使3種情況預(yù)測結(jié)果隨計算步長逐漸逼近。
(2)根據(jù)對流換熱機理可知,熱量與換熱系數(shù)h以及時間間隔Δt呈正相關(guān),即在高換熱系數(shù)和大的時間間隔下,輪盤獲得的熱量更多,因而溫度更高(圖15)。將這2個參數(shù)各自增大50%,瞬態(tài)歷程結(jié)束時輪盤累積變形增大約10%(1C,3C),反之則有所減小(1A,3A)。
(3)由前述分析可知,輪盤材料熱傳導(dǎo)率k決定徑向溫度梯度,進而影響輪盤變形。而傳導(dǎo)率的改變通常使部分單元溫度升高,而另一部分單元溫度降低,2種單元的熱變形相互抵消,使總的變形差別并不明顯(15)。熱傳導(dǎo)率增加50 %(2C),瞬態(tài)歷程結(jié)束時輪盤累積變形僅增大約3%,反之則有所減小(2A)。
4.2 直接參數(shù)作用導(dǎo)致的輪盤變形
采用相同油門(轉(zhuǎn)速)變化歷程、考慮直接參數(shù)(表2中第5~7項)作用獲得的輪盤變形結(jié)果圖16所示。

圖16 直接參數(shù)作用導(dǎo)致的輪盤瞬態(tài)變形
結(jié)合表2和圖16具體分析如下:
(1)與基準(zhǔn)相比,增加葉片數(shù)量NoB(5C),增大了輪盤承受由葉片提供的離心力,根據(jù)前述分析,使輪盤整體應(yīng)力水平升高,結(jié)果輪盤產(chǎn)生更大的變形。使葉片數(shù)量改變50%,瞬態(tài)歷程結(jié)束時偏置量約為±3%(圖16);除葉片數(shù)量外,單個葉片質(zhì)量、葉片質(zhì)心位置也可導(dǎo)致離心力變化,進而影響變形。
(2)改用等厚輪盤(6A),瞬態(tài)歷程結(jié)束時,使變形預(yù)測結(jié)果增加8.8%。這是由于采用等厚輪盤,輪盤應(yīng)力水平較高;而采用將盤心加厚的等強度設(shè)計,可以降低整體應(yīng)力水平,提高輪盤抗變形能力。
(3)相比可變材料屬性,恒定彈性模量E和熱膨脹系數(shù)α(7A)的設(shè)定將使預(yù)測結(jié)果增加8.3%。這是由于應(yīng)力主要由離心力和溫度作用導(dǎo)致,因此2種情況下應(yīng)力基本相同。但由于彈性模量影響彈性變形,熱膨脹系數(shù)決定熱變形,2項共同作用導(dǎo)致變形發(fā)生變化。
5 結(jié)論
(1)本方法是對現(xiàn)有簡化預(yù)測方法的發(fā)展,主要改進包括:可用于不同類型不同尺寸輪盤剖面;考慮了冷熱氣流量對換熱的影響;增加燃氣對盤緣加熱的模擬;對輪盤分網(wǎng)并分區(qū)域進行換熱模擬;考慮材料屬性隨溫度的變化。
(2)對流換熱系數(shù)、時間間隔影響輪盤整體溫度水平;熱傳導(dǎo)率影響盤心與盤緣間的溫度梯度;而初始溫度決定盤心及中部溫度。葉片數(shù)量變化使輪盤周向應(yīng)力發(fā)生偏置;與等厚輪盤相比,典型剖面能顯著降低周向應(yīng)力水平;可變材料屬性設(shè)定,使徑向應(yīng)變有所降低。
(3)綜合影響變形的主要參數(shù),其中初始輪盤溫度θi影響最為顯著,使輪盤初始變形出現(xiàn)約±65%偏置;換熱系數(shù)h以及時間間隔Δt使變形發(fā)生約10%偏差;采用等厚輪盤或恒定材料屬性的設(shè)定,導(dǎo)致預(yù)測結(jié)果出現(xiàn)8.8%和8.3%的偏差。葉片數(shù)量的調(diào)整可導(dǎo)致3%的變形變化;熱傳導(dǎo)率k改變對于預(yù)測結(jié)果影響較小。
(4)本方法較好地預(yù)測了加速過程中的渦輪盤盤緣變形瞬態(tài)歷程,通過定義參數(shù)可進一步優(yōu)化預(yù)測結(jié)果。本方法基于結(jié)構(gòu)模型,遵循傳熱學(xué)、力學(xué)基本定律,通過調(diào)整參數(shù)定義,可針對不同發(fā)動機、不同工作狀態(tài)建立滿足特殊需求的輪盤變形預(yù)測模型,具有較好的工程適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