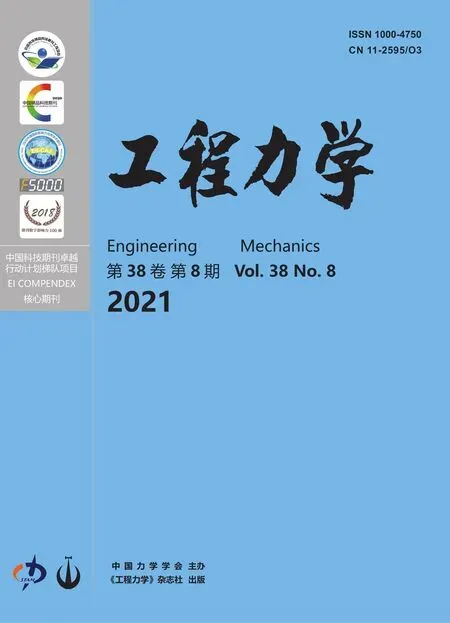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特性研究綜述
陳笑宇,王東升,付建宇,國 巍
(1. 大連海事大學(xué)道路與橋梁工程研究所,大連 116026;2. 河北工業(yè)大學(xué)土木與交通學(xué)院,天津 300401;3. 中南大學(xué)土木工程學(xué)院,長沙 410083)
多次地震后災(zāi)害調(diào)查表明,近斷層地震動(dòng)對(duì)臨近斷層的結(jié)構(gòu)物具有顯著破壞性。1957 年美國Port Hueneme 發(fā)生矩震級(jí)4.7 級(jí)地震,雖然震級(jí)較小,但其造成的災(zāi)害是同等震級(jí)地震中前所未有。后續(xù)研究發(fā)現(xiàn),此次地震事件中第一次記錄到含有速度脈沖的地震動(dòng)是造成大量結(jié)構(gòu)破壞的重要原因[1]。分別發(fā)生于1966 年和1971 年的Parkfield地震和San Fernando 地震再次證實(shí)了近斷層脈沖型地震動(dòng)的危害[2?4]。工程師們廣泛認(rèn)識(shí)到地震動(dòng)中的脈沖對(duì)長周期結(jié)構(gòu)的破壞性并在設(shè)計(jì)中考慮其影響卻始于1994 年Northridge 地震和1995 年的Kobe 地震[5]。這兩次地震均發(fā)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區(qū)域,結(jié)構(gòu)較普遍采用了現(xiàn)代抗震措施,但面對(duì)脈沖型地震動(dòng)作用較多建筑仍未能經(jīng)受住考驗(yàn)。這是由于近斷層地震動(dòng)攜帶的速度脈沖可以使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較大的位移反應(yīng),使得臨近斷層的結(jié)構(gòu)在其作用下有更高的強(qiáng)度和延性需求[5?11]。
對(duì)于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特性深入研究有利于加深對(duì)臨近斷層結(jié)構(gòu)反應(yīng)的認(rèn)識(shí),從而為臨近斷層結(jié)構(gòu)抗震設(shè)計(jì)提供理論依據(jù),也助益于加深理解震源破裂過程。但在研究早期,受強(qiáng)震儀水平限制,得到的近斷層脈沖型記錄十分有限,難以宏觀獲取其統(tǒng)計(jì)特性。1999 年土耳其Kocaeli 地震、Duzce 地震和中國臺(tái)灣集集地震中獲得了大量近斷層脈沖型強(qiáng)震記錄,為近斷層地震動(dòng)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礎(chǔ)數(shù)據(jù)資料。隨后,2008 年汶川地震、2013 年蘆山地震和2014 年魯?shù)榈卣穑覈箨懸搏@得了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本文從強(qiáng)震記錄處理、脈沖識(shí)別和建立地震參數(shù)統(tǒng)計(jì)關(guān)系等方面,對(duì)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特性相關(guān)科研工作做簡要回顧。
1 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成因
近斷層地震動(dòng)在諸多因素作用下主要呈現(xiàn)出上盤效應(yīng)、方向性效應(yīng)和滑沖效應(yīng)。上盤效應(yīng)是地震動(dòng)在上盤場地比其在距離發(fā)震斷層地表跡線相同的下盤場地?fù)碛懈鼮閯×业亩讨芷谡駝?dòng)、強(qiáng)震分布區(qū)域更大并且衰減更緩[12?15]。上盤效應(yīng)在逆沖斷層上表現(xiàn)尤為顯著。但是低頻速度脈沖主要是由方向性效應(yīng)和滑沖效應(yīng)引起。
方向性效應(yīng)是指斷層破裂朝向觀測(cè)點(diǎn),并以接近巖層剪切波速的速度傳播,地震動(dòng)能量在短時(shí)間內(nèi)同時(shí)到達(dá)觀測(cè)點(diǎn)并積累釋放,在地震動(dòng)記錄的初始階段形成大峰值、短持時(shí)的低頻速度脈沖;而在破裂后方,地震動(dòng)低頻成分被削弱,能量持時(shí)長、峰值小[14,16 ?17]。方向性效應(yīng)從物理層面可以理解為斷層破裂傳播的多普勒效應(yīng),它與震源破裂機(jī)制、斷層破裂方向和速度、斷層面的錯(cuò)動(dòng)方向以及破裂方向與觀測(cè)點(diǎn)的夾角等因素相關(guān)。由方向性效應(yīng)引起的速度脈沖在斷層傾角較小時(shí)常出現(xiàn)在觀測(cè)點(diǎn)與斷層面相垂直的方向上,在斷層傾角較大時(shí),常出現(xiàn)在與斷層走向相垂直的方向。
方向性效應(yīng)的另外一層含義是在地震動(dòng)空間分布上,地震動(dòng)的頻譜特性、持時(shí)和峰值等參數(shù)隨方位角發(fā)生變化。研究發(fā)現(xiàn),近斷層速度脈沖在空間上可以發(fā)生在不只一個(gè)方向,并且根據(jù)觀測(cè)方向不同表現(xiàn)出明顯強(qiáng)度差異[18?24]。
滑沖效應(yīng)與地震過程中兩盤發(fā)生相對(duì)滑移或錯(cuò)動(dòng)而產(chǎn)生的地面永久靜位移相關(guān),可以用彈性位錯(cuò)理論進(jìn)行解釋。在強(qiáng)震記錄中則呈現(xiàn)為近似階躍函數(shù)形式的永久位移時(shí)程。滑沖效應(yīng)引起的速度脈沖常呈現(xiàn)為單側(cè)脈沖,出現(xiàn)在平行于斷層滑動(dòng)的方向上。
對(duì)于走向滑移斷層,在特定觀測(cè)點(diǎn),向前方向性引起的脈沖主要出現(xiàn)在垂直于斷層走向的方向,滑沖效應(yīng)引起的脈沖則出現(xiàn)在平行于斷層走向的方向;而對(duì)于傾向滑移斷層,向前方向性效應(yīng)和滑沖效應(yīng)引發(fā)的速度脈沖均大概率出現(xiàn)在垂直于斷層面的方向,這兩種效應(yīng)引發(fā)的脈沖可發(fā)生耦合。
2 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處理
對(duì)于近斷層脈沖型地震動(dòng)的深入研究依賴于強(qiáng)震記錄的準(zhǔn)確獲得。由于背景噪聲、儀器噪聲、地面傾斜(儀器傾斜)等因素影響,原始地震動(dòng)加速度記錄不可避免的存在基線偏移等問題[25?28]。這種偏移對(duì)于加速度記錄影響較小,當(dāng)積分為速度、位移時(shí)程時(shí),誤差卻被急劇放大,對(duì)近斷層地震動(dòng)低頻速度脈沖特性的研究造成困難。
在地震動(dòng)中的低頻成分獲得充分關(guān)注前,高通濾波是最為廣泛的強(qiáng)震記錄處理手段[29],美國地調(diào)局(USGS)即采用此方法開發(fā)了通用基線校正程序BAP(Basic acceleration processing)。高通濾波會(huì)濾除包含永久位移信息的低頻信號(hào),因此不適用于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的處理。目前,各國學(xué)者提出的適用于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處理的方法可總體分為兩類:傳統(tǒng)分段校正法與基于時(shí)頻分析的校正方法。
2.1 傳統(tǒng)分段校正法
Graizer 等[30]于1979 年提出強(qiáng)震記錄中的基線偏移可以由多項(xiàng)式進(jìn)行擬合。Iwan 等[31]于1985 年采用此方式嘗試將原始強(qiáng)震記錄分為三段進(jìn)行擬合處理。該方法針對(duì)特定儀器的磁滯效應(yīng)引起的基線偏移,將加速度大于50 cm/s2作為固定限值,當(dāng)加速度首次大于此限值的時(shí)刻記為t1,末次大于此限值時(shí)刻記為t2,根據(jù)t1和t2將原始速度時(shí)程劃分為三段,對(duì)其尾段(t2時(shí)刻到記錄末端)進(jìn)行線性擬合,所得斜率af即為加速度時(shí)程尾段基線偏移值,即:

式中:vc(t)為t2到記錄末端的線性擬合;af為斜率;v0為截距。
中間段(t1到t2之間)加速度時(shí)程基線偏移平均值由式(2)獲得:

式中,vc(t2)為t2時(shí)刻線性擬合值。
尾段和中間段分別減去相應(yīng)的偏移值即為校正后的加速度時(shí)程。
這個(gè)方法可以保留強(qiáng)震記錄中的永久位移信息,但是t1和t2的選擇是基于特定儀器的特定效應(yīng)。基線偏移的原因多樣,固定限值的選取過于主觀,不適用于其它情況。
Boore[25]于2001 年對(duì)Iwan 等[31]的三段校正法進(jìn)行改進(jìn)。他在對(duì)集集地震記錄研究時(shí)發(fā)現(xiàn),此次地震中的儀器并未發(fā)現(xiàn)明顯磁滯效應(yīng),因此在基線校正過程中放棄了將50 cm/s2作為固定限值,重新定義了t1和t2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Boore[25]的方法中,t1和t2均被設(shè)定為可變參數(shù),t2定義為原始速度時(shí)程tf1到tf2段擬合直線與零軸交點(diǎn)時(shí)刻,(tf1為強(qiáng)震剛剛消退時(shí)刻,tf2通常選取記錄結(jié)束時(shí)刻)。t1是一個(gè)自由變化的參數(shù),不再以某一固定限值選取,但其選取規(guī)則不唯一,這對(duì)獲得穩(wěn)定的強(qiáng)震記錄的峰值位移(PGD)影響較大。
Wu 等[32]在基線校正過程中將位移時(shí)程引入,再次對(duì)關(guān)鍵時(shí)刻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優(yōu)化。在他們的方法中t1的選取被明確為原始位移時(shí)程開始非零的時(shí)刻;增加參數(shù)t3(位移時(shí)程達(dá)到永久位移水平的時(shí)刻),而后引入平坦度指標(biāo)f對(duì)t2進(jìn)行選擇:

式中:f為平坦度指標(biāo);r為線性相關(guān)系數(shù);b為校正后的位移時(shí)程;t3時(shí)刻到記錄尾部的最小二乘回歸斜率; σ為t3到記錄尾部位移時(shí)程的方差。
t2可為t3到記錄結(jié)束時(shí)刻之間的任意時(shí)刻,根據(jù)不同t2備選時(shí)刻對(duì)原始記錄進(jìn)行反復(fù)校正并計(jì)算相應(yīng)f值,取f值最大的時(shí)刻為最終t2的取值。Wang 等[33]結(jié)合Boore[25]和Wu[32]的工作,引入更細(xì)致的參數(shù)確定t1和t2的選擇范圍,采用窮盡算法對(duì)位移時(shí)程進(jìn)行非線性擬合從而獲得波形上最合理的t1和t2。至此,強(qiáng)震記錄基線分段校正實(shí)現(xiàn)軟件自動(dòng)化,降低了人為主觀性,也應(yīng)看到,對(duì)于關(guān)鍵時(shí)刻t1和t2初步范圍的確定仍是基于部分物理?xiàng)l件設(shè)定。
國內(nèi)也有學(xué)者基于Boore[25]工作做了諸多改進(jìn)和在強(qiáng)震記錄處理上的應(yīng)用。王國權(quán)等[27]基于集集地震動(dòng)數(shù)據(jù)對(duì)分段校正方法進(jìn)行優(yōu)化,于海英等[34]針對(duì)長持時(shí)的汶川地震動(dòng)記錄提出多段校正方法,謝俊舉等[35]也在汶川地震原始記錄的處理中應(yīng)用分段校正法。陳勇等[36]基于最佳時(shí)段擬合思想引入均方差來確定尾段最為平穩(wěn)的位移時(shí)程從而獲得合適的t2;榮棉水等[37]基于陳勇等[36]的工作再次引入時(shí)移斜率比、擬合段標(biāo)準(zhǔn)差和位移時(shí)程尾段均方差三個(gè)參數(shù)對(duì)關(guān)鍵時(shí)刻的選擇工作進(jìn)行優(yōu)化;張斌等[38]引入均方根偏差對(duì)關(guān)鍵時(shí)刻的選取進(jìn)行優(yōu)化。
國內(nèi)外這些工作將傳統(tǒng)分段校正方法中關(guān)鍵時(shí)刻的選取進(jìn)行了充分優(yōu)化,并應(yīng)用于實(shí)踐。臺(tái)灣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即采用傳統(tǒng)分段校正法處理原始強(qiáng)震記錄,建立了近斷層脈沖型地震動(dòng)數(shù)據(jù)庫[39]。結(jié)果證明,傳統(tǒng)分段校正法可以保留永久位移信息,處理近斷層地震動(dòng)原始記錄是有效的,但是無法解決此類方法存在的本質(zhì)問題。
分段校正法對(duì)于強(qiáng)震記錄的處理結(jié)果高度依賴于關(guān)鍵時(shí)刻t1和t2的選擇,時(shí)刻選點(diǎn)不同導(dǎo)致最終獲得的PGD 和永久位移差異性很大;更多關(guān)注于速度、位移波形的調(diào)整,本質(zhì)上去除了何種頻率成分未知[26]。
在傳統(tǒng)分段校正法中,基線偏移被簡化為加速度時(shí)程上的兩階段階躍函數(shù),這種假設(shè)與基線偏移成因的研究結(jié)果略有矛盾。如前所述,導(dǎo)致基線偏移的因素復(fù)雜,對(duì)應(yīng)頻率成份變化多樣,這種偏移應(yīng)該是一個(gè)復(fù)雜的頻率變化過程,而階躍函數(shù)頻率變化過于單一。隨著大型、高柔結(jié)構(gòu)建造越來越多,抗震分析對(duì)強(qiáng)震記錄中更真實(shí)的頻率成分(低頻)還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2 基于信號(hào)時(shí)頻分析的校正方法
隨著信號(hào)時(shí)頻分析技術(shù)的發(fā)展,諸多學(xué)者嘗試通過強(qiáng)震記錄的頻域分解、去噪解決基線偏移問題。
Chen 和Loh[40]基于離散小波變換提出三相位校正方法。首先將原始加速度記錄添零擴(kuò)充以解決小波分解邊界效應(yīng)問題,而后對(duì)擴(kuò)充后的數(shù)據(jù)以Meyer 小波為母波進(jìn)行離散小波變換,連續(xù)分解16 層后將各層分解得到的高頻項(xiàng)疊加重構(gòu),將重構(gòu)信號(hào)積分為位移,根據(jù)三個(gè)標(biāo)準(zhǔn)確定第一相位處理后的最佳近似信號(hào)。第一相位的處理中滿足了位移波形起始零值的限制并獲得了穩(wěn)定的PGD,但是位移時(shí)程尾部變形說明仍有低頻噪聲存在。將第一相位中擴(kuò)充后的原始加速度信號(hào)直接積分為速度時(shí)程,對(duì)速度時(shí)程進(jìn)行小波變換,同樣16 層分解后將高頻項(xiàng)逐層疊加,再將各層重構(gòu)的速度時(shí)程積分為位移時(shí)程,選擇一個(gè)尾部波形最平穩(wěn)的信號(hào)作為最佳近似。第二相位的處理能夠捕捉到位移時(shí)程平穩(wěn)的尾部波形。而后在第三相位處理中,將第一、第二相位結(jié)果結(jié)合,從而獲得最終校正后的記錄。此方法被應(yīng)用于集集地震動(dòng)原始記錄的處理,表現(xiàn)良好,但是物理基礎(chǔ)較為薄弱。
Ansari 等[41? 42]根據(jù)小波去噪理論提出強(qiáng)震記錄兩階段去噪方法。首先,對(duì)原始加速度記錄進(jìn)行N 層次小波分解,針對(duì)每一層的細(xì)節(jié)(高頻)項(xiàng)進(jìn)行降噪處理,將去噪后的所有細(xì)節(jié)項(xiàng)和最后一層近似(低頻)項(xiàng)重構(gòu)為新的加速度信號(hào);而后將重構(gòu)信號(hào)積分為速度時(shí)程,進(jìn)行二次降噪處理,以SureShrink 程序確定去噪限,再將去噪后的細(xì)節(jié)項(xiàng)重構(gòu),獲得降噪后的記錄。該方法針對(duì)有永久位移的近斷層地震動(dòng)記錄仍需要進(jìn)一步的基線校正處理。Chanerley 等[43]也使用小波變換將原始記錄分解為高頻子信號(hào)和低頻子信號(hào),對(duì)高頻子信號(hào)去噪,使用低頻子信號(hào)估計(jì)永久位移和儀器傾斜。這些基于小波變換的強(qiáng)震記錄處理方法與一般濾波方法假定噪聲存在于某一固定頻域內(nèi)不同,是對(duì)全頻域進(jìn)行分解去噪,但是分解層數(shù)是人為主觀確定的,著重于對(duì)信號(hào)進(jìn)行處理,物理基礎(chǔ)較為薄弱。
Huang 等[44]提出一種基于經(jīng)驗(yàn)?zāi)B(tài)分解(EMD)的基線校正方法。該方法首先將原始記錄低通濾波從而降低后續(xù)分解得到的本征模態(tài)分量(IMF)的階數(shù),而后將濾波后的信號(hào)進(jìn)行EMD 分解,篩選其中幾項(xiàng)IMF 疊加,構(gòu)建基線偏移模型。這個(gè)方法雖然引入了新的信號(hào)處理技術(shù),但是本質(zhì)依舊是將原始加速度時(shí)程基線偏移假定為階躍函數(shù)形式,并且處理結(jié)果非常依賴低通濾波限的選取,并未發(fā)揮EMD 分解的優(yōu)勢(shì)。筆者根據(jù)希爾伯特-黃能量密度譜分析提出了一種新的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基線校正方法。該方法通過對(duì)每一階本征模態(tài)進(jìn)行希爾伯特能量密度譜分析將原始信號(hào)區(qū)分為未被污染頻率成份和被污染的頻率成份,保留未被污染成份,針對(duì)被污染的頻率成份進(jìn)行處理,從而實(shí)現(xiàn)對(duì)于原始記錄的類似“靶向治療”的降噪處理。圖1 給出了通過此方法與傳統(tǒng)分段校正方法提取出的基線偏移的波形對(duì)比:通過新方法提取出的基線偏移包含復(fù)雜的頻率變化,與傳統(tǒng)方法相比更加符合基線偏移的物理過程。

圖1 希爾伯特-黃能量密度譜方法提取出的基線偏移與傳統(tǒng)方法提取結(jié)果的比較Fig. 1 Acceleration time history of baseline offset extracted by HSA method and that removed by traditional baseline adjustment method
綜上所述,現(xiàn)有的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處理方法中,傳統(tǒng)分段校正方法經(jīng)過多年發(fā)展已被充分優(yōu)化并實(shí)踐應(yīng)用,但是此類方法是基于加速度時(shí)程基線偏移為階躍函數(shù)形式的假設(shè),這與基線偏移的物理原因略有矛盾,難以在頻域盡可能最大真實(shí)地還原地震動(dòng)信息(尤其低頻),對(duì)于關(guān)鍵時(shí)刻的優(yōu)化選取并不能解決此問題。基于時(shí)頻分析的校正方法可以在頻域內(nèi)將原始地震動(dòng)信號(hào)做“解剖”并還原到時(shí)域。小波變換和希爾伯特黃變換等時(shí)頻分析手段都可達(dá)到此目的,但是此類方法在強(qiáng)震記錄里中的應(yīng)用和發(fā)展略顯緩慢,各個(gè)方法均未被充分研究。
3 脈沖識(shí)別與參數(shù)獲取
基于基線校正后的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各國學(xué)者對(duì)脈沖的識(shí)別和脈沖參數(shù)的獲取開展了廣泛研究。從結(jié)構(gòu)抗震角度,高效的識(shí)別和提取出脈沖波形,有利于“精準(zhǔn)”描述脈沖型地震動(dòng)作用下結(jié)構(gòu)響應(yīng)和破壞機(jī)理。在2007 年Baker[20]提出通過小波變換定量、自動(dòng)化提取脈沖之前,近斷層地震動(dòng)的相關(guān)研究主要是通過構(gòu)建各種數(shù)學(xué)模型來表征地脈沖特性。在Baker[20]小波方法提出后,又有一些采用信號(hào)處理手段的脈沖研究方法面世。
3.1 數(shù)學(xué)模型表征脈沖
Alavi 和Krawinkler[45? 46]界定了單側(cè)、雙側(cè)和多脈沖三種脈沖形式,采用方形波表征脈沖加速度時(shí)程。Makris 和Black[8,47? 48]同樣針對(duì)這三種脈沖形式以簡諧波構(gòu)建脈沖模型。Menun 和Fu[49?50]嘗試采用較為復(fù)雜的復(fù)合函數(shù)表征速度脈沖,并于2004 年根據(jù)Haskell 震源模型對(duì)近斷層脈沖的數(shù)學(xué)模型進(jìn)行改進(jìn)。李新樂和朱晞[51]在Menun 和Fu[49? 50]的工作基礎(chǔ)上提出改進(jìn)的等效速度脈沖模型,并討論了脈沖模型參數(shù)的確定方式;田玉基等[52]采用連續(xù)函數(shù)建立等效速度脈沖模型。
在眾多脈沖表述的數(shù)學(xué)模型中,Mavroeidis和Papageorgiou[53]于2003 年構(gòu)建的模型應(yīng)用最廣。該模型對(duì)Gabor 小波進(jìn)行修改提出了M&P 小波:

式中:t0為包絡(luò)曲線峰值時(shí)刻;其余參數(shù)同上。脈沖周期取為中心頻率fp的倒數(shù)。
此模型可以模擬脈沖的速度、加速度、位移時(shí)程和相應(yīng)反應(yīng)譜,與其它數(shù)學(xué)模型相比變化靈活,更接近于實(shí)際脈沖波形,并且在將其作為輸入研究單自由度體系地震反應(yīng)時(shí)能夠獲得封閉解。李帥等[54]采用Butterworth 濾波器將實(shí)測(cè)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分解為高頻無脈沖速度時(shí)程和低頻脈沖速度時(shí)程,而后以M&P 速度脈沖模型對(duì)低頻速度時(shí)程進(jìn)行擬合。Dickinson 和Gavin[55]基于Gabor小波也建立了速度脈沖模型。這些數(shù)學(xué)模型統(tǒng)一存在的問題是脈沖周期、幅值、位置、相位等重要參數(shù)需要提前獲取,而對(duì)于多脈沖情況,脈沖個(gè)數(shù)更需要人為確定。針對(duì)M&P 模型,Mimoglou等[56]優(yōu)化了各參數(shù)自動(dòng)化確定過程,他們建立了Sv×Sd譜,由此卷積譜峰值對(duì)應(yīng)的周期作為脈沖周期,再通過建構(gòu)小波的累積絕對(duì)位移(CAD)與反應(yīng)譜峰值的關(guān)系獲得其它參數(shù),此優(yōu)化程序后續(xù)應(yīng)用較少,原因尚不清楚。
另外,數(shù)學(xué)模型表述只是對(duì)于近斷層地震動(dòng)中脈沖波形的擬合重現(xiàn),無法對(duì)一條強(qiáng)震記錄是否為近斷層脈沖型進(jìn)行判別。有學(xué)者基于這些數(shù)學(xué)模型針對(duì)脈沖型記錄的判別開展了部分工作。Vassiliki 等[57]采用M&P 小波作為母波,將M&P小波與強(qiáng)震記錄的互相關(guān)系數(shù)作為脈沖判定指數(shù),當(dāng)此系數(shù)大于0.65 時(shí)地震動(dòng)記錄可被判定為脈沖型,當(dāng)系數(shù)小于0.55 時(shí)即為非脈沖型記錄。翟長海等[58]采用Dickinson 和Gavin[55]提出的脈沖模型構(gòu)造速度脈沖,而后由其是否占總能量30%來對(duì)脈沖型地震動(dòng)進(jìn)行判定,其中脈沖周期采用峰點(diǎn)法確定。常志旺等[58? 59]在2016 年對(duì)此方法進(jìn)一步修正。這些方法雖然能夠粗略實(shí)現(xiàn)脈沖型地震動(dòng)的判定,但是脈沖參數(shù)需要人為確定的困難仍無法解決。
3.2 基于信號(hào)處理的脈沖識(shí)別方法
隨著信號(hào)處理工具的發(fā)展,對(duì)于脈沖型地震動(dòng)定量的自動(dòng)化判別成為可能。Baker[20]基于小波變換提出脈沖型地震動(dòng)定量判定方法。該方法以Db 小波為母波,對(duì)地震動(dòng)記錄速度時(shí)程進(jìn)行連續(xù)小波變換,提取出系數(shù)值最大的小波,而后通過三個(gè)標(biāo)準(zhǔn)判定提取出的信號(hào)是否為早到脈沖——即向前方向性效應(yīng)引起的脈沖,需同時(shí)滿足的三個(gè)判定標(biāo)準(zhǔn)為:
1)以幅值比和能量比為參數(shù)通過回歸分析獲得脈沖指數(shù)(PI),當(dāng)PI>0.85 時(shí),提取信號(hào)即可被判定為脈沖,當(dāng)PI<0.15 時(shí)即為非脈沖;
2)脈沖能量積累達(dá)到10%的時(shí)刻早于原始地震動(dòng)總能量累積達(dá)到20%時(shí)刻;
3)原始地震動(dòng)速度峰值大于30 cm/s。
判定為近斷層脈沖型地震動(dòng)后,提取出的攜帶最大小波系數(shù)的小波即為地震動(dòng)中的等效速度脈沖波形,脈沖周期定義為提取出的小波最大傅里葉幅值對(duì)應(yīng)的周期。這是目前近斷層脈沖型地震動(dòng)研究工作采用最多的方法。該方法中,母波的選取雖然對(duì)脈沖型地震動(dòng)判定影響較小,對(duì)脈沖周期求解影響卻十分顯著[60?61]。小波系數(shù)表征的是相關(guān)小波的能量,提取最大系數(shù)的小波本質(zhì)即為找到能量最大的小波。因此,對(duì)于多脈沖情況,此方法只能提取出一個(gè)能量最大的脈沖。
Lu 和Panagioto[62]根據(jù)Baker[20]的小波方法,以M&P 小波為母波,針對(duì)多脈沖記錄提出了迭代提取的方法。這個(gè)方法中,脈沖個(gè)數(shù)與提取次數(shù)并不完全相關(guān),且每次提取出的脈沖在時(shí)域上相重疊,無法將各個(gè)脈沖發(fā)生時(shí)刻準(zhǔn)確定位,如圖2所示。

圖2 迭代提取方法兩次提取獲得的速度脈沖(2010 年新西蘭,Christchurch 地震,PRPC 臺(tái)站)Fig. 2 Pulses extracted by iterative procedure for velocity time history recorded in Christchurch earthquake at PRPC station
針對(duì)向前方向性脈沖,Xu 等[63]提出了多尺度分析法,仍可以理解為小波變換的擴(kuò)展。Chang等[64? 65]在近期研究工作中發(fā)現(xiàn),對(duì)于向前方向性效應(yīng)引起的脈沖,波形相似的速度脈沖有可能是由完全不同的頻率成分構(gòu)成(既可以由加速度脈沖積分而成,也可由加速度時(shí)程單側(cè)高頻振蕩積分而成),同時(shí)攜帶加速度脈沖和速度脈沖的地震動(dòng)對(duì)短、中周期(1.5 s~2.5 s)結(jié)構(gòu)有顯著影響,而非加速度脈沖型速度脈沖記錄對(duì)長周期(大于4 s)結(jié)構(gòu)影響顯著。因此他們通過小波包變換提取出速度脈沖,而后根據(jù)能量占比將速度脈沖型地震動(dòng)繼續(xù)深入判定,劃分為加速度脈沖型和非加速度脈沖型。這是近斷層地震動(dòng)中加速度脈沖首次受到特別關(guān)注,為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特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翟長海等[66]提出了脈沖型地震動(dòng)的能量判定方法。該方法可以對(duì)所有攜帶速度脈沖的地震動(dòng)記錄進(jìn)行判定,并未明確針對(duì)的是何種效應(yīng)引起的速度脈沖,應(yīng)該注意盆地效應(yīng)、軟土場地及液化等也會(huì)產(chǎn)生速度脈沖。他們將速度時(shí)程離散為多個(gè)半圈(half-cycles),根據(jù)重要半圈能量占地震動(dòng)總能量的比值,劃分為五種情況對(duì)脈沖型地震動(dòng)進(jìn)行判定,但無法同時(shí)獲取如脈沖周期等重要的參數(shù),并且脈沖個(gè)數(shù)要人為確定。Zhao 等[67]也提出了一個(gè)基于三角函數(shù)和速度穿零點(diǎn)判定脈沖型地震動(dòng)的方法(ZVPM 方法),也無法獲得等效脈沖。
筆者以希爾伯特-黃變換(HHT)為基礎(chǔ),提出了近斷層地震動(dòng)速度脈沖判定、波形提取和重要參數(shù)確定的自動(dòng)化方法[68?69]。該方法將頻率與能量相結(jié)合,認(rèn)為速度脈沖是由記錄中能量貢獻(xiàn)較大的低頻成份組成。這個(gè)方法與前述方法關(guān)注于地震動(dòng)整體波形不同,而是著重把握脈沖的低頻特性。因此通過HHT 方法提取的脈沖幅值不完全等同于原始記錄的峰值。首先,將記錄的速度時(shí)程通過聚合經(jīng)驗(yàn)?zāi)B(tài)分解(EEMD)為表征不同頻率成分的IMF,以PGV/PGA 比值作為頻率判定標(biāo)準(zhǔn)(PGV/PGA 大于0.12 即為低頻)、以能量貢獻(xiàn)率(ΔEc(n))表征各IMF 分量對(duì)原始地震動(dòng)總能量的貢獻(xiàn),如果存在某一階IMF 能量貢獻(xiàn)大于0.32,且其PGV/PGA 比值大于0.12,該記錄即可被判定為脈沖型地震動(dòng);所有能量貢獻(xiàn)率大于0.1 的低頻分量疊加即為提取出的粗糙速度脈沖信號(hào);而后通過雨流計(jì)數(shù)法去除時(shí)域內(nèi)“脈沖不相關(guān)”信息,最終將單個(gè)或多個(gè)脈沖準(zhǔn)確定位在時(shí)域上,它們可以不連續(xù)。該方法通過一次提取即可獲得脈沖個(gè)數(shù)、脈沖周期和脈沖幅值。目前,主要應(yīng)用于處理向前方向性效應(yīng)引起的脈沖型地震動(dòng)。若對(duì)近斷層速度脈沖成因感興趣,可結(jié)合震源信息對(duì)提取后的脈沖進(jìn)行后續(xù)研究。
近二十年來,針對(duì)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識(shí)別與提取學(xué)者們提出了諸多方法,使近斷層脈沖型地震動(dòng)的批量獲取以及后續(xù)的深入研究成為可能。目前,絕大多數(shù)方法的開發(fā)都是基于向前方向性效應(yīng)引起的速度脈沖,相比之下,針對(duì)滑沖效應(yīng)引起的脈沖研究較為不足。一些方法可以對(duì)脈沖型地震動(dòng)進(jìn)行判定和提取,但是無法對(duì)不同效應(yīng)引起的脈沖進(jìn)行深入識(shí)別。應(yīng)該指出,不同的脈沖成因?qū)е虏煌拿}沖特性,如有學(xué)者指出,與向前方向性相比,滑沖效應(yīng)引發(fā)的脈沖潛在破壞作用更大[70]。在后續(xù)研究中,除向前方向性效應(yīng)引起的脈沖外,滑沖效應(yīng)引發(fā)的脈沖特性值得同等關(guān)注,也包括二者的耦合出現(xiàn)。
另外,若干學(xué)者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除水平方向外,近斷層地震動(dòng)豎向分量中也會(huì)存在顯著速度脈沖,且其影響不可忽視[71?75],其在近斷層速度脈沖提取工作中仍缺乏獨(dú)立、系統(tǒng)的討論。
4 脈沖參數(shù)統(tǒng)計(jì)特性
通過前述方法提取出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波形后,各脈沖參數(shù)與地震參數(shù)的統(tǒng)計(jì)關(guān)系可以獲得。
4.1 脈沖個(gè)數(shù)與地震參數(shù)關(guān)系
Somerville 等[16]早在1997 年即提出近斷層地震動(dòng)中速度脈沖個(gè)數(shù)與一個(gè)斷層內(nèi)的破裂面相關(guān);Bray 和Rodriguez-Marek[76]也曾指出一條地震動(dòng)記錄中速度脈沖數(shù)與斷層滑移分布相關(guān)。這充分說明近斷層地震動(dòng)速度脈沖與斷層及破裂過程關(guān)系密切,可作為地震震源反演的信息使用,而不僅僅是出于結(jié)構(gòu)抗震研究需求[77?79]。
目前對(duì)速度脈沖個(gè)數(shù)確定的研究工作尚不充分。Bray 和Rodriguez-Marek[76]通過將脈沖幅值折減50%作為獨(dú)立的脈沖個(gè)數(shù),他們自己也承認(rèn)這很主觀。翟長海等[66]提出的脈沖型地震動(dòng)的能量判定方法給出了多脈沖的判別,而細(xì)節(jié)性信息不足。最近筆者基于前述HHT 方法對(duì)86 條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中的脈沖個(gè)數(sh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認(rèn)為速度脈沖個(gè)數(shù)與斷層類型、斷層距、場地條件相關(guān)[69]。與走滑斷層相比,多脈沖更易發(fā)生在逆斷層和逆斜斷層(reverse-oblique fault);針對(duì)場地條件,脈沖個(gè)數(shù)隨著場地條件Vs30(地下30 m 平均剪切波速)的增加而減小。綜合考慮斷層距與場地條件,多脈沖地震動(dòng)更易發(fā)生在相對(duì)集中的區(qū)域(圖3)。土層對(duì)于地震動(dòng)中長周期成份有放大作用,這使得在較軟場地可以識(shí)別到更多的脈沖。

圖3 速度脈沖個(gè)數(shù)與斷層距、30 cm剪切波速(Vs30)關(guān)系Fig. 3 Contour map of rupture distances, shear wave velocity and number of inherent pulses
4.2 脈沖周期與地震參數(shù)關(guān)系
在眾多研究中比較統(tǒng)一的認(rèn)識(shí)是,速度脈沖周期與矩震級(jí)相關(guān),也受場地條件影響。
近斷層地震動(dòng)速度脈沖周期與矩震級(jí)的關(guān)系已在眾多研究工作中得到證實(shí),各個(gè)統(tǒng)計(jì)回歸公式列于表1,示于圖4。從總體趨勢(shì)來看,脈沖周期隨震級(jí)的增加而增加,各個(gè)統(tǒng)計(jì)關(guān)系式間的差異來源于脈沖周期的定義和采用數(shù)據(jù)構(gòu)成不同。在眾統(tǒng)計(jì)模型中,Mavroeidis 和Papageorgiou 采用42 條記錄,而筆者工作基于PEER 數(shù)據(jù)庫中86 條近斷層脈沖型記錄,注意到筆者提出的統(tǒng)計(jì)模型和謝俊舉等[80]考慮汶川強(qiáng)震記錄后提出的模型最為相近。通過的統(tǒng)計(jì)分析發(fā)現(xiàn)脈沖周期也與斷層類型有關(guān),這在以往研究中未曾揭示[69]。Mavroeidis 和Papageogiou 的模型在小震級(jí)時(shí)吻合走滑斷層統(tǒng)計(jì)規(guī)律,而在大震級(jí)時(shí)傾向于逆斜斷層(reverse-oblique fault)。謝俊舉等[80]提出的模型由于考慮了以逆沖斷層為主要構(gòu)造形式的汶川地震,統(tǒng)計(jì)分析結(jié)果則更為靠近逆斜斷層的統(tǒng)計(jì)公式。三者之間認(rèn)識(shí)是一致的。

圖4 速度脈沖周期與震級(jí)關(guān)系統(tǒng)計(jì)回歸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pulse period and moment magnitude

表1 速度脈沖周期與震級(jí)關(guān)系Table 1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of pulse periods and moment magnitudes
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周期與板內(nèi)地震和板間地震也具有很強(qiáng)相關(guān)性[81?83]。Cork 等[81]根據(jù)板內(nèi)地震、板間地震將地震動(dòng)記錄分類進(jìn)行回歸統(tǒng)計(jì)發(fā)現(xiàn):在同等震級(jí)下,板間地震記錄的脈沖周期遠(yuǎn)大于板內(nèi)地震記錄的脈沖周期,這是由于板間地震的應(yīng)力降一般來講要低于板內(nèi)地震。筆者也提出,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周期與震級(jí)的關(guān)系與斷層類型相關(guān):對(duì)于走滑斷層,脈沖周期隨震級(jí)增長較緩,而對(duì)于逆斜斷層,脈沖周期隨震級(jí)增長較為快速。針對(duì)多脈沖情況,在同一條近斷層地震記錄中,所有速度脈沖的周期處于相近水平,可以由能量最大的脈沖(主脈沖)周期線性表達(dá)[69]。臺(tái)灣學(xué)者僅以臺(tái)灣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回歸了脈沖周期與矩震級(jí)的關(guān)系,認(rèn)為還是存在地區(qū)差異的[39]。
Rodriguez-Marek 和Bray[84]于2006 年針對(duì)場地反應(yīng)對(duì)近斷層地震動(dòng)方向性效應(yīng)脈沖參數(shù)的影響進(jìn)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土層場地的脈沖周期要普遍大于巖石場地記錄到的脈沖周期,并且隨著輸入地震動(dòng)脈沖周期的增加,土層場地與巖石場地記錄到的脈沖周期的比值趨向一致。很多學(xué)者根據(jù)可以獲得的數(shù)據(jù)資料對(duì)不同場地記錄到的脈沖周期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回歸,結(jié)果如圖5 所示。矩震級(jí)小于7.2 時(shí),土層場地記錄到的脈沖周期明顯大于巖石場地的脈沖周期,隨著震級(jí)的繼續(xù)增加,兩類場地的脈沖周期趨向于同一水平。由于脈沖周期的定義不同、采用的數(shù)據(jù)量不同,各個(gè)回歸模型有些許差異,但是統(tǒng)計(jì)回歸的總體趨勢(shì)是相近的,能夠和理論認(rèn)知相互佐證。

圖5 速度脈沖周期與場地條件關(guān)系統(tǒng)計(jì)回歸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pulse periods and site conditions
4.3 脈沖幅值與地震參數(shù)關(guān)系
與近斷層地震動(dòng)速度脈沖周期相比,脈沖幅值的影響因素較多,其與斷層距和場地條件均相關(guān),但是脈沖幅值與震級(jí)的關(guān)系目前在研究中并未達(dá)成共識(shí)。
在同等斷層距下,土層場地記錄到的速度脈沖幅值要大于巖石場地。這是由于近斷層地震動(dòng)作用下,土體反應(yīng)對(duì)長周期信號(hào)有放大作用。無論何種場地條件,記錄到的脈沖幅值隨斷層距的增加均有明顯衰減。關(guān)于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幅值的各個(gè)統(tǒng)計(jì)回歸公式列于表2。多數(shù)學(xué)者在對(duì)脈沖幅值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回歸分析時(shí)將震級(jí)作為影響因素納入回歸公式。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脈沖幅值與震級(jí)并不具有明顯相關(guān)性,因此在統(tǒng)計(jì)分析中只考慮斷層距影響[81,83]。筆者研究發(fā)現(xiàn),震級(jí)對(duì)脈沖幅值的影響根據(jù)斷層類型的不同有所差異。對(duì)于逆斜斷層,震級(jí)項(xiàng)系數(shù)僅為0.08,對(duì)脈沖幅值影響較小;對(duì)于走滑斷層,震級(jí)項(xiàng)系數(shù)達(dá)到0.2,對(duì)速度脈沖幅值影響較為明顯。

表2 速度脈沖幅值統(tǒng)計(jì)回歸關(guān)系式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of pulse PGV and earthquake parameters
針對(duì)多脈沖情況,在研究工作中界定了能量主脈沖,發(fā)現(xiàn)主能量脈沖多數(shù)為發(fā)生在時(shí)域的第一個(gè)脈沖,在一條近斷層強(qiáng)震記錄中,隨著脈沖個(gè)數(shù)的增加,脈沖幅值呈現(xiàn)線性衰減,每一個(gè)脈沖的幅值均可以用主能量脈沖幅值以線性函數(shù)表征。
獲取準(zhǔn)確的脈沖參數(shù)統(tǒng)計(jì)關(guān)系有利于近斷層區(qū)域的地震危險(xiǎn)性分析及特定場地下的結(jié)構(gòu)抗震設(shè)計(jì)等工作開展。目前來看,統(tǒng)計(jì)關(guān)系仍依賴于數(shù)據(jù)樣本的選取和處理,因此,不同學(xué)者的分析結(jié)果會(huì)存在些許差異。另外,統(tǒng)計(jì)工作結(jié)果的闡釋仍需深入的理論分析佐證,這依賴于地震工程和地震學(xué)界對(duì)相關(guān)問題的深入討論和研究。目前針對(duì)斷層類型與脈沖參數(shù)關(guān)系的討論依然較少,這二者是近斷層脈沖特性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很值得更多關(guān)注。此外,統(tǒng)計(jì)分析工作目前主要關(guān)注于水平向地震動(dòng)中的脈沖,對(duì)于近斷層豎向地震動(dòng)中的脈沖特性研究尚未見到。
5 脈沖特性對(duì)結(jié)構(gòu)反應(yīng)的影響
近斷層地震動(dòng)會(huì)很大程度增加臨近斷層結(jié)構(gòu)的強(qiáng)度和延性需求,造成較大的地震破壞[87?89]。脈沖周期、幅值以及脈沖個(gè)數(shù)等參數(shù)對(duì)結(jié)構(gòu)反應(yīng)的影響較為顯著[54,90 ?91]。速度脈沖對(duì)結(jié)構(gòu)反應(yīng)的放大作用體現(xiàn)在反應(yīng)譜上,為以脈沖周期(Tp)為中心的單峰曲線,且在0.9Tp處放大效應(yīng)最強(qiáng),具有顯著影響的周期范圍為0.5Tp~2Tp[22]。同時(shí),較大的PGV/PGA 值使得加速度反應(yīng)譜具有較寬的加速度敏感段,這增加了結(jié)構(gòu)基底剪力、層間變形和延性需求[87]。對(duì)于隔震結(jié)構(gòu),脈沖特性與其動(dòng)力響應(yīng)的相關(guān)程度尤為密切[92?98]。長周期、大幅值速度脈沖使隔震支座位移顯著增加,造成耗能構(gòu)件的破壞[92?95,97],對(duì)于高阻尼橡膠支座還要考慮其速度相關(guān)性在脈沖作用下的表現(xiàn)[98]。有研究表明,基礎(chǔ)隔震體系動(dòng)力響應(yīng)的最大值與脈沖周期、PGV/PGA 正相關(guān),其減震率與此二參數(shù)負(fù)相關(guān),脈沖幅值對(duì)基礎(chǔ)隔震體系的減震效果影響則相對(duì)集中,可作為隔震體系的重要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96]。
近年興起的自復(fù)位結(jié)構(gòu),因其兼具高耗能、小殘余位移的特性而獲得大家廣泛關(guān)注[99?105]。在近斷層脈沖型地震動(dòng)作用下,自復(fù)位結(jié)構(gòu)表現(xiàn)為泛旗幟型滯回模型,其彈塑性位移譜隨T/Tp值增大呈現(xiàn)出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shì),譜峰值對(duì)應(yīng)T/Tp值為1[101,105]。脈沖特性對(duì)樓層反應(yīng)譜也同樣具有放大效應(yīng)[106?107]。當(dāng)結(jié)構(gòu)周期與脈沖周期相近時(shí),樓層位移反應(yīng)譜值和加速度反應(yīng)譜值均明顯增大。
針對(duì)脈沖個(gè)數(shù)對(duì)結(jié)構(gòu)反應(yīng)的影響,有研究指出,當(dāng)脈沖個(gè)數(shù)為奇數(shù)時(shí)脈沖對(duì)結(jié)構(gòu)反應(yīng)的影響更為顯著[54]。受限于實(shí)際地震動(dòng)中的多脈沖及其相關(guān)參數(shù)研究的局限,脈沖個(gè)數(shù)對(duì)結(jié)構(gòu)動(dòng)力響應(yīng)的影響仍有待深入研究。
6 結(jié)論
隨著人類社會(huì)的發(fā)展,工程建設(shè)已無法完全避開臨近斷層區(qū)域。從20世紀(jì)至今發(fā)生的多次大地震表明近斷層脈沖型地震動(dòng)對(duì)結(jié)構(gòu)有顯著破壞作用,與震源過程也密切相關(guān)。深入研究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特性對(duì)結(jié)構(gòu)抗震設(shè)計(jì)、地震危險(xiǎn)性分析和震源破裂過程聯(lián)合反演等相關(guān)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對(duì)近斷層原始強(qiáng)震記錄處理、脈沖識(shí)別和提取以及脈沖參數(shù)的統(tǒng)計(jì)分析等研究工作進(jìn)行了簡要評(píng)述。
(1)對(duì)于近斷層原始強(qiáng)震記錄處理,傳統(tǒng)分段基線校正法的階躍函數(shù)形式假設(shè)過于簡單,基于時(shí)頻分析的校正方法在此方面逐步表現(xiàn)出優(yōu)勢(shì),宜被充分重視。
(2)近斷層地震動(dòng)脈沖識(shí)別與參數(shù)獲取大多基于向前方向性效應(yīng),針對(duì)滑沖效應(yīng)及二者耦合引起的脈沖研究不足。近斷層豎向地震動(dòng)中脈沖的形成機(jī)理也需獨(dú)立研究。
(3)脈沖參數(shù)與地震參數(shù)關(guān)系仍需要地震學(xué)等相關(guān)理論支持及實(shí)證分析,如斷層類型等因素對(duì)脈沖參數(shù)影響,也包括震源破裂過程與脈沖特性參數(shù)的關(guān)系等。
(4)真實(shí)脈沖參數(shù)的準(zhǔn)確獲得有利于加深對(duì)臨近斷層各類結(jié)構(gòu)動(dòng)力響應(yīng)的理解,從而對(duì)其施行更加高效的抗震或減震設(shè)計(j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