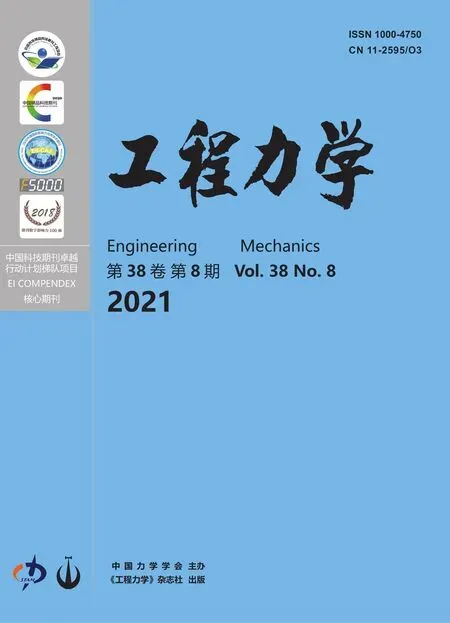基于Kresling 折紙構型的空間結構可控失穩模式研究
喻 瑩,徐新卓,羅堯治
(1.汕頭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廣東,汕頭515000;2.浙江大學空間結構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00)
折紙是一種古老的藝術,通常由二維紙張經過折疊形成各種不同的空間構型。由于折紙構型能夠實現復雜的三維形狀[1]、構型轉換[2]以及傳統材料難以實現的機械性能[3],其蘊含的科學價值和工程價值已經逐漸被國內外研究者重視,在可展天線、超材料、生物醫學、可展機器人[4? 25]等領域均有較好的研究成果出現。
失穩是指結構在壓力作用下突然發生大變形或大變位的現象,是結構中常見的破壞模式。一方面,如果能夠對結構在外荷載下的失穩過程和位置進行控制,將為智能結構的設計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很多折紙構型可以通過改變折痕性質實現多剛度、多穩定性的變化[26],Kresling[27]折紙構型就是其中的一種,如圖1。這種折紙構型是由Birtua Kresling 發現并命名的,其折痕是薄壁圓柱經扭轉產生的。該構型在折疊過程中會出現多個穩定狀態[28]。蔡建國等[29]分析了Kresling 折紙構型的邊長和高度對其力學性能和失穩應變能的影響;Paulino和Liu[30]使用鉸鏈彈簧模型分析了多層Kresling 模型,發現折痕剛度對其力學性能影響很小,并提出結構可能的破壞位置;Li 等[31]則研究了旋轉角度和高度比對Kresling折紙構型破壞性能的影響。Kresling 折紙構型的多穩態失穩模式已經引起了很多學者的重視。然而,對于如何控制該類結構的失穩,目前還未見相關研究。

圖1 兩層Kresling 折紙結Fig.1 Two-layer Kresling origami
本文基于有限質點法研究如何控制Kresling折紙構型空間結構的失穩模式。首先采用有限質點法模擬全桿模型下的Kresling 空間結構的失穩過程,計算其折疊過程中桿件應變能的變化,驗證有限質點法的有效性。然后在該結構中引入索單元和膜單元,研究索桿模型、索桿膜模型、嵌套式模型的失穩模式,分析預應力水平和彈性模量對結構剛度的影響,最終實現對雙層Kresling空間結構的失穩模式進行控制。
1 基于有限質點法的索、桿、膜結構分析
1.1 基本計算公式
有限質點法以向量力學為基礎,采用離散的質點描述結構,用牛頓第二定律描述質點運動,各質點的運動遵循牛頓第二定律,如下式:

1.2 單元內力計算
有限質點法通過逆向轉動求出單元純變形,進而得到單元內力[32]。此處簡單介紹桿、索和膜單元的內力計算。
1.2.1桿單元的內力計算
桿單元僅發生軸向變形產生軸力,并將軸力反向作用到與其相連的兩個質點上。質點α 的內力[33]可表示為:

1.2.2索單元的內力計算
根據索單元能夠受拉不能受壓的特點,其內力求解[34]如下:

1.2.3膜單元的內力計算
求解膜單元內力需要先估算一段時間內薄膜元的剛體平移和剛體轉動,利用虛擬逆向運動估算節點變形位移,然后在變形坐標系下計算單元的內力。三角形膜單元的內力計算公式[35]為:

2 Kresling 空間結構雙穩態研究
本節研究基于Kresling 構型的空間桁架結構的失穩過程。結構模型如圖2所示,其中底邊長a=1000 mm,側向斜邊長b=1500 mm,結構高h=1440 mm。所有構件均為彈性模量為2.1×105MPa的桿件,桿的橫截面積為393 mm2。

圖2 Kresling 純桿空間結構模型Fig.2 Bar model of Kresling spatial structure
采用有限質點法模擬該純桿模型在均布荷載P作用下的折疊過程,結構的失穩過程如圖3所示,在均布荷載P作用下,該結構向下折疊,結構高度從初始的1440 mm 變化到完全折疊的0 mm,此過程中構件的應變能變化如圖4所示。隨著該空間結構折疊下壓,構件的應變能從零增大到一個最大值然后又逐漸減小到零。這種現象即為Kresling折紙構型失穩過程的雙穩態現象。圖4將本文的結果與文獻[28]的計算數據進行對比,結果吻合較好,驗證了有限質點法在研究基于Kresling構型的空間結構失穩過程的有效性和準確性。

圖3 Kresling 空間結構折疊過程Fig.3 Folding processof Kresling spatial structure

圖4 Kresling 空間結構折疊過程應變能變化Fig.4 Strain energy variation in folding processof Kresling spatial structure
3 Kresling 空間結構的可控失穩模式研究
本節采用有限質點法對Kresling 空間結構的失穩行為進行研究,共分析了四種不同的結構布置:索桿模型、索桿膜模型、嵌套式模型和雙層模型。通過分析材料彈性模量和拉索預應力對結構豎向荷載下結構剛度和應變能的影響,尋找結構失穩模式的控制方式。
3.1 索桿模型模擬
索桿模型分為兩種:一種是斜框線AH、BI、CJ、DK、EL為索,其余單元均為桿件,如圖5;另一種是豎框線AG、BH、CI、DJ、EK、FL為索,其余單元均為桿件,如圖6。兩種模型均由12個質點組成,其中桿單元的數量為18,索單元的數量為6。頂部6個質點G、H、I、J、K、L作用相同的荷載P=1500 N,采用斜坡加載的方式進行加載,考察索的預應力和桿的彈性模量對結構豎向剛度的影響,取質點G的Z軸坐標隨時間變化曲線進行分析。

圖5 斜框線為索的索桿模型Fig.5 Cable rod model with inclined cable

圖6 豎框線為索的索桿模型Fig.6 Cable rod model with vertical cable
3.1.1斜框線為索的索桿模型模擬
當AH、BI、CJ、DK、EL為索時(如圖5),首先找到結構在預應力的作用下的自平衡狀態,然后再施加荷載P。不同預應力(0.001 MPa,0.01 MPa,0.1 MPa)對質點G的Z軸坐標的影響如圖7所示。由于該結構在較大預應力下難以維持穩定狀態,區別于Kresling 結構順時針轉動的失穩模式,結構會整體逆向轉動發生破壞,因此本文中索的預應力都比較小。隨著預應力的增大,質點G的Z軸坐標并沒有明顯的變化,結構剛度變化規律一致。

圖7 不同預應力下G 點Z 軸坐標變化Fig.7 Variation of Z-axis coordinate of G-point under different prestresses
圖8為桿的彈性模量(2.1×103MPa,2.1×104MPa,2.1×105MPa)對質點G的Z軸坐標的影響。此處選擇的彈性模量是為了考察材料對結構性能的影響,并不與具體的物理材料對應。隨著桿件彈性模量的增大,質點G的Z軸坐標因為桿件的彈性模量不同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桿件的彈性模量越大,質點G的Z軸位移越小,結構的剛度越大。以上分析說明索的預應力變化時,結構的剛度變化規律相同;桿的彈性模量越大,結構的剛度越大。

圖8 不同彈性模量下G 點Z 軸坐標變化Fig.8 Variation of Z-axis coordinate of point G under different elastic moduli
圖9為不同彈性模量和預應力下的結構應變能變化情況,當索預應力變化時,結構桿的彈性模量取2.1×103MPa,當桿的彈性模量變化時,索的預應力取0.001 MPa。從圖中可以看到,隨著桿的彈性模量不斷增大,結構的應變能峰值不斷變大。桿的彈性模量越小,結構應變能越快達到峰值。而隨著索的預應力的變化,結構的應變能變化規律一致。

圖9 不同彈性模量和預應力的結構應變能變化Fig.9 Energy variation of structures with different elastic moduliand prestresses
3.1.2豎框線為索的索桿模型模擬
當AG、BH、CI、DJ、EK、FL為索時(如圖6),預應力對外荷載作用下的質點G的Z軸坐標隨時間變化的曲線如圖10所示。隨著預應力的增大,質點G的Z軸坐標僅有細微的變化,結構剛度變化規律一致。預應力過大時,質點G、H、I、J、K、L會逆時針轉動以維持結構平衡,結構會整體逆向轉動發生破壞。

圖10 不同預應力下G 點Z 軸坐標變化Fig.10 Variation of Z-axis coordinate of point G under different prestresses
圖11為桿的彈性模量(2.1×103MPa,2.1×104MPa,2.1×105MPa)對質點G的Z軸坐標的影響。隨著桿件彈性模量的增大,質點G的Z軸坐標因為桿件的彈性模量的不同出現了明顯區別。桿件的彈性模量越大,質點G的Z軸位移越小,結構的剛度越大。以上分析說明不同索預應力對下,該構型剛度變化規律相同,然而彈性模量的不同對該結構的剛度變化影響較大。桿的彈性模量越大,該構型的結構剛度也越大。

圖11 不同彈性模量下G 點Z 軸坐標變化Fig.11 Variation of Z-axis coordinate of point G under different elastic moduli
圖12為不同彈性模量和預應力下的結構應變能變化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到,桿的彈性模量對結構應變能的影響與純桿結構相同。而隨著索的預應力的變化,結構的應變能變化規律一致。對比圖9,相同結構參數下,可以看到第一種索桿的布置方式下結構的應變能大于第二種布置方式。索的預應力對第二種索桿模型剛度的影響大于第一種索桿模型,但在預應力水平較小的情況下,無法通過設置預應力明顯地調控結構的豎向剛度。桿的彈性模量的不同對第一種索桿模型剛度的影響大于第二種索桿模型,在預應力相同的情況下,不同彈性模量引起的第一種結構的剛度變化更加明顯。

圖12 不同彈性模量和預應力的結構應變能變化Fig.12 Energy variation of structures with different elastic moduli and prestresses
3.2 索桿膜模型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圖5基礎上加上膜單元,構成索桿膜模型。整個模型由12個質點構成,其中桿單元的數量為18,索單元的數量為6,膜單元的數量為12。模型如圖13所示,頂部6個質點G、H、I、J、K、L作用相同的荷載P,采用斜坡加載的方式進行加載,考察膜的彈性模量和桿的彈性模量對結構豎向剛度的影響,取質點G的Z軸坐標隨時間變化曲線進行分析。

圖13 索桿膜模型Fig.13 Cable rod membrane model
圖14為膜的彈性模量(1.0×104MPa,1.0×106MPa,1.0×107MPa)對質點G的Z軸坐標的影響。從圖14、圖15可以看出隨著膜的彈性模量的增大,質點G的Z軸位移出現了較大的差別。膜的彈性模量越大,質點G的Z軸位移越小,結構的總應變能越大,結構的剛度越大。

圖14 不同彈性模量下質點G 的Z 軸坐標變化Fig.14 Variation of Z-axis coordinate of point G under different elastic moduli

圖15 不同彈性模量下結構的應變能變化Fig.15 Energy variation of structureunder different elastic moduli
圖16為膜的彈性模量EM(膜的彈性模量依次為102MPa、106MPa)和桿的彈性模量EB(桿的彈性模量依次為103MPa、104MPa、105MPa)對質點G的Z軸坐標的影響。從圖16所示的索桿膜結構剛度的曲線變化可知:1)膜的彈性模量不變的情況下,桿的彈性模量越大,結構剛度越大;2)桿的彈性模量不變的情況下,膜的彈性模量越大,結構剛度越大;3)當膜的彈性模量較小時,桿的彈性模量的改變對結構剛度的影響很大,當膜的彈性模量較大時,桿的彈性模量的改變對結構剛度的影響很小。

圖16 不同彈性模量下質點G 的Z 軸坐標變化Fig.16 Variation of Z-axiscoordinate of point G under different elastic moduli
3.3 嵌套式Kresling 空間結構的失穩模式研究
本節對嵌套式Kresling 空間結構的失穩模式進行分析。嵌套式Kresling 結構由內部較小的Kresling結構和外部較大的Kresling 結構組合而成,根據內外兩個結構旋轉方向的不同,分為內外自旋方向相反(圖17,模型A)和內外自旋方向相同(圖18,模型B)兩種。如圖17,從上向下看,外部大的空間結構為順時針旋轉,內部小的空間桁架結構為逆時針旋轉,二者旋轉方向相反。如圖18,從上向下看,外部大的空間桁架結構為順時針旋轉,內部小的空間桁架結構為順時針旋轉,二者旋轉方向相同。兩種模型均由24個質點構成,其中桿單元數量為72,索單元數量為12。頂部6個質點G、H、I、J、K、L作用相同的荷載P,采用斜坡加載的方式進行加載,考察內外自旋方向和內部Kresling 結構尺寸對結構豎向剛度的影響,取質點G的Z軸坐標隨時間變化曲線進行分析。h為內部Kresling 的高度,aa為內部Kresling 的邊長。外部Kresling 尺寸與第2部分模型的尺寸相同。

圖17 內外自旋方向相反嵌套模型(模型A)Fig.17 Nested model with opposite spin directions(Model A)

圖18 內外自旋方向相同嵌套模型(模型B)Fig.18 Nested model with same spin direction (Model B)
3.3.1內外自旋方向相反的嵌套結構
圖19為內部不同高度,不同底邊尺寸的內外自旋方向相反的嵌套空間結構在豎向荷載下質點G的Z軸坐標隨時間變化曲線。從圖可以看出:1)內部結構高度不變的情況下,邊長越大,該結構的剛度越大;2)內部結構邊長不變的情況下,高度越小,該結構的剛度越大。

圖19 模型A 質點G 的Z 軸坐標變化Fig.19 Z-axiscoordinatevariation of point G of Model A
3.3.2內外自旋方向相同的嵌套結構
圖20為內部結構在不同高度,不同底邊尺寸時,內外自旋方向相同的嵌套空間結構在外部荷載下,質點G的Z軸坐標隨時間變化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其變化規律與內外自旋方向相反的嵌套空間結構相同。

圖20 模型B質點G 的Z 軸坐標變化Fig.20 Z-axiscoordinatevariation of point G of Model B
如圖21所示,對比相同結構尺寸下,不同旋轉方向的嵌套結構質點G豎向荷載下的Z軸位移基本相同,因此內外結構的相對自旋方向對結構剛度沒有影響。

圖21 模型A 與B質點G 的Z 軸坐標變化對比Fig.21 Comparison of Z-axiscoordinateof point G between Models A and B
為進一步研究內部結構尺寸的變化對結構性能的影響,以模型A 為例,分別考察內部結構高度和底邊長對結構應變能在豎向荷載作用下變化過程的影響。如圖22所示,內部結構高度h不變時,隨著底邊長aa的增大,結構的應變能逐漸越大,并且均表現出雙穩態現象。然而,當內部結構底邊長不變時,隨著結構高度的增加,內部結構不再發生失穩,結構的雙穩態現象消失(圖23)。因此對于內外嵌套結構,無論旋轉方向如何變化,調節內部結構與外部結構的相對尺寸,能有效調節結構的應變能變化趨勢。

圖22 內部結構邊長對模型A 應變能的影響Fig.22 Energy variation of model A with different side lengths of internal structure

圖23 內部結構高度對模型A 應變能的影響Fig.23 Energy variation of Model A with different heightsof internal structure
3.4 雙層Kresling 結構的失穩模式分析
本節對雙層Kresling 索桿膜結構的失穩模式進行控制。為實現雙層Kresling 結構的失穩模式可控,必須定量的調整兩層之間的相對剛度。如果要實現下層結構失穩上層結構維持不變,則上層結構的剛度必須大于下層結構剛度,反之亦然。經過以上對索桿結構、索桿膜結構、嵌套式結構的分析發現,調整桿和膜的彈性模量,能夠有效達到調控結構剛度的目的。
分析模型如圖24所示,模型中單層Kresling模型的尺寸與第2部分模型相同。上下層索的預應力均取0.01 MPa。為實現下層結構失穩上層結構維持不變,上層桿的彈性模量為2.1×105MPa,膜的彈性模量為1.0×105MPa,下層桿的彈性模量為2.1×103MPa,膜的彈性模量為1.0×103MPa。在上層質點作用相同荷載P=1500 N,結構的失穩過程如圖25所示。為實現雙層Kresling 結構上層結構失穩下層結構不變,上層桿的彈性模量為2.1×103MPa,膜的彈性模量為1.0×103MPa,下層桿的彈性模量為2.1×105MPa,膜的彈性模量為1.0×105MPa。在上層質點作用相同荷載P=1500 N,結構的失穩過程如圖26 所示。由兩種不同的失穩模式可見,通過調節兩層結構構件的彈性模量,成功實現了對該雙層Kresling 結構失穩過程的控制。

圖24 兩層Kresling 空間結構模型圖Fig.24 Two-layer spatial structure model based on Kresling pattern

圖25 兩層Kresling 空間結構下層失穩Fig.25 Instability process of lower story of two-layer Kresling spatial structure

圖26 兩層Kresling 空間結構上層失穩Fig.26 Instability process of upper story of two-l ayer Kresling spatial structure
圖27為兩層Kresling空間結構在失穩過程中結構的應變能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隨著上層結構壓縮量的增大,應變能逐漸達到峰值,當上層結構達到最大下壓高度時,結構的應變能從峰值回落到一個低值,隨后下層結構開始壓縮,結構應變能又繼續變大。整個能量變化過程體現了每層Kresling 結構雙穩態失穩疊加后的特點。

圖27 兩層Kresling 空間結構應變能變化Fig.27 Energy variation of two-layer Kresling spacial structure
4 結論
本文采用有限質點法對基于Kresling 折紙構型的空間結構豎向荷載下的失穩過程進行了模擬。研究了不同結構布置下,結構彈性模量和預應力水平對該結構豎向剛度、失穩模式和結構應變能的影響,研究發現:
(1)對于Kresling 索桿結構和索桿膜結構,斜方向布索的索桿模型比豎方向布索的索桿膜性失穩過程中的應變能更大。在較低預應力水平下,索的預應力對結構失穩過程的影響較小。桿和膜的彈性模量對結構的失穩過程的影響較大。隨著彈性模量的增加,結構剛度變大,結構變形速率降低,結構失穩后存儲在結構中的應變能增大。
(2)對于嵌套Kresling 空間結構,內外結構的相對大小對結構的失穩過程有明顯影響,內部結構高度不變的情況下,底邊長越大,該結構的剛度越大。內部結構底邊長不變的情況下,高度越小,該結構的剛度越大。通過調節內外結構的相對尺寸,可以大幅調節結構失穩過程中應變能的發展,在單調遞增和雙穩態變化兩種模式之間調節。然而,內外結構的旋轉方向對結構的失穩過程影響不大。
(3)通過調節單層Kresling 索桿膜結構構件的彈性模量,本文實現了雙層Kresling 結構失穩模式的控制,為設計可控失穩模式的智能結構奠定了基礎。雙層Kresling 結構整個失穩過程中的能量變化體現了每層Kresling 結構雙穩態失穩相疊加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