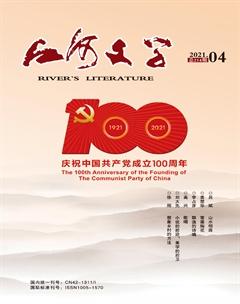短詩選粹
黑馬的村莊(組詩)
◇黑馬
大屯鎮
在大屯鎮,在四月潮濕的麥尖上
吹滅鐵道線上遙遠的黃昏
以風的行走,一匹馬的淺淺吟唱
在蘇北,荒涼如漠的地層之下
以黑夜中燃燒的瞳孔,以烈日般的胸膛
呵,這如火如荼的青春
在煤塵飛揚的日子,忘卻了影子的憂傷
像復活的斧子,這運斤成風的力量
煤炭,煤炭,我們共同照耀春天
這變輕的煤炭,蓄積了季節光芒的煤炭
飽含了工人階級多少的愛憎與情操的煤炭
讓我變得更黑的煤炭……
在感恩的清晨,在喧囂的街頭
我與煤炭工人們擦肩而過,我贊美這神秘的
閃電,一匹匹黑馬魚貫而出
哦,大屯鎮,我的整日傳誦的詩歌
抵不過他們肩頭飄浮著的一顆小小的煤粒
蟄居在這蘇北的煤礦
我將內心的烏金越發抱得更緊
黑馬的村莊
黑馬的村莊,深淵里涌動的魚群
一根衰草的力量大過一張硬弓
在冬夜,十匹黑馬復活
黑色的火,黑色的舌頭,不安的閃電的力量
在煤一樣的燃燒里,狂飆——
懷念風,吹過籬笆的輕響
一滴滴的聲音滴入季節的草莽
我透過霧氣,眺望村莊,冥想中的村莊
一場雪是一場風的密謀
風,剪下天堂里的鵝毛
無聲的麥地里,潛伏下十萬精兵
黑馬的村莊——黑黑的村莊——空空如也
失去星辰的村莊,失去皈依的村莊
我在仰望中,淚流滿面
居住在煤炭中間
我從城市一個人回到鄉下
居住在煤炭中間,雪花盛開
嚴寒里,幾乎一切都斂去了原色
惟有煤炭使我越發沉靜
在鄉村的周圍,煤炭像黑奴的家族
和草芥的姓氏一樣貧賤
我的黑哥們,守住黑夜的手掌和秘密
煤炭閃爍著日月星辰的光芒
一直是我內心仰望的部分
遠離煤礦的人們自然不會理解
那一塊塊黝黑發亮的寶貝
常常使人激動得為之流淚
在煤塵中整整奔波了一年的父親
穿灰棉襖的父親
終于坐下來了,圍爐夜話
爐火正旺,家園充滿溫馨的祥和
居住在煤炭中間
歲末的雪花還在窗外自由的舞蹈
在深夜,在礦區,一個名叫黑馬的詩人
還遲遲不愿睡去
他在潔白的稿紙上深情地寫下:
我是一塊沉靜的煤核
正從通往春天的夢巷里,悄悄醒來……
小聲歌唱(組詩)
◇符純榮
雨季
大雨滂沱。在南方
大雨
像一場找回知心的故交
被洗亮的
被蒙敝的
被歧義的……
有多少歡喜,就有多少惆悵
哪怕它們無一例外地經過這道門扉
雨水一直下著
在南方以南
無關乎季節、天氣。有人低頭走過
傘架上
一輪經年的日頭
給出持續的暖意
出租屋
在墻面拐角處
誰握著誰的手
寫下一個筆劃歪歪扭扭的愛字
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間
匆忙而散淡的時光
頓時有了愛的溫度、家的安謐
偶有蛛網、蚊蠅駐足其上
遷入一撥人
便認真清理一遍
但很快習以為常
——只有愛字是堅定的。在小小的出租屋
不被攪擾
保持住對人間的信心
故鄉的雪
返回的路上,大雪紛紛
背負行囊的人,像一群特殊信使
蓋上命運的郵戳
又一再錯過發往故鄉的郵車
低緯度的海風吹動。上升的樓層
述說高處不勝寒
留在異鄉的人,靠著冰冷的屋檐打盹
心中尚有暖意,被雪花傳遞
兩千公里外,路在延伸
蘆葦在風中尖叫
邊緣是過路黃、車前草——多么生動呵
被雪反復溫暖的這些地址
云海竹影聽茶雨(組詩)
◇劉貴高
云海
隱藏的不只是風景,還有雞鳴和犬吠
大別山腹地
那些綠蔭覆蓋的山水
那些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
生動著,浩浩蕩蕩的黃柏山意象
農耕文明與傳說隱藏得那么深
泛黃的族譜隱藏得那么深
白冠長尾雉與商城肥鯢
隱藏得那么深
只有滴落的天籟,彈奏心靈的遠方
竹影
與稻田池塘相連,與溪流水庫相伴
月色融融,溪水叮咚
鄉愁愈來愈濃
在天麻燉土雞的香味中搖曳
微風過處,輕漾的暖意擦亮了笛聲
天空披翠。朦朧的山谷,萬水靜綠
雞鳴聞三省的黃柏山
從沉睡中醒來。幽深的古塔
飄逸空靈的語境
斑駁的竹影,拂過豫鄂皖的醉意
茶雨
讀書修禪,法眼寺里佛香裊裊
那滴答的雨聲
不正是泡茶的水聲么
彌漫的霧氣彈奏曼妙的揚琴
黃柏山,茶中有景,景中有茶
銀杏樹下,紅塵俗事漸行漸遠
而你我,只不過是
這茶中的幻物
看九峰比肩,思浮沉人生
風嶺清嵐,過往的傳奇依稀浮現
風在午后敘事(組詩)
◇馬端剛
元月五日,日落時分
小寒大寒,冬肆無忌憚
記憶已是殘章
詞語藏在云朵背后
有悲,無淚,天空霧霾依舊
夢開始的地方
存在與虛無,不聲不響
臉龐,白紙上若隱若現
微笑,淚光,名字芳香四溢
時時刻刻,看見滴落
路上奔跑的孩子無影無蹤
一年,一生從鐘表脫離
寒風拯救暮鼓和鳥鳴
在潰退,在死亡
一聲與一聲,掛樹梢
花開花謝,糾纏著孽緣
風花雪月的脈象,走過千山萬水
兩只腳下,印跡虛無
蝴蝶,打量來往的人
經歷天災人禍,在不知名的酒館
將不知名的骨頭,煙火
倒入杯盞,除欲望
打坐布道,解人間疾苦
佛語凍僵,即將蘇醒
聽流水還魂
希拉穆仁之冬
直到離開,羽毛陳舊
未重現飛翔
遠方逝去,成群遷徙
淚痕死而復生,寒冷里咀嚼春
踩疼雪,是融化腳印的割舍
落葉堆,陽光忽略露水
被荒廢,被遺棄
想起時,抱起夕陽
抱起馬頭琴
在希拉穆仁
沒有房子,街道
酒杯,可以痛飲懸浮的悲涼
篝火飛向天,敖包已驚醒
彈唱,舞蹈
身體腹地,鳥鳴久遠
一個人的舊時代,守候牧場
看大雪紛飛
草生的敖包抓緊石子
迎接顫抖,唯有白樺林古老
策馬而來時
字句搖晃,白色呼喊
占據每一棵樹
誓言是年輕的閃電
眼睛牽掛,看見靜默的少女
身披紅色嫁衣
在荒草的無邊無際里蕩漾
風在午后敘事
影子使云朵慢下來
在高樓間盜火,墻上顏色舊了
像野馬,似飛鳥
奔跑,飛翔
眼眶積雪,含混,模糊
向誰去表達
臉是暗夜,如果云朵死了
可以用白紙
折一只鶴放在藍天里
是為了歡呼誕生
行走的,停滯的
廣場鴿子午后失眠
夢紛紛逃遁,習慣背叛
揉昨夜的眼,是今天掉下的淚
鑲入的牙齒,轉身扶正
漢字丈量良心,交換嘴唇,耳朵
未完成冬的介紹信
一人著火,另一人也著火
細節燃燒,只有雪降臨
吃掉所有的欲望
才會遇到春
閑談波爾卡(組詩)
◇張永波
和樹一起去思考
讓一些思考重新回到條枝上
從下到上,在云上結出些
雜七雜八的野果子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這些有思想的樹,長出了
人情世故的葉片
樹想法不多,有葉子就行
闊葉林和針葉松、山毛櫸
都是重要成員
向上向下是形式,沒有主義
種子,花香,風箏都是向上的風
它們組完成蓓蕾的造型
它們基因和我一樣
要求的并不多
抓住世界手的同時
我和樹一起思考
同一個問題
蓬蒿菊
在秋天,我開始懷念
蓬蒿菊的暖和善意,隱身遠郊近旁
一叢叢的藍或紫粉,都像我
安放在祖母墳頭
那一束追憶的心思
野生與馴養的區別在
秋天這本飽滿變數的綠皮書里
闡述到了極致的燦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些
快要到寒露的早晨
露水攀附在花朵上
像兒時攀附父親脊背的我
走在收割的田間
我看見,這些花朵用集體的
智慧,把秋天抬在高處
那金子般的質地,可以讓辛勤了半生的人
輕輕地
松上一口氣
閑談波爾卡
我的夜空里,不下雪
月光落在身上,仿佛
在下雪
那雪里,我看見了一匹棗紅馬
在旋風里跑,我不動
等一團火焰從身體內跑過
我用命運的韁繩套住它
雞鳴被大地出賣了
月光的身后沒留下什么
我們也不閑談。也不奢望去
讓低音區模擬空谷足音
笨拙的飛翔往往借助懸崖
夕陽無限,先于我
在一朵野花上安頓搖晃的影蹤
仰望的時候,一枚松針
深知人世間的隱疾
落下來的光芒,又輕又準
雨過天紫湖
天紫治愈色盲
雨絲纏著陽光,落得滿地都是
枯樹以為末日來臨
年輕的花朵開始勵志
野渡并不存在,湖岸被踢踏得汗毛倒豎
挑逗墨色的芳心
一朵烏云并沒有開口
以白日的夢游打撈當年明月
類似的痛苦,被一抷香囊釋盡
滄浪之水還噙在鷗鷺的眼里
而草木之心被琴弦收緊
十萬枚袖劍引而不發,把塔松鉚得生疼
被蟬鳴孵熱的懷抱,肯不肯容留
朝覲者的蜷縮
絲瓜花(外一首)
◇湯秀英
順著山坡爬上來的黃色小精靈
宛如一群淘氣孩子
用好奇的目光
打探著這個陌生的世界
有的花瓣偏小。如蠅頭小楷
只能容納一滴民間朝露
有些花瓣過大。遮天蓋地
足夠兩只蜜蜂搭伙過日子
經歷過夏天洗禮
只有少數花瓣完好無損
有蜜蜂居住生活過的大多數
已是千瘡百孔
挖花生
地表以下是一個偌大的子宮
無數白白胖胖的嬰兒等待問世
母親是個經驗豐富的接生婆
將鋤頭這把接生鉗高高舉起
再輕輕落下
生怕傷到嬰兒肌膚或臍帶
每一鉗下去都有驚喜
有時剖出的是獨生子
有時剖出的是雙胞胎
甚至還有三胞胎四胞胎五胞胎
不禁讓人感嘆
花生家族基因竟如此強大
一個人的河岸(外一首)
◇伍岳
最好是時過凌晨,蓉河空寂
孤獨會無限接近完整
最好是徒步而行,夜色濃郁
一個腳印會覆蓋另一個腳印
你可以聽見蛐蛐交換心事
在草叢間,咬住另一只的耳朵
燈影陷入聲浪里搖晃
當你裹緊秋夜的涼,念及
多年前一場沒有痊愈的隱痛
或掏出一小塊月亮碎片
只有那些落向河面的星星
試圖靠近你
中秋書
先寫月光,讓詩句
找到一卷鋪滿銀霜的生宣
讓《靜夜思》找到李白的雞距筆
然后再寫故鄉,它遠
需要一枚月亮牽著,還寫
門前那口水缸,鄉愁溢出
久了,容易發酵
把酒勾兌成墨汁,沾好一滴
下筆自有唐宋遺風
夜色上頭,當文字開始傾斜的時候
就寫一寫那條趴著的老狗
它對著院門喊一聲,回鄉的路就短一程
一個畫面(外一首)
◇林國輝
七月雨水
渾濁的江面
我順從這條道路,走進
紅光中的灰雨
雨水對我廣播
一截潮濕的信息
“田園淹沒了,快回來。”
如果雨氣
無法信任思想的鸚鵡
一切想象和傳說
也會保持
克制
雨水把格格不入的人
壓在異鄉的漩渦入口處
月光下
醉酒
經過平安路和南湖路的交叉路口
從電線桿子滑落一些碎裂的字符
叔叔年輕時會織毛衣,并是泥瓦匠
人民互相建造然后逐一磨損
門后山倒影在中秋的風雨里,一口
飲盡故鄉的池塘
和她的倩影
除非月光停止閃爍
大雁入飛悲傷的城市
一片落葉敲響
我空洞的外套
月永遠是道路的利刃
在我和高樓的圍墻下
用秋色
刺入她的心臟
夜坐(外一首)
◇魏先和
在枯萎的草地上坐久了
枯草就長進我的身體
把一枚下弦月看久了
月亮就變成一把雪亮的彎刀
如果你此時喚我
枯草必答以歸于泥土的靜寂
月亮必答以彎刀懸于頭頂的寒光
我一會兒低頭,一會兒抬頭
喜歡貼著大地死去的從容
也喜歡活在人世需要的鋒利
舊地
舊地的一切其實都是新的:
建筑,廣告牌,人行道的欄桿
大多已經換過,小店已經易主
在柱子上偷偷畫下的記號被時光覆蓋
唯有第六顆椰子樹
保持原來的樣子,風一吹
似乎在招呼我:
“多年不見!你怎么一個人回來了?”
海水一遍一遍沖洗記憶
少了你
那些說過話,發過的誓,終究殘缺不齊
責任編輯:邱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