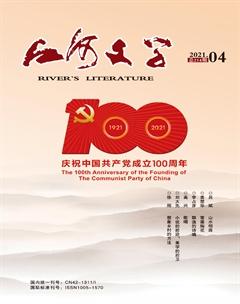讓歷史在敘事詩中重獲呼吸
李婉
眾所周知,蒙太奇(法語:Montage)是音譯的外來語,最早為建筑學術語,意為構成、裝配,后來被廣泛運用于電影剪輯技術之中。“蒙太奇就是根據影片所要表達的內容,和觀眾的心理順序,將一部影片分別拍攝成許多鏡頭,然后再按照原定的構思組接起來。一言以蔽之:蒙太奇就是把分切的鏡頭組接起來的手段。”因此,電影的基本元素是鏡頭,蒙太奇是連接鏡主要方式和手段。從這個角度來說,蒙太奇是電影藝術的獨特表現手法。
而詩人田耘將這種電影表現手法運用于詩歌的意象表達,使詩歌具有了畫面感和鏡頭感,使靜止的文字具有了流動的韻律,使情感表達更具抒情性和流暢性。她在2019年出版的中國第一部城市史詩《石家莊長歌》中就使用蒙太奇手法,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給詩歌增加了新的活力。
一、將詩歌中的歷史片段進行蒙太奇式分鏡頭剪輯
電影的蒙太奇手法,主要是通過導演、攝影師和剪輯師的再創造來實現的。首先導演先按照劇本或影片的主題構思,以分鏡頭的方式進行拍攝。然后再依照原定的主題故事,把這些鏡頭有機地、藝術地組接起來,使之成為完整的敘事單元。同時,這樣的敘事單元能給觀眾帶來連貫的情感投射,基于畫面的故事想象以及情緒有節奏的波動。就此產生一部好的影片。普多夫金說:“把各個分別拍好的鏡頭很好地連接起來,使觀眾感覺到這是完整的、不間斷的、連續的運動——這種技巧我們慣于稱之為蒙太奇”。在《石家莊長歌》中,田耘就是將蒙太奇手法中的遠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寫、大特寫、長鏡頭和短鏡頭等大量運用于詩歌的敘事和情感表達,為讀者展現了隱匿于歷史深處的眾多細節。
七天七夜白登之圍。讓滅火皇帝劉邦/寢食難安的,又豈是一個北疆的匈奴/智勇雙全的南越王,加上/嶺南復雜的地理環境,等于/一張殘缺不全的大漢王朝南疆版圖/打開這把鎖的鑰匙在東垣(今石家莊東古城)/是劉邦親征東垣的意外收獲。南越王的根/在中原,南越王竟是妥妥的東垣人/公元前196年。帶著一張紙和一張嘴/出發的大夫陸賈,一定還攜帶著一顆/被五月的春風吹得搖搖晃晃的心(《正確解決西漢嶺南問題的一把鑰匙,在石家莊》)
在這首詩中,蒙太奇手法常用的遠景、中景、近景、特寫等景別皆有。比如“七天七夜白登之圍”是遠景,交代了事件發生的時間和歷史背景,渲染出緊張的戰爭氣氛和西漢建國初期邊疆問題的棘手狀況,作者這里的遠景設計著重在于“取勢”,而非雕琢白登之圍的細節。之后,“讓滅火皇帝劉邦/寢食難安的,又豈是一個北疆的匈奴/智勇雙全的南越王,加上/嶺南復雜的地理環境,等于/一張殘缺不全的大漢王朝南疆版圖”是中景和近景。鏡頭由遠及近向本詩的主題“西漢嶺南問題”的層層遞進。作者用直觀的畫面再現了西漢初年劉邦面對錯綜復雜的邊疆問題時的窘迫和束手無策。接下來,近景以“一張殘缺不全的大漢王朝南疆版圖”直觀地給每一位讀者帶來一種深刻印象和心理訴求——此時的大漢王朝是不完整的,而它本來應當完整。此外,“帶著一張紙和一張嘴/出發的大夫陸賈,一定還攜帶著一顆/被五月的春風吹得搖搖晃晃的心”是特寫。這一組“鏡頭”(描寫)表現了歷史人物的內心狀態。“被五月的春風吹得搖搖晃晃的心”給我們帶來一種生活中不常見的特殊的視覺感受,只帶著一張紙、一張嘴,與一顆搖晃的心奉命出使南越國招降的欽差大臣陸賈,他心中的緊張、恐懼此刻已躍然紙上。
遠景著重于環境的渲染和烘托,近景表現人物面部神態和情緒、刻畫人物性格,特寫可以放大形象、強化內容、突出細節,從而準確地傳達故事情節,直接反映出主人公的心理狀態和情緒,并間接地影響讀者的心理反應。總的來說,全景出氣氛,特寫出情緒,近景側重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詩人田耘試圖通過《石家莊長歌》每首詩中不同景別的運用,給讀者帶來了閱讀每首詩時不一樣的獨特心理體驗。
她用由遠及近逐漸拉近的特寫鏡頭來深度描摹“土改”:“一開始,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太陽也照在了滹沱河上/‘土改的深度敘事里/一條河的身體里住著一百條河”(《石家莊宋村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
此外,詩人還用一系列的長鏡頭唱出這樣一曲深情的勞動之歌:“隨著1954年那陣喜悅的鞭炮聲/隨著一垛垛棉包中綻放的白色火焰/依次照亮清花車間、梳棉車間、粗紗車間、/細紗車間、織造車間、整理車間/是打開這座紡織博物館的正確方式/讓一雙忙碌的手匯入成千上萬雙手的海洋/將織機的隆隆聲化作心跳,讓棉花、/紗線和布匹的白色成為生命唯一的顏色/把每日機臺前的20公里秒殺成白駒過隙/是抵達一顆紡織之心的正確方式/換上短袖、單褲、涼鞋,戴上白帽/在溫度30度和濕度80%的巨大車間里/與六千顆紡織之心彼此應和/與翻飛的棉毛、斷頭的棉線共舞/與冬日屋頂不停滴落的水珠共舞/是觀看上世紀紡織操作的正確方式”(《在棉一紡織博物館》)。而長鏡頭中又包含著一系列特寫:當白色火焰“依次照亮清花車間、梳棉車間、粗紗車間、/細紗車間、織造車間、整理車間”,當“一雙忙碌的手匯入成千上萬雙手的海洋”,當新中國數千萬紡織工人曾經的日常重新再現在紙上,細細讀來怎不令人淚目?
可以說,《石家莊長歌》中的每首詩,都是由若干個鏡頭組成的。詩人用蒙太奇的手法將這些孤立的鏡頭進行有意義的剪輯、拼接,呈現出完整的畫面、故事和情緒,能讓讀者沉浸在歷史的敘事之中。與此同時,在對鏡頭的角度選擇上,也包含著詩歌作者的意念、情緒和褒貶。作者將自己的主觀評價運用蒙太奇手法隱形地投射在詩歌的編排以及敘事的順序之中。可見,詩人在呈現歷史的同時,也對歷史作出了自我評價。
二、全書蒙太奇式的整體呈現和組合方式
《石家莊長歌》中,30萬年的石家莊歷史被濃縮為“起”“承”“轉”“合”四部分,分別對應“古代石家莊”“近代石家莊”“解放石家莊”“現代石家莊”四個歷史時期。而這部書本身,就是一出以蒙太奇手段組接出來的歷史大劇。在“起”“承”“轉”“合”的分鏡頭聚焦下,鱗次櫛比、紛繁復雜的歷史人物、事件被安排得井井有條,按照時間順序在聚光燈下依次登場。
《石家莊長歌》中的蒙太奇式呈現,對于觀眾來說,是從分到分,而對于詩歌作者田耘來說,蒙太奇則先是由合到分,再分切,最后由分至合,一氣呵成。因此,在《石家莊長歌》的創作過程中,作者首先把搜集到的與石家莊相關的歷史人物與事件創作成獨立的詩歌作品,再按歷史時期歸類,歸類后再按時間和邏輯順序逐一排列。《石家莊長歌》“起”于《商王朝從石家莊走來》中“隨著商族的八次遷徙/沿著時光逆流而上”回到石家莊黃壁莊水庫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十五萬片甲骨文,一次歷史尋根之旅躍然紙上。而各個歷史時期的石家莊在“起”“承”“轉”之后,最終“合”于一首可歌可泣的“現代竇娥還鄉記”,一曲長歌隨著一件發生在石家莊的中國法制史里程碑事件畫上句號,更加凸顯出全書的人文關懷和人本主義精神。
《石家莊長歌》中的蒙太奇手法,是作者田耘用來講故事的一種方式。從讀者的角度來說,他們希望故事能夠講得順暢、生動,在富有感染力的同時又能被充分的調動起遐思和聯想,引起閱讀的興趣。同時,讀者也不僅僅滿足于弄清詩歌中的情節梗概,或一般地領悟到詩歌的思想意念,而是要求清晰流暢地感知敘事詩中敘述流程的每一個環節和細部。田耘蒙太奇手法的成功運用,讓讀者看懂每一處具體細節,從而對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全貌有一個清晰透徹的了解。可以說,《石家莊長歌》的最大特色就是遍布其中的大量歷史細節的呈現,它的成功就在于這些細節。
歷史本身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缺乏人性的溫度。然而一部優秀的史詩卻能夠貫通古今、穿越時空的阻隔,讓死去的歷史和人物再重新立于紙上,重新開始呼吸,讓21世紀的現代人重新觸摸到歷史的紋路。寫歷史詩,難度在于如何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歷史細節中,縱橫捭闔,而不被紛繁復雜的歷史細節所淹沒,從而失去自己的聲音,作者必須要有極好的掌控力,要有能力重構和再現歷史,并與之保持清醒的距離,必須具備高超的話語敘述技巧。
三、貫穿全書的一套特別的“蒙太奇語法”
愛森斯坦關于蒙太奇理論有一句名言:“兩個蒙太奇鏡頭的對列,不是二數之和,而是二數之積。”用匈牙利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茲的話說,就是“上下鏡頭一經連接,原來潛藏在各個鏡頭里異常豐富的含義便象火花似地發射出來。”電影在連接鏡頭場面和段落時,會根據不同的變化幅度、不同的節奏和不同的情緒需要,選擇使用不同的聯接力法,例如淡、化、劃、切、圈、掐、推、拉等,而與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有各種聯接力法類似,田耘的《石家莊長歌》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詩歌“蒙太奇語法”——
1.長鏡頭與大特寫構成的“圈”
“1947年夏,東焦村馬家巷/炕頭一盞忽明忽暗的煤油燈/上下跳躍的火苗/是否已經知悉一張四開的紙上/正在展開的驚心動魄/兩雙腳在門外來回踱步/三雙手將細節反復推敲、計算/算錯的路程問題不斷擦掉重改/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東西南北四個兵營、汽油庫、物資庫、/第三軍軍部、32師師部/《石門城防圖》上的每一個點/都暗藏霹靂和閃電”(《潛伏》)。讀者在閱讀這首詩時,難免會產生一種錯覺——這哪里是詩歌,分明是電影或電視劇里驚心動魄的地下工作的真實再現,而這些鏡頭也并非虛構,作者通過一系列的長鏡頭和大特寫,把當事人經歷這些事件時的心理感受逼真地再現了出來,給讀者帶來親歷性和現場感。
“長安公園西北蒼松翠柏中的閻錫山手跡/‘故燕晉聯軍大將軍綬卿吳公之墓/墳墓里閻錫山請高人制作的木人頭/與公園里蹣跚學步、牙牙學語的孩童/構成了一幅寓意多么深刻的畫面/藏在這歡樂世界之中的凝重/早已化為一個民族身體里的鈣質/在漫漫長夜后/托舉出一輪蓬勃的朝陽”。(《吳祿貞,或石家莊1911》)。這首歌頌辛亥革命烈士吳祿貞的詩,結尾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特寫鏡頭,“公園里蹣跚學步、牙牙學語的孩童”與旁邊墳墓里的無頭尸體形成鮮明對比,再次強調歷史的每一次進步都是英雄用生命和鮮血的代價換來的,沒有英雄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
2.以修辭的方式情感化的介入歷史
作者通過擬人、暗喻等手法,把痛感代入歷史,拉近與歷史的距離。“941年臘月,石敬瑭大軍圍困的/鎮州城內,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如粟的金銀,卻無法為兩萬多個/由于饑餓而痙攣的胃換來一粒米/換不回涂漆函里自己的頭顱”(《真定,真定》),本來可以使鬼推磨的“如粟的金銀”,在關鍵時刻卻一錢不值,既換不來一粒可以飽腹的米,也換不回自己的性命,這種強烈的痛感被植入詩中,使讀者產生共鳴。
“半鉤留照三秋淡,一練分波平鏡明/一座橋聞名于世,不是因為/永定河上燕京八景的‘盧溝曉月/而是因為一名‘失蹤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因為1937年7月8日/凌晨五點,那蓄謀已久的炮聲/北方最大的石橋上,被迫與/一群舉槍狂笑的日軍合影的/485個怒目圓睜的石獅子/眼里噴射出的,是血與火”,《在太行山上》一詩中,作者的歷史痛感表達得更為濃烈,詩句也就更富感染力,擬人手法的成功運用使被日寇欺凌的民族仇恨力透紙背,當盧溝橋上的485個石獅子都“怒目圓睜”“眼里噴射出血與火”,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燃燒的將是千百年來所未曾有過的熊熊火焰。
3.以畫面感的方式再現歷史人物的復雜心理
作者將復雜的理性思辨作直觀化畫面處理,再現歷史人物面對種種事件時的復雜心理。還以《正確解決西漢嶺南問題的一把鑰匙,在石家莊》為例:“智勇雙全的南越王,加上/嶺南復雜的地理環境,等于/一張殘缺不全的大漢王朝南疆版圖”。歷史教科書中需要用整整一個段落來講清的問題,在這里只用一句話就解決了,A加B等于C的一道加法,一目了然地直觀再現了西漢初年劉邦面對棘手的南疆問題時的苦惱和煩悶心理。
“有因必有果。1996年廣州市重點工程/‘廣電大廈為越王城讓位幾十米是果/公元前196年趙佗奉漢稱臣/為國家統一讓位是因;/‘趙陵鋪‘趙佗公園‘趙佗先人墓/歷代吟詠趙佗浩如煙海的詩句是果/一顆身居王位卻‘寢不安寧,食不味甘,/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心存不安,因為不能奉侍漢朝的/赤子之心,是因”(《正確解決西漢嶺南問題的一把鑰匙,在石家莊》)。
作者在這首詩中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古今,由公元前196年“為國家統一讓位”“赤子之心”的“因”,引出1996年“為越王城讓位幾十米”的廣州市重點工程廣電大廈之“果”,寥寥數行,就勾勒出今天的石家莊趙陵鋪、趙佗公園,廣州市中心的廣電大廈,與公元前196年的南越王趙佗的因緣際和,將歷史的理性思辨梳理得井然有條。
4.通過強烈的對比映襯人物內心
以《傅崇碧,石家莊1947》為例,“1932年入團宣誓時沸騰起來的熱血/遭遇一顆1933年打進后腦勺的子彈/卻并未冷卻。那個寡不敵眾/帶著十幾個人壯烈跳崖的17歲少年/頭朝下掛在樹藤上,臉上血流如注/卻望著敵人扔下后被樹枝攔住/沒有爆炸的‘馬尾手榴彈,笑了”,當“熱血”遭遇“子彈”卻并未冷卻,壯烈跳崖的17歲少年“臉上血流如注”卻望著一顆手榴彈“笑了”,這兩個鏡頭的強烈對比,相信會令每一位讀者過目難忘,它們映襯出的,是17歲的紅色少年傅崇碧那顆永不磨滅的紅色的心,一系列長鏡頭和特寫中,一個在慘烈的戰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堅毅勇敢的少年將領形象已躍然紙上。而下文中“那個每當想起尸橫遍野的戰友/與敵人的尸體抱在一起再也無法分開的情景/便會泣不成聲的老人,那個最愛吃地瓜、土豆/退休后將自己的全部積蓄20萬元/捐獻給四川老家‘希望工程的老人”,卻凸顯出一個英雄“堅硬”表象下的“柔軟”,而這種柔軟并不是他的弱點,而是令他身上的人性光輝更加燦爛,熠熠發光,更加凸顯出一個既堅毅勇敢又無私善良、充滿博愛精神的英雄形象。
綜上所述,詩人田耘在《石家莊長歌》中,通過對蒙太奇手法的一系列創造性運用,完成了石家莊30萬年歷史在紙上的再現,通過躍然紙上的一個個歷史鏡頭的組接,演出了一幕歷史活劇。運用如剪輯方式再次呈現的重大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無不令人讀來回味悠長。
以詩歌寫史,在當下的中國詩壇絕非主流,因為用詩歌去展現歷史的困難程度人盡皆知。除了搜集整理史料方面的困難外,更多的則是表達上從何處下手的困難,以及如何讓已經遠去的歷史引起讀者共鳴的困難。為了克服這些困難。作者要把自己真正融入那段歷史,用可觸可感的詩歌鏡頭、直擊人心的語言還原歷史現場的真切感,融入作者個人鮮活而深切的生命體驗,讓歷史重新在紙上站立起來,用那些閃閃發光的細節和場景。讓死去的歷史重新再獲得呼吸作者通過蒙太奇手段重組歷史的瞬間,再次去講述真實,還原真實,從而用詩歌的抒情性填補了歷史的縫隙。
而挽留那些已經逝去和行將逝去之物,正是文學存在的全部價值與意義。伽達默爾說:“日常語言就像是普通的硬幣,而詩歌語言則是金幣。”“詩不會褪色,因為詩的語言把短暫的時間,帶入一種停滯之中。”《石家莊長歌》中,作者田耘對于蒙太奇手法在詩歌中的創造性運用,正是把我們這個偉大而飽經苦難的民族那些不該被輕易忘記的歷史鏡頭“帶入一種停滯之中”的有效嘗試。
責任編輯: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