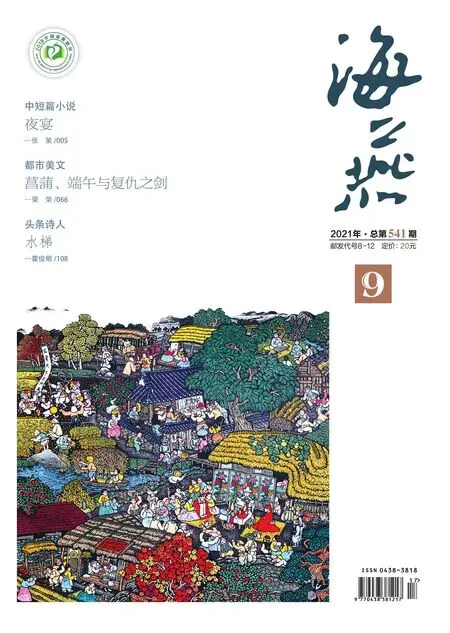橘樹下的遐想(外一篇)
文 胡富健
父親老了,已年近八旬,每當(dāng)站在橘樹下,便遐想,春天那些濃郁潔白的花,秋天結(jié)出的金黃香甜的果。
橘樹,常綠喬木,生在江南,不像白楊挺拔,沒(méi)有銀杏高貴,不如水杉偉岸,也無(wú)青松剛強(qiáng)。在父親眼中,它的每一片綠葉,都是一個(gè)故事;每一枚果實(shí),都是一個(gè)希望。它是明山秀水滋育出的嘉木,浸透了杏花春雨的芬芳明麗,也浸透了迷蒙梅雨的悱惻纏綿;浸透了太陽(yáng)的激情熱烈,也浸透了月亮的幽冷寂靜。在陰多晴少的江南,太陽(yáng)和月亮?xí)r常隱匿行跡,或蔽于濃霧之中,或藏于云層之間,在太陽(yáng)月亮的陰晴變換里,那玉樹臨風(fēng),獨(dú)立寒秋,滿枝滿椏的卻是萬(wàn)千太陽(yáng)和萬(wàn)千月亮的精靈。好像太陽(yáng)和月亮借著霧啊云啊這些道具的掩蔽,早把自己做了分身術(shù),躲進(jìn)了一棵棵橘樹中。橘樹是太陽(yáng)樹、月亮樹,它生長(zhǎng)出一個(gè)個(gè)的太陽(yáng)和月亮,橘樹是節(jié)日樹、吉祥樹,它的樹上掛著過(guò)年的燈籠和祝福。
父親出生在橘鄉(xiāng)黃巖,與橘樹打了一輩子交道,雖稱不上專家,卻是種橘的一把好手。父親對(duì)橘樹的嫁接、施肥、病蟲防治、采摘、儲(chǔ)存等等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每年收獲的橘子,不僅比別人家的甜,賣相也好,來(lái)收橘子的販子一看就中,往往搶先訂購(gòu),價(jià)錢也要貴一些,這常會(huì)引得鄰居羨慕。鄰居常跟著父親操作,對(duì)自家的橘進(jìn)行管理,向父親討要秘訣,父親都毫不保留地講解傳授,鄰居們都非常受益。
父親識(shí)字不多,只有初中學(xué)歷,當(dāng)年考入當(dāng)?shù)氐拿#驗(yàn)榉N種原因,未能就讀,50多年了,還仔細(xì)保管著一張已經(jīng)泛黃的高中入學(xué)通知書。雖然高中沒(méi)讀成,但父親在務(wù)農(nóng)的歲月里,并沒(méi)有泯滅對(duì)知識(shí)的渴求,對(duì)書本的鉆研。父親常說(shuō)種田人就要像種田人的樣子,把田種好,把橘樹管理好,多產(chǎn)橘,產(chǎn)好橘。因此,父親把當(dāng)年能買到的僅有幾本有關(guān)橘子栽培的書翻爛了。父親與橘為伍,也越來(lái)越像一棵橘樹了。父親的這種對(duì)書的愛(ài)好鉆研,對(duì)事情的矢志執(zhí)著,深深地影響了我的人生。
記得小時(shí)候,父親提個(gè)敞口木匣子,不知是干啥,里面放著鐵鉤、鋼絲、刮皮刀、鉆、鑿、小榔頭……稍長(zhǎng)大些才知是捉樁蟲用的。大集體時(shí)干農(nóng)活,父親常帶我到橘園里,圍著橘樹樁轉(zhuǎn),發(fā)現(xiàn)橘樹樁旁有樹木粉末堆起,那是有樁蟲在破壞嚼樹槳,于是,父親拿起一把稻草,隨手一箍就扎成一個(gè)簡(jiǎn)易墊子,往地上一放,一屁股坐下,開始聚精會(huì)神捉拿樁蟲。樁蟲大的有鉛筆那么粗,小的如鐵釘,長(zhǎng)短一寸左右,而樁蟲這“壞蛋”鬼精鬼靈的,打著地道戰(zhàn),常常會(huì)拐彎,這時(shí)父親木匣子里的十八般兵器就派上用場(chǎng),鑿開些口子,淺的就用鉤來(lái)鉤出,深的拐彎的就拿帶鉤的鋼絲鉤,不開太大的創(chuàng)口,類似現(xiàn)在人類的微創(chuàng)手術(shù)。而我則都是和小伙伴滿橘園的瘋玩,追蝴蝶,捉蜻蜓,撲蚱蜢,逮蛤蟆……當(dāng)父親成功捉拿了“壞蛋”,便喊我們拿去玩,直到玩死它,被一群螞蟻搬走為止。每當(dāng)此時(shí),父親則在橘樹腳下,點(diǎn)上支煙,開始吞云吐霧,心里舒坦得像打了場(chǎng)大勝仗,瞇眼看煙霧升騰,我知道父親又開始遐想了。
父親常想自己什么時(shí)候也有屬于自己的一片橘園。那時(shí)家里人口多,我和弟弟、妹妹都小,又要上學(xué),每年分得口糧后,到年底抵扣了勞動(dòng)掙得的工分,還要倒給生產(chǎn)隊(duì)錢,稱為“找出”,如果自己有成片橘園,就不會(huì)有如此窘境。那年我當(dāng)兵后,農(nóng)村實(shí)行了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父親夢(mèng)想成真,有了幾十上百棵橘樹,雖分散多處也總算是有了自己的橘園。父親在大集體時(shí)學(xué)到的本領(lǐng)就發(fā)揮了作用,他侍弄橘樹更加勤勉,第一年就有幾千元的收入,這與“找出”的年成可是個(gè)天壤之別了,要知道那時(shí)的萬(wàn)元戶很稀罕,還接受政府的表彰呢!但是,好景不長(zhǎng),橘子有豐年小年,價(jià)錢隨行就市,豐年價(jià)賤,有時(shí)小年更糟。隨著時(shí)光的流逝,不時(shí)有惡劣的氣候,不斷有橘樹凍死、老死。盡管如此,父親的積極性還是很高,一直堅(jiān)守著,呵護(hù)著他的橘樹,不停止橘樹下的遐想,遐想過(guò)上橘子一樣更好更甜蜜的日子。
父親說(shuō),橘樹也有生老病死,可我覺(jué)得父親更像棵橘樹。那年父親生病住院,母親又陪著,橘樹無(wú)人管理照料,一任病蟲肆虐,等父親出院,有些橘樹病入膏肓,即使努力救助,還是沒(méi)法成活,陸陸續(xù)續(xù)的枯萎被砍作柴火了。父親不死心,挖掉枯樹,裁上新苗。如今,父親已是耄耋之年,而那些橘樹又到了青春勃發(fā)產(chǎn)橘的青壯年。
我想,父親對(duì)橘樹的感受是深入情懷的,是父親擺脫失學(xué)煩惱、走向社會(huì)、建設(shè)家園、孝敬長(zhǎng)輩、養(yǎng)育子女的依靠,這種依靠就是這樸素而勤勉的生活態(tài)度和方法。
橘樹又開花了,聞著清香馥郁的芬芳,我想,他老人家又要開始新的遐想了,遐想這后皇嘉樹的風(fēng)華絕代,“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精色內(nèi)白,類任道兮。”以及它的秋天,陽(yáng)光照進(jìn)橘林,金燦燦,黃澄澄,一個(gè)個(gè)橘子就如一顆顆發(fā)光的寶石,閃爍著絢麗的光芒。
道地頭的夏夜時(shí)光
道地,字典解釋是做人地道,實(shí)誠(chéng),或者是名副其實(shí)。但在我的家鄉(xiāng),道地是一種名稱,管天井叫道地,或道地頭。上世紀(jì)70年代,風(fēng)扇還是個(gè)稀罕物,停電倒是常態(tài)。夏天,傍晚的道地頭成了納涼消暑的好去處。

插圖:邢安贏
從記事起,感覺(jué)我們住得很特別,前無(wú)氣派的臺(tái)門,四周沒(méi)有高高的圍墻,不是老式的四合院,而是長(zhǎng)長(zhǎng)的十幾間樓房相連著的一整棟,坐北朝南的畚斗樓,冬暖夏涼。鄰里都是一個(gè)祖宗下來(lái)的叔伯親份,從最東邊那家到西頭那家要走一百多米的路,但我們很自豪,這樣的房子沒(méi)有四合院的那種憋屈壓抑,有的是通透舒暢。家家的道地都連通著,我們小孩子特喜歡,可以肆無(wú)忌憚地瞎跑瞎鬧騰,尤其能放開手腳滾鐵環(huán),架起磚塊可以滾銅鈿銅板比遠(yuǎn)近。
小時(shí)只知玩樂(lè),長(zhǎng)大后才佩服起我的老太公,一個(gè)晚清秀才,眼光杠杠的,十九世紀(jì)就有如此氣魄,敢于從幾個(gè)兄弟合住的臺(tái)門里,跳出個(gè)新天地,砌了個(gè)前后左右毫無(wú)遮擋的“長(zhǎng)大屋”,足見其思想的開放,他辦的私塾遠(yuǎn)近聞名,惠及鄉(xiāng)里。
記得各家門前的道地,并不都是石板的,有的是在“雙搶”(夏收夏種,需要搶收搶種,所以稱作“雙搶”)前,把家門前的地平整了,當(dāng)曬場(chǎng),等“雙搶”結(jié)束在芒種之前又種上相應(yīng)的蔬菜。那時(shí),每當(dāng)太陽(yáng)落山,大人們收了晾曬的稻谷,便到房子西頭的小塘提水,潑灑在各自的道地上。當(dāng)然,泥巴地是極少噴灑的,不然,第二天曬稻谷就不易干。有的人家便三三兩兩將飯桌搬出,邊吃飯邊海闊天空的“賣白搭”(黃巖方言,意同北方人的嘮嗑,聊天吹大牛)。
那時(shí),道地頭的前后左右除了橘子樹,還有柳樹、苦楝樹、桉樹、沙樸樹、田榴樹等,一年四季郁郁蔥蔥。因此,就是在無(wú)風(fēng)的夜晚也比房間里涼快。有時(shí),我躺在涼席上,母親坐在邊上給我搖蒲扇,不是扇涼,而是趕蚊子,一家人圍著,在蛐蛐的奏鳴聲中,聽爺爺講些老套的故事,什么楊家將啊、岳飛啊,不過(guò)我還是最喜歡聽“四叔婆”講故事,她是名醫(yī),年輕時(shí)跟著農(nóng)村的戲班子唱過(guò)戲,故事可多了,什么唐明皇與楊貴妃、薛仁貴與樊梨花、賣油郎與花魁女、梁山伯與祝英臺(tái)等等,雖然那時(shí)聽起來(lái)都懵懵懂懂的。
也常有村里人串過(guò)來(lái),講些道聽途說(shuō)的事,尤其那些鬼故事,雖然喜歡聽,但聽著聽著就鉆到大人的懷里,晚上睡覺(jué)興許還會(huì)做惡夢(mèng)。還有的中年男女湊到一起,平時(shí)不好說(shuō)的話這個(gè)時(shí)候打著哈哈也就說(shuō)出來(lái)了,時(shí)不時(shí)地還帶上幾句葷話,那時(shí)沒(méi)有黃段子,也就相互之間開幾句玩笑,耍耍嘴皮子,我們這些小屁孩也聽不懂,都自顧自地玩耍。
很多時(shí)候,我們是圍繞著這道地頭玩小屁孩的游戲,什么捉迷藏啊,騎人馬打架啊,離腳頭啊,打陀螺啊,不一而足。有時(shí)也會(huì)跟大哥哥數(shù)天上的星星,什么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北斗七星……他站在開闊的道地頭用手指著天空,一顆一顆教我們認(rèn)星星,我看著看著就睡著了,不知什么時(shí)候被父母放到了床上。
夏夜里螢火蟲也特別靚眼,像是一種精靈,在夜空中飛舞著,給我們這些小屁孩帶來(lái)深厚的玩味和興趣。每當(dāng)看到一盞盞小燈籠似的螢火蟲翩然飛來(lái)的時(shí)候,就會(huì)飛奔向它們,這時(shí)的螢火蟲就像故意逗人似的,一會(huì)兒高飛,一會(huì)兒低飛,我們就會(huì)窮追不舍,拿蒲扇飛撲,一會(huì)兒跳起,一會(huì)兒貓腰。也有幾人結(jié)伴特意去道地周圍的橘樹林捕捉,把它們放進(jìn)洗凈的青霉素瓶里。那時(shí)我很好奇,它們的屁股上怎么會(huì)一閃一閃的放光,認(rèn)為很好玩,甚至,在晚上睡覺(jué)時(shí)把瓶子放在被窩里,讓它們伴我進(jìn)入夢(mèng)鄉(xiāng)。母親為了不讓我殘害這些小生命,就嚇唬說(shuō),夜里螢火蟲會(huì)爬出鉆進(jìn)我的耳朵,會(huì)把“耳朵王”給吃了,起先也都怕怕的,將信將疑,通過(guò)幾次都相安無(wú)事,后來(lái)也就不當(dāng)回事了。
我最喜歡夏天的道地頭,鄰居有好吃的,只要在道地頭叫一聲,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都會(huì)“嗖”一下出來(lái),圍一圈,七嘴八舌的嘗個(gè)鮮,嘴甜的,往往還會(huì)把主人的手藝夸贊一番;心細(xì)的,會(huì)討個(gè)做法。幾個(gè)桃子、半塊西瓜、幾塊糕點(diǎn),傳遞著道地清涼之外的另外一種清涼。
上世紀(jì)80年代的一個(gè)夏天,父親扛回家一臺(tái)落地扇,后來(lái)又買了一臺(tái)12寸的黑白電視,夏夜就有了躲進(jìn)小樓的享受,道地納涼便逐漸地淡出。現(xiàn)在老家建設(shè)了新農(nóng)村,家家都建筑起了別墅式的小洋樓,道地頭的清涼已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tái),但卻在我的心里漸漸滋生出一抹又一抹的清涼環(huán)繞在童年上空,隨著歲月的逝去而益發(fā)的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