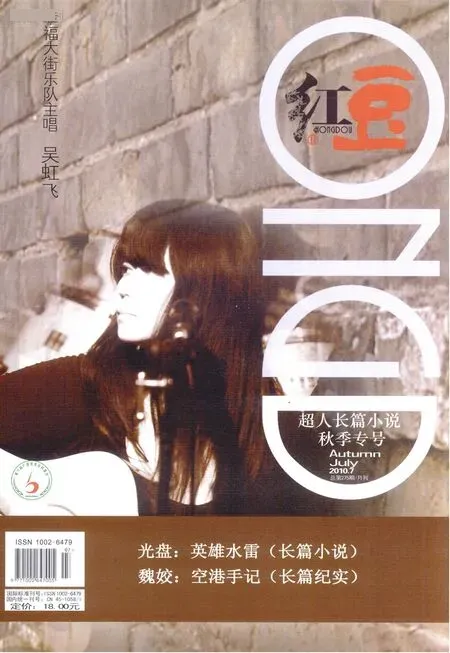狩獵時間

房偉
一
狩獵時間結(jié)束了。我在人工湖邊的水龍頭洗凈了手,撥打了110。幾小時后,警察來到,在湖里找到導(dǎo)師和高處長。他們詢問我發(fā)生的事。我簡單說了經(jīng)過,做了筆錄,簽上名字,離開了警局。這和我沒什么關(guān)系,我不過幫了導(dǎo)師點小忙罷了。
一個警察追出來對我說,不能離開學(xué)校,有事隨時要找我。
我答應(yīng)著,打了車,回到學(xué)校。陸陽是我的舍友,也是二年級的碩士生。我回到宿舍時,他一邊在電腦上修改論文,一邊拿手機打著《王者榮耀》游戲。他擺動著腦袋,眼珠亂動,好似一只剛學(xué)會互搏術(shù)的胖倉鼠,在枯燥的圖表、數(shù)字與電光火石的打斗之間,不斷切換場景。游戲有炫酷的戰(zhàn)甲和燃燒的長劍,無論是人,還是魔獸,都倒在他的劍下。
你沒事吧?陸陽停下手中活計,對我說。關(guān)我鳥事?我抖抖手,我能有啥事?但你畢竟在現(xiàn)場。陸陽似笑非笑,摸著下巴,沉思著說,而且死了人。這和我沒關(guān)系,我低下頭,說我只是幫著看看高處長出來的時間。你認識高處長?陸陽合上筆記本電腦,蹺著二郎腿,繼續(xù)問。不認識。我快速鉆到床上,不耐煩地說,警察都問過了,你是不是有病啊?可惜了。陸陽伸伸懶腰,說一個前途遠大的中年學(xué)者,也是咱們學(xué)校的新貴,你當(dāng)時看到他臉上的血了嗎?你可以救活他嗎?陸陽問。
我假裝睡覺,沒有回答問題。透過眼睛瞇起的縫隙,我看到陸陽脫下襪子,摳著腳丫,空氣中彌漫著新鮮的臭,點點黃色的液體從青黑色腳趾縫間漏出。他的手指甲也是青黑色的,充滿污垢,好似野熊長長的爪子。我的眼角充滿淚水,我使勁翻了個身。那天我太疲倦了,需要好好休息。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會想起宿舍那一幕,邋遢至極的桌上,擺著個易拉罐剪成的煙灰缸,煙灰缸里擠滿了烏黑的煙頭,電腦旁還有一袋吃剩的肉松面包。陸陽摳完腳,在衣服上蹭了蹭手,就去抓那面包……
去他媽的,骯臟的世界。我在心里咒罵,用被子蒙住頭,進入了沉沉黑暗。我需要黑暗,正如我需要休息。我要忘記一切,盡快回到正常軌道,我有四篇課程論文要應(yīng)付,要收拾行裝,準(zhǔn)備回河北老家過春節(jié)。我還有封電子情書要寫,我想發(fā)到她的微信里。收信人是個鵝蛋臉女生,長相一般,身材好,屁股翹,個子高大,符合我對床笫之歡的想象。
二
事情要從十幾天前說起。我的導(dǎo)師,管理學(xué)院楊修副教授找我談話。
我對他主攻的城市規(guī)劃管理學(xué)毫無興趣,對楊修本人也毫無興趣。我本科時成績不錯,但努力學(xué)習(xí),不過是不想就業(yè),或者說找不到什么像樣的職業(yè),來讀研混幾年罷了。我父母都是河北農(nóng)民,我不會討好那些當(dāng)紅教授,分導(dǎo)師時就被推給了楊修。除了學(xué)校安排的課程,我從不主動找他,他也不找我。我正好落得清閑,不像陸陽他們,天天幫導(dǎo)師查資料、畫設(shè)計圖,甚至干家務(wù),也沒啥報酬。
楊修五十多歲,矮胖,臉上流著油光光的汗,日益稀疏的頭頂像衰敗的荒原。他有一張大嘴,總是緊緊抿著,嘴唇咬在里面,從側(cè)面看就像一只扁口鯰魚。學(xué)生們傳言他是gay,專門對俊俏男生下手。我并不俊俏也不相信這些。我看到楊修上課時,偷偷瞟著漂亮女生。夏天來臨,他有意無意地拍拍女生裸露的胳膊。師母是S大團委書記,常將楊老師罵得狗血淋頭。我在楊修打電話時聽到過幾次。楊修漲紅了臉,訥訥不能言。楊修就是這副德性,但當(dāng)他用哀怨愁苦的眼神看著你時,還是會讓你不寒而栗。
我朝教學(xué)樓左邊走去。那棟老舊教學(xué)樓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建筑,中西合璧風(fēng)格,紅的墻,雕梁畫棟的重檐歇山頂,屋檐有彩釉怪獸,我叫不上名字。我站在樓下的榆葉梅下,等著導(dǎo)師的接見。北方的冬天,干冷,寒霜之下,灌木也落了葉,法國梧桐光禿禿的,焦黃的葉片趴在地上,榆樹和楊樹的枝條刺戟般伸向空中。我裹緊黑色羽絨服,跺著干硬的地面。天太冷,風(fēng)不大,小刀似的,白霜的地面凍得裂出幾道口子。血頭顱般的夕陽飄在天際,將大地涂上一層淡淡的紅。學(xué)期末,校園人不多,教學(xué)樓有時斷時續(xù)的誦讀英語的聲音,都是認真復(fù)習(xí),準(zhǔn)備考研究生的刻苦女生。工作太難找,我的幾個本科同學(xué)都在當(dāng)外賣小哥,還有一個賣廚衛(wèi)產(chǎn)品。這些也不關(guān)我的事。我在冷風(fēng)中呼著白氣,聞到教學(xué)樓內(nèi)自助奶茶機發(fā)出的溫?zé)崮滔阄丁R粋€戴著白色絨毛玩具帽、身材高挑的女生,正小口地飲啜奶茶,紅色短裙下,兩條白嫩的大腿晃動著,不時互相蹭一下。
闖禍了,還有心情看這些?一個陰冷的聲音響起。回頭看去,楊修冷冷地盯著我,嘴角帶著點古怪的笑。我趕緊喊老師好,那笑意逃掉了,好似一群被風(fēng)刮走的碎青石子。你闖禍了,楊修繼續(xù)強調(diào)。我做過什么?我目瞪口呆,口干舌燥。因為抄襲同學(xué)的課程論文,還是晚上在被窩偷看小黃片被舍友舉報了?我大腦混亂。楊修的表情卻愈發(fā)嚴肅,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想退學(xué)嗎?一個農(nóng)民家庭,供出個研究生容易嗎?怎么不懂珍惜?
我快崩潰了,不停撓著頭,指甲上沾著點血跡,露出了粉紅色頭皮。我哀求楊修,讓他不要折磨我,否則我瘋起來,對大家都不好。我?guī)缀觚b出了兇狠的獠牙,楊修這才不緊不慢地告訴我,論文代寫的生意東窗事發(fā),學(xué)校正在考慮處分我。
我真沒做……我囁嚅著,聲音越來越小,感覺喉嚨里藏著一只白色的蟲,它吞掉了我的聲音,讓嗓子癢得難耐。
讀書太清貧,偶然機會,我發(fā)現(xiàn)QQ空間有請人代寫論文的留言,抱著試試看的心態(tài),我接了一單。拼拼貼貼,外加規(guī)避論文查重,很快做好了。這對我來說是小菜一碟。拿到“第一桶金”,我又接了第二單、第三單。生意不錯,我建了一個微信群,陸續(xù)把幾個外系好友拉進來,甚至還有系里的青年教師。我寫得少了,主要負責(zé)轉(zhuǎn)包。一個學(xué)期,我凈賺了六萬。誰料好運剛開始,就遭到無情打擊。楊修說我代寫的論文,有的出了問題,被買論文的人告到了學(xué)校。校領(lǐng)導(dǎo)非常震怒,正考慮處分我。
三
沒有霧的冬天,也許不是好季節(jié)。
我開始了盯梢的生活。我放棄上課的時間、寫論文的時間、打游戲的時間、看黃片的時間,甚至犧牲了部分睡眠時間。我變成了世界可疑的游魂。我失去了自己的時間感。我穿著黑色羽絨服,戴著藍色毛線帽和白色口罩,手上也有厚厚的褐色絨手套。我徘徊在教學(xué)樓、職工公寓樓、學(xué)校酒店等地方。那幾天J市霧霾很濃,能見度低。灰色有毒物質(zhì),掩蓋了我的尷尬和沮喪。我盯梢的對象是社科處的高遠方處長。這是楊修給我的任務(wù),條件是幫我在學(xué)校開脫,免除處分。
我不明白,導(dǎo)師為何讓我干這事,他陰郁的眼神阻止了我的發(fā)問。我隱隱約約聽同學(xué)講過,高遠方和楊修是博士同門,高遠方一路春風(fēng)得意,很早升到教授博導(dǎo),在學(xué)界名氣很響,且出任學(xué)校社科處處長,有望成為下一屆副校長。相反我的導(dǎo)師楊修,一文不名,默默無聞,至今還是副教授。學(xué)期結(jié)束前,楊修再一次沖擊教授失敗,據(jù)說是他的高師兄使的絆子。高處長的“某學(xué)者”稱號剛公示,就被人舉報還在學(xué)生時代就有不當(dāng)言論,因此落選。高遠方懷疑是楊修所為,于是便阻止他升職。
我穿梭在嚴寒的校園,將自己融化在寒冬霧氣里。灰色的霧,有著毛茸茸的爪子,鉤著我的羽絨服,濕氣侵入內(nèi)衣和汗水混成一體,讓我越來越沉重。我艱難地移動,跟隨著高處長的軌跡。高處長每天早上七點準(zhǔn)時開著白色越野寶馬停在文科教學(xué)樓,然后快步走到主辦公樓,小跑上到三樓辦公室,開始一天緊張忙碌的工作。那是間寬敞的辦公室,不時有老師和學(xué)生進進出出。他有時在學(xué)校會議室開會,也去教育廳開會。如果看到他出校園,我就打車跟上,追隨他的步伐,好似癡情戀人苦苦追求著一個絕代佳人。下午下班,高處長開車回家,如果加班,就要延遲許久。楊修告訴我,記錄高處長的行程及他見過的人和遇到的事,打的費可以報銷。
高處長體格精壯,紅通通的鼻梁,挺拔俊朗,目光帶著一種譏誚的銳利,仿佛一只長著鮮紅長鼻的、強壯的幾內(nèi)亞狒狒。有一次,我站在辦公室旁,被他發(fā)現(xiàn)了。他把我當(dāng)成來申請創(chuàng)新項目的學(xué)生,叫我到樓下找楚老師。我的心狂跳,聞到他身上有一股薄荷味,應(yīng)是他抹在額頭提神用的。我躲在主樓旁的黑皮松樹下,用望遠鏡觀察他的辦公室。他讀文件,從身后的鐵柜取報刊。他大聲訓(xùn)斥下屬,與送文件的女助理調(diào)情,也畢恭畢敬地在電話里向領(lǐng)導(dǎo)匯報工作。沒人時,他蹺著腿,梳理毛發(fā),或啃著鉛筆沉思,將茶杯的每一片茶葉,都仔細噬咬,并一點點地吞下。他表現(xiàn)得很正常,沒有可疑之處。
高處長在高新區(qū)有別墅,但不常回去,周末偶爾光顧。他的妻子住在別墅,高處長大部分時間都回十五號教職工宿舍樓。那是棟老式電梯房,那天黃昏,我第一次尾隨高處長進入那棟樓。收發(fā)室的門房是一位面無表情的中年婦女。我默默地上樓,她默默地盯著我。她有著狹長的狐貍般的眼,眼神仿佛兩條銹跡斑斑的鐵鉤。我飛快盤算著如何應(yīng)對問話,可她始終沒有問我,只是目送我進入電梯。樓道間狹窄、潮濕、陰暗,堆滿廢紙殼等雜物,人只能側(cè)著身進入電梯間。那扇綠色電梯間外門有著各色涂鴉,間或不起眼的角落有捐精、替考等神秘小廣告。我閉上眼,鼻腔里有不知何處涌來的尿臊味,雜物霉味,各家各戶煮飯的味道。我按了十八層,閃爍的樓層號仿佛一只巨大的金屬心臟,伴隨著電梯門顫抖著緩緩合上又顫抖著上升,我就在這心臟之中被送往未知的宇宙空間……
電梯停下,我驚魂未定,踮著腳尖,來到1814房間旁。那扇黑色的門緊閉,有昏黃光亮透出,還傳出輕柔的鋼琴曲聲,打電話的聲音,人走動的腳步聲,廚房間灶臺點燃的聲響。高處長在做飯,我掏出一塊面包小心地吞咽。為了不被人發(fā)現(xiàn)我只能躲在人行樓梯通道。走廊燈是聲控的,有人來,我趕緊藏好,等住戶們窸窸窣窣地開門、關(guān)門,燈光就拋棄了我,我只能再次沉入黑暗。我貼著樓梯間墻壁,冰冷的感覺環(huán)繞著我,仿佛是一座深邃狹長的石墓。我看不清自己的手,只能打開手機電筒,尋找微弱的光芒。我站了兩個多小時,凍得麻木,那扇門還是緊閉。我跺跺腳,只見電梯間出現(xiàn)兩團黑乎乎的影子。是一對躲在暗處親熱的小情侶,看他們的校服,是S大附中的學(xué)生。擁抱著的情侶驚恐地看著我,似兩只柔弱的考拉。借著手機電筒光亮,我在他們稚嫩的眸子中,看到一個戴口罩的面目模糊的青年。那就是我,一個眼睛閃著餓狼般兇光的男人。情侶可能將我當(dāng)成盜賊或變態(tài)殺手。我再次看了眼高處長家的門,在情侶小獸般的尖叫聲中,飛快地順著樓梯間跑了下去。
我太疲倦了。連續(xù)五天,我持續(xù)對高處長盯梢,逐漸陷入幻覺狀態(tài):那件黑色羽絨服粘連在我的身體之上,蓬松溫暖的羽絨緊緊吸吮皮膚,化為粗硬的鬃毛。我的嗅覺越來越發(fā)達,視力增加,鼻孔變大,指甲鋒利無比。我熱愛長時間站立,沒緣由地奔跑……
放過我吧,我哀求著說,讓我干別的任何事都行,別讓我去盯梢,太熬人了,我撐不下去了……我哭泣著對著楊修作揖。我甚至不可察覺地諂媚地把手搭在楊修的胳膊上。他厭惡地甩掉我的手,說不要胡思亂想,幫我盯住他。再有七天,你只要再盯七天就好。楊修說。
臨走,楊修放下一個信封,里面有一千元錢,讓我補充體力,多買點好吃的。
四
我的行蹤越來越詭異。我原是一個開朗的大男孩,現(xiàn)在越來越憂郁。我不再和舍友一起打游戲,談?wù)摳黝惻恕N以绯鐾須w,沉默寡言,無聲無息地存在著,好似一只透明的蠕蟲。我快“消散”了。我必須在結(jié)束盯梢之前,保持健康,才能掙脫鎖鏈,順利拿到畢業(yè)證。
你好像變了。陸陽盯著我看了半天,喃喃地說。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陸陽掏出劣質(zhì)香煙,吞云吐霧地抽了半根,又繼續(xù)沉浸在游戲中。他發(fā)誓要在學(xué)期結(jié)束前,通關(guān)打爆幾個游戲。我不想管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了解我,我要保守秘密。我甚至懷疑,代寫論文的事是陸陽舉報的。當(dāng)初他也想加入我的論文組掙點錢,可我沒同意,我不想讓身邊的人參與這事,他極有可能惱羞成怒。他就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
在忙什么?陸陽問我,在圖書館寫論文?考博士嗎?找工作。我低聲地回應(yīng)他,我只想活得舒服點。
陸陽嘿嘿地笑著,轉(zhuǎn)動黑熊般壯碩的身體,靈活地轉(zhuǎn)動手指,繼續(xù)盯住游戲。
我適應(yīng)了盯梢生活。它讓我成為游魂,類似于剛剛脫離死亡肉體的陰身,讓我脫離束縛,進入自由境界。我和螞蟻聊天,與麻雀進行眼神交流,和兇猛的喜鵲對峙,在小雨中聽老槐樹上寂寞的野貓的歌。高處長參加聚會,我跟著他去酒店,默默記下和他吃飯的人的車牌號。高檔飯店前停滿高檔車,旁邊的小吃店卻很少有人光顧。為了迎接春節(jié),政府在經(jīng)三路翰林酒店后面搭出一條美食街,一個個紅色的、土氣的小棚里賣著各類年貨與小吃。天太冷,鮮有人光顧,小販在明亮的電燈下苦苦支撐著。一個瑟瑟發(fā)抖的女商販?zhǔn)刂久娼顢傋印K┲衩抟拢瑢⒛ν蓄^盔戴在頭上,手上還有一個暖手皮套。她的腳旁,趴著一只悲苦的、黑白花點的土狗。失去了溫暖的犬,在寒風(fēng)中靠長毛保存體溫,它將長長的嘴藏在毛里,露出兩只惶恐的眼,讓路人無法直視。醉醺醺的高處長走出酒店,叫了代駕。他似乎真醉了,咧著嘴,舌頭打著卷,嘰里咕嚕地罵著,比比畫畫,也不曉得在罵誰。
盯梢生活讓我體驗到孤狼狩獵的樂趣。我是“秘密”獵殺者。我越來越有耐心,還增長著一種殘忍心性,那是對人性陰暗面的鄙視。一個人的時空是被切割的,會呈現(xiàn)出不同面向,莊嚴肅穆與猥瑣無聊并存,光明正大與悲苦麻木共生。每個人都有無限小秘密,小秘密構(gòu)成無限細節(jié),進而構(gòu)成豐富立體的人,一個別人永遠也無法完全理解的人生。我不僅窺視到了高處長的隱私,也看到了很多人的秘密。翰林酒店,我偶遇和大款來開房的校花。大款像只肥胖的土撥鼠,開一輛黑色勞斯萊斯。校花姓王,長相清秀,行政管理專業(yè)的,碩士二年級的美女,也是我意淫的對象之一。土撥鼠將猥瑣的爪子放在王校花腰上。王校花面色紅暈,扭了扭屁股,不知是難受還是幸福。酒店輝煌的吊燈下,她仿佛一條裹著黏液的青蛇,嫵媚妖嬈,帶著滑膩手感。學(xué)校花圃,我看到神叨叨的,偷練氣功的陳教授。他早年畢業(yè)于北大,近十幾年來,醉心某種功法,嘴上說改了可還是偷著練。他閉著眼念念有詞,不斷擺著各種手印,花白的頭發(fā)在寒風(fēng)中飄蕩,非常滑稽,有點像樹精靈。經(jīng)過校園學(xué)生澡堂,年級的輔導(dǎo)員,一位以嚴肅著稱的禿頭老師正色瞇瞇地拿著望遠鏡,躲在草叢里向女澡堂方向認真巡視。他和我一樣是校園秘行者。高處長家門口,我也看到鬼鬼祟祟地來送禮的青年教師。他們爭取項目、評審職稱,都要取得高處長的支持。我默默記下這些教師的長相、車牌號。楊修這次非常滿意,他問我是否聽到高處長攻擊政府和社會的言論。楊修說,高遠方年輕時是憤世嫉俗的文藝青年,喜歡寫朦朧詩,給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提意見。我搖頭說,沒聽他講過。楊修多少有點失望,鼓勵我繼續(xù)站好最后幾天崗。
最后一天,楊修目光堅定地說,我會和你一起,見證歷史的時刻。
還有件事,我囁嚅著說,我說了,您不要生氣。
楊修呼吸急促,面色蒼白,臉上油汗更多了,鯰魚似的嘴癟著,一張一翕,口臭味讓人窒息。他輕輕咳嗽了幾聲,痛苦又帶著期待的神色問,關(guān)于我的家庭嗎?
我想了想,還是告訴了楊修。真相很殘忍,他大概也有所耳聞,因此不至過于痛苦。我很奇怪,楊修是個窩囊廢,師母是S大團委書記,中層領(lǐng)導(dǎo),比楊修小六歲,頗有幾分姿色,他們怎樣走到一起的?這里也有很多秘密。我盯梢的第十二天下午六點,在十五號教工宿舍樓旁的車庫,我看到了驚人的一幕。車庫是開發(fā)商后來建的,在小公園后面,那里有個人工湖,一片假山,還有茂盛的桃林。桃樹剛噴了大量白色液態(tài)膜和殺蟲劑,干硬的黑色枝干綁著一道道褐色草繩,防止它們在冬天被凍死。車庫價格不菲,大約七萬元,都被有錢的教師買走了。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規(guī)律。每隔幾天下班時,高處長就會把車開到車庫,在里面待上幾個小時,等到天黑后再回家去。
我仔細地觀察車庫,終于捕獲重要信息。車庫面積不小,里面有微弱的光透出。一個穿米色大衣、裹著藍頭巾、戴著黑墨鏡的女人,從車庫走出來。過了一會兒,高處長才溜溜達達地走出,朝家的方向走去。我恍然大悟,前幾次我看到高處長先出來,就跟著他回宿舍樓,卻沒想過車庫里還會有個女人。這次如果不是女人先走出,我還未能發(fā)現(xiàn)這個秘密。高處長很聰明,帶女人回宿舍樓總會遇到各種熟人,偏僻的車庫顯然較安全。女人是誰?我改變盯梢方向,將目標(biāo)轉(zhuǎn)移到女人身上。她身材高挑,穿著皮靴,步伐很快,腳掌鐵敲打著石子路,發(fā)出咔嗒咔嗒的聲音,好似灑在路面上的無數(shù)小鐵珠。她穿過桃林,繞過人工湖,在假山旁的小亭旁停下,擦著皮靴上的泥點。大概晚上七點半,四周無人,只有一盞路燈發(fā)著幽幽的光。女人看樣子并不害怕。剛下過一場冬雨,草根和泥土讓本就泥濘的小路更加骯臟。女人頭巾滑落的一瞬間,終于證實了我的猜測。那是我的師母,S大團委劉珂書記。她保養(yǎng)得很好,臉紅撲撲的,顯然剛經(jīng)歷了一場纏綿的愛情運動。她大衣掉下一顆黃銅紐扣,骨碌碌地滾到湖水中。她不理睬。昏黃的燈光下,她捋了捋頭發(fā),站直身體,好似一條剛躍出湖水的大青魚,散發(fā)著閃閃的鱗光。
五
最后的期限終于來臨。
我期待最后的時空點到來,莫名有些亢奮。楊修不斷地安撫我說,他會在學(xué)校會議力保我,讓學(xué)校撤銷處分我的決議,但這一切都要等下學(xué)期再說。只要拖上一段時間,他再去找相關(guān)領(lǐng)導(dǎo),事情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耽誤領(lǐng)畢業(yè)證。我對他的說法有所懷疑。楊修紅著臉脖子上的青筋聳動著說,你看不起我?我不比高遠方差,他不過是更能鉆營罷了。看到他這樣,我也只能相信他信誓旦旦的說法。
我越來越瘦削,動作愈發(fā)敏捷,我的血管變得粗大、凸起,顯現(xiàn)出青黑色的脈絡(luò)。睡覺時,我的磨牙聲甚至吵醒了舍友。我在洗手間藍色鏡子前,仔細觀察兩排牙,感覺它們越來越鋒利。我利索地將食堂醬大骨上的筋腱肉剔了個干凈,讓同學(xué)們目瞪口呆。
我必須配合楊修。我告訴楊修我看到的那些,他的表現(xiàn)過于平靜。那是一種反常的、瘆人的平靜。楊修擦著汗,不再喘粗氣,好似什么沉重的心思,終于塵埃落定。他拍了拍我說,我不會虧待你的。那天下午,楊修特意穿了墨綠色運動服,換了登山鞋。他拿了一根結(jié)實的棒球棍,不斷扭著身子,練習(xí)擊打準(zhǔn)確率。我聞到他身上散發(fā)出一陣河泥般的惡臭,那是鯰魚獨有的味道,也大概是失敗的齷齪氣息。他大概要捉奸,但依照高處長和楊修的體格而言,顯然楊修沒有什么勝算。我肯定不會參與他的行動,我只負責(zé)把風(fēng)。
我們躲在了假山的一片山石后面。
他戴了一副面具,塑料的、京劇花臉的臉譜,顯然是某些節(jié)慶的副產(chǎn)品。面具完全遮住楊修的頭發(fā)和上半臉,只有兩道細縫露出眼,眼神木然,仿佛也是面具的一部分,面具下露出他暗紅的、肥厚的鯰魚唇,以及嘴四周發(fā)灰的皮膚。他也給了我一副小丑面具,逼迫我戴上。這讓我很不舒服。我們仿佛不是去捉奸,而是準(zhǔn)備去搶銀行的兩個悍匪。我只是把風(fēng),我再次向他強調(diào)。是的,我不會連累你。楊修也強調(diào)。但我總是感覺似乎有著陷阱般的圈套。可事已至此,只能進行到底了。
冬陽好似一團冰冷水銀,白得亮眼,但缺乏熱情。空氣潮冷,剛下過小雨,時間一如雨勢懸停在半空,在沉默中凝固成空蒙的虛無。石頭假山也是冰冷的,有一股青苔般的苦味。我和楊修擠在假山臺階上,像誤入猴山的一只孤狼和一條鯰魚。我討厭他的氣味,卻不得不忍耐。從假山望去,湖水面積不小,湖面已結(jié)冰,一層薄薄的冰像煎餅般脆弱。湖心亭有一副對聯(lián),寫著校訓(xùn)“學(xué)高為師,身正為范”。湖中還有蘆葦和鳥類的蹤跡,是那種黑白相間的,肥大而兇猛的喜鵲。它們嘰嘰喳喳地叫著,絲毫不畏懼寒冬,堅硬的喙敲在冰面上,發(fā)出奇異的聲響。再往遠處,就是學(xué)校網(wǎng)球場,此時空空如也。越過了網(wǎng)球場,才能走到學(xué)校食堂和教學(xué)樓,最后到達那片紅色的學(xué)校外墻。
我的眼皮不停地跳動,有不好的預(yù)感。這些天我都在做一個怪夢,不能安睡。我夢到高處長的頭顱帶著鮮紅血跡滾落在我的腳邊,又怪笑著一路跑進湖水。我很想將這個夢告訴楊修,導(dǎo)師沒有理會我,而是專心致志地用望遠鏡看著車庫方向。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們等得焦急。我們終于看到那輛白色寶馬車。車庫電動鎖打開,車輛緩緩行駛進溫暖的后宮,卷簾門又緩緩放下,將我們隔絕在外面。棒球棍不停地顫抖。楊修瞇起眼,眼神在面具后面散發(fā)著駭人的光芒。
現(xiàn)在怎么辦?我問楊修。楊老師嘆口氣說,等等吧,等你師母出來,不要嚇到她。
現(xiàn)場捉奸是不可能了,楊修還是個慫貨。我們等了許久,天色慢慢黑了。太陽慘叫著閉了眼,徹底逃離了奸情現(xiàn)場。路燈慢慢亮了,車庫燈光也慢吞吞地亮著。我們終于等到師母靚麗的身影,出現(xiàn)在車庫旁。她還是穿著皮靴,邁著輕快步伐,走過人工湖和假山。楊修把我的頭壓得更低了一點。師母沒發(fā)現(xiàn)我們。
現(xiàn)在要沖過去嗎?我說,再不過去,他就走了。楊老師又嘆了口氣,說再等等吧。還要等多久?我問。楊修說,車庫門卷起,你把他叫到假山這邊,就說我要找他談?wù)劇?/p>
霧霾漸升起,遮蔽了湖面,眼前的一切變得模糊。我摘下面具,替楊修悲哀。從捉奸角度而言,充滿理性的楊修副教授還不如武大郎有血性。有什么好談的?難道要“相逢一笑泯恩仇”?看到楊修慢慢松弛下來的手、躲閃的眼,我明白了,他徹底慫了,想象中的暴力場景不會出現(xiàn)了。我走到車庫卷門前,輕輕地敲了敲。卷門緩緩升起,高處長充滿警惕地看著我。我講明來意,說我是楊修的學(xué)生,楊修讓他到假山那邊有事相商。高處長不斷冷笑,一邊系著大衣扣子一邊說,楊修現(xiàn)在膽子大了,敢出來找我談。
高處長拎起根撬棍,冷冷地對我說,你真的是楊修的學(xué)生?
我摘掉口罩,給他看了學(xué)生校園卡。他放松了一點,掂著撬棍說,量他也沒有那個雄心,敢找社會的人來暗算我。
我們走過桃林。他跟在我的后面,問這問那。這是我第二次近距離接觸高處長。我無法回答他,只能保持沉默。
就在假山那邊。我回答。耳邊傳來很遠的汽車鳴笛聲,驚醒了桃林里的鳥雀,發(fā)出驚恐尖叫聲。高處長停下不走。我只能再次強調(diào),楊修老師就在假山那邊,他相信你肯定敢去赴約。高處長挺了挺胸膛,捉住我的手腕和我肩并肩一起走,我們繞過人工湖來到了假山。楊修縮著脖子哈氣,沒有拿棒球棍,搖搖晃晃地從假山走下來。他還戴著面具,這讓他看起來更加滑稽。高處長丟下我,罵罵咧咧地迎上,看樣子要教訓(xùn)一下他。我看不真切,高處長突然停下,撬棍掉到地上。楊修好像熱情擁抱著他,高處長掙扎幾下沒有掙脫。楊修貼著他耳朵,像對他說悄悄話。我很好奇,走上前去,聞到了奇特的氣味。
霧漸漸散去了,掙脫楊修懷抱的高處長,踉踉蹌蹌地逃走了。借著路燈和月光,我看到我的導(dǎo)師楊修舉著一把閃亮的匕首,上面還有鮮紅的血液,滴答地流淌著。我不曉得他帶著匕首,只見過那根棒球棍。我嚇呆了,立住不動。楊修倒提匕首在月光下追殺,步伐從容,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高處長倒在人工湖邊,大口喘著氣。楊修越過我追到那里。他瞥了一眼掙扎的高處長,回頭對我笑了笑,用匕首抹了自己的喉管,縱身跳入湖水。那些薄薄的冰,被他砸得粉身碎骨,發(fā)出咔嚓的呻吟聲。隨之而來的是一陣沉淪的聲響,好似什么沉重貨物,或剛死去的大魚的掙扎,冒出一連串氣泡。楊修很快消失在水面。他還戴著那個滑稽的面具,至死也不肯摘下它……
我一聲不吭,戴上小丑面具。我湊近他的頭,小聲說,狩獵時間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做,只蹲在湖邊。我的牙根發(fā)癢,胸腔涌動狩獵的快感。這讓我難以自持,解開褲帶,對著湖水撒了一泡火辣辣的熱尿。高處長還在掙扎,動作越來越慢。月亮又白又亮,像一片被剝落的女孩的指甲。寒風(fēng)不小,刮走了霧霾和湖面溢出的血腥味,湖邊一個人沒有,假山也沒人,桃林也沒有人。我側(cè)耳聽聽,汽車鳴笛聲和驚起的鳥鳴聲也不見了,這片小小天地,仿佛世界末日后的地球,蠻荒而神秘。
六
整整一個寒假,我都在學(xué)校度過。我打電話給父母,說導(dǎo)師要求做研究模型,春節(jié)過后再回老家。學(xué)校食堂不開門,我偷偷買了電熱鍋,在宿舍涮羊肉吃。最近胃口特別好。我寫了兩篇課程論文,早上冒著嚴寒去操場跑步,不用盯梢,沒了威脅,我感覺輕松不少。
陸陽在宿舍賴著不走。他的家在本市,不用急著回去。他的碩士生導(dǎo)師就是高遠方處長。高處長是中層領(lǐng)導(dǎo),也在管院兼任碩導(dǎo)和博導(dǎo)。他常給陸陽布置任務(wù),陸陽很少能按時完成。還好他家境不錯,父母都是本市中層公務(wù)員,高處長沒難為他,但很多同門就慘了,極少有人按時畢業(yè),大部分延時畢業(yè)半年或一年。高處長死后,警察和校方聯(lián)合辦公,清理了高處長掛靠在學(xué)校的公司。高處長的很多科研經(jīng)費,都通過公司走賬,他在省里與市里接了規(guī)劃設(shè)計工程,讓學(xué)生們?nèi)プ觯瑢W(xué)生延期畢業(yè),是為更好地完成所接的工程。
你解放了很多人,陸陽半開玩笑地說,要不是你我現(xiàn)在還要做圖紙呢。高處長畢竟是你的導(dǎo)師,我沒有笑,說他的去世,是學(xué)術(shù)界的巨大損失。我想推薦你考他的博士呢,陸陽說,可你那個楊修導(dǎo)師與他結(jié)怨太深。我不想考博士,我搖頭說,我沒啥學(xué)術(shù)理想,又沒有天賦。別這么說,陸陽冷冷地說,你那些當(dāng)槍手寫的論文,有些還是不錯。我愣住了,趕緊換話題,說我也沒想到,楊老師能做出偏激的行為。
陸陽聳聳肩,不再和我討論。他總想和我討論那晚兩位導(dǎo)師斗毆致死的場景,我不會滿足他的好奇心。這些天,警察找我談過幾次,還到人工湖邊搞了模擬再現(xiàn)。學(xué)校匆匆忙忙給兩位教授舉行了葬禮,詢問我是否參加。我拒絕了。我甚至拒絕去太平間為法醫(yī)指認死亡創(chuàng)面。狩獵時間結(jié)束了,我不想再看到兩位導(dǎo)師布滿傷痕的肉體。我的師母,尊敬的劉珂書記,想請我吃頓飯,這我無法拒絕。
燈火輝煌的翰林酒店,師母請我吃自助西餐。牛排味道鮮美,還有法國紅酒和鵝肝,澳洲的龍蝦和豬肋排,泰式冬蔭湯和韓式烤肉,也符合我的食物審美。我從未到如此高檔的酒店吃飯,正好大快朵頤。她吃得很少,眼角還紅腫著,她的話很少。她問我當(dāng)天是否見過她,還了解什么。我老實回答說,那天沒見過師母,我對警察也是這么說的。我什么也不曉得,這些東西和我沒關(guān)系,我只是給導(dǎo)師幫點小忙。
師母點頭,掏出一張訓(xùn)誡意見,蓋著鮮紅的學(xué)校公章。我心驚肉跳,接過仔細看去,是學(xué)校對我的處理。鑒于我的悔過表現(xiàn),學(xué)校決定不開除我,也不給予留校察看處分,但要求管理學(xué)院內(nèi)部對我進行訓(xùn)誡談話。我心中一陣狂喜。師母也露出笑容,問我是否滿意。我表示感激。她又說楊修雖走了,但我是他的學(xué)生,就和她自己的學(xué)生一樣,我在學(xué)校有事,可以找她幫忙。
說完這些,師母說有事先走,讓我在這里慢慢吃。我咀嚼著羊骨,透過酒店藍色窗簾,看到師母優(yōu)雅地走向一輛紅色保時捷。她還是穿著那件米色大衣,風(fēng)度迷人。車門里鉆出一個高大男人忙不迭地為她撐開傘。我依稀認出,高大的男人,是學(xué)校的甄副校長。不知何時,紛紛揚揚的雪花,偷襲了這個城市。這美麗的裝飾物,讓我們忘記寒冷和不愉快的記憶。寒風(fēng)吹著陣陣細雪,吹過幾乎垂直的高樓大廈。縱橫的仿佛蛛網(wǎng)般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此刻也披著盛裝,仿佛化身為無邊無際的樅樹、桉樹和白皮松樹林。
這些東西和我沒什么關(guān)系。我要專心致志地對付那些美餐。我將在宿舍迎接美好的春節(jié)。我思忖著要準(zhǔn)備哪些燉火鍋食材,是否還要準(zhǔn)備彩色拉花。我還想邀請那位心儀的女生來宿舍吃飯。她的家也在本市。如果順利的話,也許我會結(jié)束處男生活,成為真正的男人。時間緊迫,易于破碎,我們都要抓緊。
責(zé)任編輯? ?丘曉蘭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