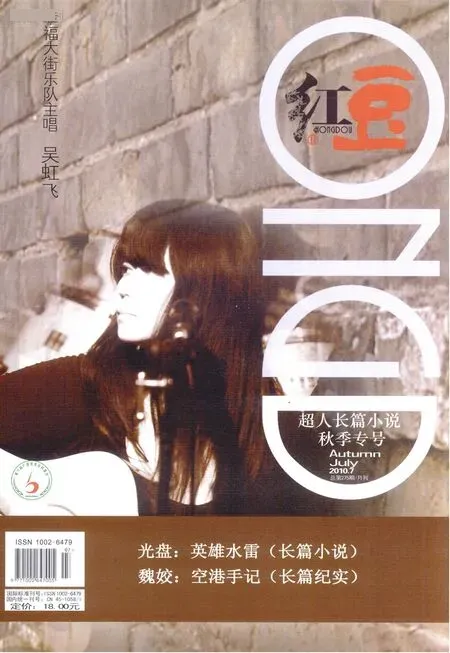個(gè)性獨(dú)異的萬物學(xué)與時(shí)光書
張德明
詩人吳少東的《吳少東詩選》較為生動(dòng)地體現(xiàn)著詩人所具有的生命觀、世界觀和詩學(xué)觀。作品中的“萬物的動(dòng)靜”之“動(dòng)靜”,是詩人對大千世界充滿生機(jī)和韻味的自然與人生的高度概括,而“萬物”則凸顯著詩人別具特色的詩學(xué)理解方式和審美表達(dá)路徑。詩人借助“萬物皆備于我”的自由化詩性思維,既能將世間的各種事物從容自如地納入書寫筆端,讓它們發(fā)生聯(lián)絡(luò)和關(guān)系,碰撞出詩意的火花和光焰,又能令人驚奇地呈現(xiàn)不同性狀事物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借助詩人的巧手點(diǎn)化,“萬物”在詩的文學(xué)空間里,常能奇跡般地集聚組合在一起,一點(diǎn)也不顯得隔閡和尷尬,也不顯得突兀和荒謬。
世界上的萬般事物,都是普遍聯(lián)系著的,這是馬克思、恩格斯辯證唯物主義的經(jīng)典哲學(xué)結(jié)論。正如恩格斯所說:“當(dāng)我們通過思維來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的精神活動(dòng)的時(shí)候,首先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lián)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交織起來的畫面。”也就是說,吳少東所秉持的“萬物關(guān)聯(lián)”思維,首先是一種世界觀和哲學(xué)意識,是遵循著辯證唯物主義哲學(xué)所主張的一種基本的理解世界的態(tài)度與方式。與此同時(shí),“萬物關(guān)聯(lián)”也是一種生態(tài)意識和生態(tài)精神。人類學(xué)家和控制論專家貝特森這樣指出,人類和其他生物以及非生物在最高層面上相互關(guān)聯(lián),共同生活在一個(gè)超級生態(tài)系統(tǒng)中。這段話強(qiáng)調(diào)的就是“萬物關(guān)聯(lián)”的生態(tài)學(xué)意義。在當(dāng)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生態(tài)詩已然成為一種顯在的詩歌形態(tài),吳少東所持有的“萬物關(guān)聯(lián)”理念,無疑是與當(dāng)下方興未艾的生態(tài)詩歌熱潮相合拍的。當(dāng)然“萬物關(guān)聯(lián)”的思想,更多的還是一種突出的詩性思維,是由詩性邏輯而促發(fā)的某種人文理念和情懷,因?yàn)樵姼鑴?chuàng)作向來就鐘情于“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嚴(yán)羽《滄浪詩話》),向來就鐘情于“精騖八極,心游萬仞”(陸機(jī)《文賦》),那種超常規(guī)的物象串接令人匪夷所思的時(shí)空穿越,一定程度上更能將詩歌表達(dá)“無理而妙”“韻味無垠”的美學(xué)優(yōu)點(diǎn)盡可能發(fā)揮出來。由此可見,吳少東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鮮明凸顯的“萬物學(xué)”精神征候,是哲學(xué)思維、生態(tài)思維和藝術(shù)思維三者合一的結(jié)果。這種綜合性精神質(zhì)素,賦予了吳少東詩歌開闊的情緒發(fā)散空間和自由的思維拓展路徑,確立了其詩作獨(dú)特的美學(xué)辨識度和個(gè)人化特色鮮明的藝術(shù)質(zhì)地。
在吳少東的詩歌中,“萬物關(guān)聯(lián)”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是豐富而多樣的,既體現(xiàn)為物物關(guān)聯(lián),也體現(xiàn)為物事關(guān)聯(lián),還體現(xiàn)為物人關(guān)聯(lián)。多樣化的關(guān)聯(lián)形式在他的詩歌中自如組合,不斷翻新,令人炫目的詩意光芒就在這些形態(tài)各異的組合與翻新之中不斷閃現(xiàn)出來。《烈日》一詩中,“斧子落下”與“光亮漏下”,“楊樹傾斜倒下”與“陽光轟然砸在地上”等,都可以視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在物理世界里,它們彼此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聯(lián)系,但在美學(xué)世界里,它們卻密切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因?yàn)樗鼈兂綄こ_壿嫷南嗷リP(guān)聯(lián),詩歌的美學(xué)趣味也得以彰顯出來,使詩歌的內(nèi)涵和意蘊(yùn)變得更加豐厚。
毫無疑問,展現(xiàn)物與人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是吳少東詩歌中體現(xiàn)“萬物關(guān)聯(lián)”的萬物學(xué)最為突出的書寫形態(tài)。如《緩慢的石榴》,進(jìn)入中年的詩人吳少東,對某種時(shí)間哲學(xué)有了獨(dú)特的體認(rèn),因此將緩慢生長的石榴引為同調(diào),對石榴“在暮春的高枝/點(diǎn)燃火焰”的遲緩式聲明方式的極力禮贊,這體現(xiàn)的正是詩人由青春年少成長為中年人的過程中,經(jīng)過長久的人生歷練與意義追問而形成的某種相對成熟的時(shí)間觀和生命觀。
吳少東詩歌所凸顯的萬事萬物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萬物學(xué),其讓事物之間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的方式也是各自不同的。有些時(shí)候,詩人采用了自然聯(lián)想的方式,在詩歌創(chuàng)作自由隨性、無跡而行的靈性化表述邏輯引導(dǎo)下,詩人發(fā)揮了善于聯(lián)想與想象的思維特長,由一種物象很自然過渡到另一事物,串接自如,毫無滯礙。“我當(dāng)然會(huì)分開最后一層薄紗/讓光線一下子涌入,那時(shí)/我已適應(yīng)這黑白漸變的世界/會(huì)帶著普照的陽光,看待/所有的樹木、人群與過往”(《晨起的慣性》)中敞現(xiàn)的“萬物關(guān)聯(lián)”都是由自然聯(lián)想而生成的。更多時(shí)候,吳少東展示“萬物關(guān)聯(lián)”的詩性言說,都是啟用了隱喻修辭,詩人借助不同事物在性質(zhì)或情態(tài)上所具有的某些相似性、類同性等特征而將它們彼此扭結(jié)串聯(lián)在一起,從而生成蔥蘢的詩意,如《快雪時(shí)晴帖》《通訊錄》等。
在獨(dú)特的萬物學(xué)詩性思維之外,吳少東詩歌中的另一特征也格外醒目,那就是對于時(shí)光的燭照與書寫。吳少東的許多詩歌,諸如《七月初的一天夜晚》《清晨》《晨起的慣性》《圓月高懸》等,標(biāo)題上都有明確的時(shí)間符號,從中便不難發(fā)現(xiàn)詩人對詩情生發(fā)的特定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的異常關(guān)注和格外重視。吳少東在那些時(shí)間線索特別明晰的篇章之中,時(shí)間在詩歌情緒散發(fā)和意義伸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各有差別的。
有些時(shí)候,時(shí)間構(gòu)成了詩人表達(dá)某種別樣情緒的特定氛圍,《七月初的一天夜晚》即如此:“此刻,城市上空,白云被燈火/燒得通紅,像一張隱忍的臉。/大雨初歇,暴漲的江水開始回落/像常發(fā)完脾氣的我。/沒頂?shù)氖R從皖南探出/半個(gè)身來”,這是該詩的最后一節(jié)。由此可以看出,“夜晚”這一事件符碼,在詩中充當(dāng)了物象呈現(xiàn)和意蘊(yùn)吐露的某種背景和氛圍,有“黑夜”作為背景,雨后城市富有情味的獨(dú)特景觀才被詩人生動(dòng)地勾畫出來。有些時(shí)候,時(shí)間構(gòu)成了詩人展示獨(dú)到的季節(jié)感知和生命領(lǐng)悟的光陰節(jié)點(diǎn),詩人將自我對特定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上的個(gè)人化感知和歷史記憶形象地表述出來,一定意義上構(gòu)成了詩人吳少東表達(dá)某種富有紛繁復(fù)雜的情緒與思想的歷史語境,昭示自己日漸平靜和成熟的中年心境的特定歷史語境。
詩人吳少東忠信的“萬物關(guān)聯(lián)”這一觀念,促使他將大千世界的紛繁物象自如地納入藝術(shù)的筆端,從而組構(gòu)成異彩紛呈的生命景觀和美學(xué)圖式。從某種層面上說,詩人所持的這種“萬物關(guān)聯(lián)”的萬物學(xué)認(rèn)知,其實(shí)是現(xiàn)實(shí)世界所具有的詩性秩序在詩歌文本中的具體反映。也就是說,“萬物關(guān)聯(lián)”的萬物學(xué)認(rèn)知一定意義上體現(xiàn)著詩人的空間意識,是詩人對所處世界的人文景觀和社會(huì)情態(tài)進(jìn)行的審美演繹。與此同時(shí),詩人對不同時(shí)間符碼所具有的外在特征與內(nèi)在意蘊(yùn)的藝術(shù)書寫,體現(xiàn)的毫無疑問是詩人的時(shí)間意識,是詩人對人生之中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時(shí)間刻度下具體而微的生活體味與情感投射的詩化呈現(xiàn)。
我們知道,時(shí)間和空間是構(gòu)成人類社會(huì)存在和發(fā)展的兩個(gè)重要維度。它們彼此關(guān)聯(lián)、相輔相成,共同編織起我們存在的場域和生命的經(jīng)緯。德國哲學(xué)家卡西爾曾指出:“空間和時(shí)間是一切實(shí)在與之相關(guān)聯(lián)的構(gòu)架,我們只有在空間和時(shí)間的條件下才能設(shè)想任何真實(shí)的事物。”這段話強(qiáng)調(diào)了時(shí)間與空間對人類生命理解與歷史建構(gòu)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吳少東詩歌中的萬物學(xué)與時(shí)光書,分別對應(yīng)著詩人的空間意識和時(shí)間意識,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從而將詩人真實(shí)的存在樣貌、精神境遇和生命情態(tài)藝術(shù)地呈現(xiàn)出來,其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和人文價(jià)值無疑是不可被低估的。
責(zé)任編輯? ?韋毓泉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