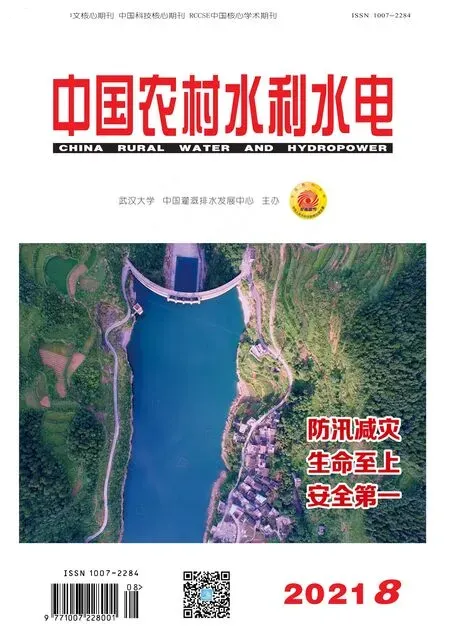運(yùn)用大尺寸涵洞解決被侵占的城市河道行洪問題數(shù)值研究
龍 藝,譚嗣城,潘龍陽,周宏偉,蔡君怡,王佳美
(1.四川省水利科學(xué)研究院,成都610072;2.四川大學(xué)水利水電學(xué)院,成都610065)
近年來,城市化進(jìn)程拓寬城市范圍的同時(shí)也侵占了城市河道原有的行洪區(qū)域,當(dāng)城市出現(xiàn)短歷時(shí)強(qiáng)降雨時(shí)很容易發(fā)生城市內(nèi)澇,給人們的生命安全、社會(huì)的正常發(fā)展帶來巨大危害。對(duì)于這類被侵占的河道,由于兩岸建筑林立,河道拓寬難度大,河岸加高又大大降低了原有河道景觀、親水效果,因此提高此類河道行洪能力困難,采用合理有效的工程方案提高河道的防洪能力、抵御汛期洪水已經(jīng)成為城市防洪的研究要點(diǎn)。
在以往的城市防洪過程中已有采用隧、管、涵等方式解決城市防洪的成功案例。孟慶佑等[1]結(jié)合城市內(nèi)河防洪防澇難點(diǎn)分析提出采用疏浚河道、使用堤防等方式提高防洪除澇的水平。黃福云[2]從城市排水系統(tǒng)在防洪治澇中發(fā)揮的作用入手,指出建設(shè)完善的城市排水管網(wǎng)對(duì)城市排澇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胡盈惠[3]、漢京超等[4]均對(duì)實(shí)際工程中排水管網(wǎng)提出了要求。耿曉明等[5]認(rèn)為吳江市防洪設(shè)施應(yīng)進(jìn)行通道疏浚、加強(qiáng)水信息化建設(shè)。黃繼新[6]結(jié)合蔥嶺溝實(shí)際情況通過技術(shù)經(jīng)濟(jì)必選確定隧洞排洪路線。劉家宏等[7]提出深邃排水系統(tǒng)可以有效分擔(dān)排洪任務(wù)。數(shù)值模擬作為一項(xiàng)重要的非工程手段,在城市防洪防澇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張曉波等[8]通過建立市政排水與區(qū)域排澇水動(dòng)力耦合模型,揭示了承泄區(qū)河道水位對(duì)城市排水系統(tǒng)中雨水管排水的頂托影響。張練等[9]基于InfoWorks ICM模型建立了地表及雨水管網(wǎng)模型,通過采用綠色屋面、下凹式綠地和滲透路面三種措施組合驗(yàn)證其在不同的降雨情況下對(duì)城市地表徑流的削減能力。劉斌玲[10]基于SWMM 模型和MIKE21 二維水動(dòng)力模型,通過構(gòu)建耦合模型對(duì)寶安中心片區(qū)進(jìn)行積水淹沒分析,提出利用地下空間解決防洪排澇的方法,探討了利用隧洞排水解決城市內(nèi)澇的可能性。夏海等[11]對(duì)深隧排水中的入流豎井的內(nèi)部流場(chǎng)進(jìn)行數(shù)值模擬,分析不同入口流速、效能管長度影響豎井內(nèi)部壓力場(chǎng)和速度場(chǎng)的變化規(guī)律及效能效率。
基于以上內(nèi)容,將工程設(shè)計(jì)與數(shù)值模型結(jié)合起來將對(duì)被侵占的城市河道治理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成都市錦江華陽段河道為研究對(duì)象,入流角選擇有限,構(gòu)建MIKE11、21 河道數(shù)值模型,選取分洪涵洞尺寸、入流角等關(guān)鍵因素研究分洪流量、流速、水位的變化規(guī)律,為被侵占的城市河道的治理提供決策依據(jù)。
1 研究對(duì)象
本工程河段為四川省成都市錦江華陽段,從天府大道錦江大橋至牧華路大橋,河段總長9.4 km。府南河道華陽段由于城市發(fā)展的需求,對(duì)河道侵占嚴(yán)重,且該河段蜿蜒曲折,最窄河寬僅為62 m,不能滿足行洪要求。由于城市發(fā)展,該河道目前已無法拓寬,且河段上游沒有可利用的調(diào)洪建筑物,河道下游有歷史古跡——二江寺古橋,無法拆除,河道上中下游均沒有分洪河流無法利用,且華陽地區(qū)暴雨洪水集中,錦江又是該地區(qū)雨洪唯一出口,洪澇問題突出。
傳統(tǒng)方式無法有效提升河道的行洪能力,本文提出使用大尺寸涵洞分洪的方案,根據(jù)河道沿程水位計(jì)算結(jié)果,二江寺古橋位置受橋梁影響上游出現(xiàn)明顯壅水,是導(dǎo)致上游行洪不暢的主要原因,因此將分洪涵洞出口設(shè)置在二江寺古橋下游,利用公共道路布設(shè)分洪涵洞將洪水直接引入下游河道,減少研究河段(包括二江寺古橋及上游附近)的洪量以降低河道水位,涵洞下游出口處河道寬闊,約為160 m。分洪涵洞入口設(shè)置于伏龍橋上游段,出口設(shè)置于二江寺古橋下游段,涵洞總長約為2.8 km,涵洞布置路線與河道現(xiàn)場(chǎng)情況如圖1所示。模型計(jì)算中,以錦江大橋位置為起點(diǎn),將河道按0.2 km 每段進(jìn)行斷面劃分。在與起點(diǎn)距離為0.9、2.37、4.09、4.55、6.11、7.35、8.12、8.65、9.32 km處依次為觀音灣大橋、伏龍橋、華龍橋、雙華橋、通濟(jì)橋、南湖大橋、江安河匯口、二江寺大橋、牧華路大橋。

圖1 涵洞布置路線圖和河道現(xiàn)場(chǎng)圖Fig.1 Culvert layout route map and channel site pictures
2 模型構(gòu)建
2.1 涵洞模型
本河段河長總計(jì)9.4 km,其中分洪涵洞涵身長度2.8 km,涵洞進(jìn)出口長度約200 m,模擬分洪涵洞總長度約為3 km。分別采用MIKE 11、MIKE 21 建立一維水動(dòng)力數(shù)值模型,進(jìn)行一二維數(shù)值模型的耦合計(jì)算,模型構(gòu)建構(gòu)建結(jié)果如圖2。

圖2 河道地形一維和二維水動(dòng)力模型Fig.2 One and two dimensional hydrodynamic model of channel topography
2.2 模擬工況設(shè)計(jì)
2.2.1 涵洞尺寸
涵洞寬度需要結(jié)合道路寬度設(shè)計(jì),高度以不影響公路通行為準(zhǔn)。經(jīng)實(shí)地測(cè)量,四河路機(jī)動(dòng)車道寬度15 m,非機(jī)動(dòng)車道寬度2.5 m,人行道寬度2 m,在不影響道路周邊建筑的情況下控制寬度最大為20 m。選取寬15~20 m、高6~8 m 進(jìn)行模型仿真。具體尺寸選取見表1。

表1 分洪涵洞斷面尺寸表Tab.1 Section size table of flood diversion culvert
2.2.2 入流角
現(xiàn)有研究表明,當(dāng)入水口與河道流向夾角趨近于30°~45°時(shí),其分流效果最佳;同時(shí)合理的入口位置也對(duì)分流效果產(chǎn)生重要影響。本次研究通過調(diào)整涵洞入口位置獲得不同的入流角度,具體情況如表2,各入口實(shí)際位置如圖3。

圖3 涵洞各入口位置Fig.3 Locations of culvert entrances

表2 涵洞入口位置方案Tab.2 Culvert entrance location schemes
2.2.3 洪水標(biāo)準(zhǔn)
本研究防洪標(biāo)準(zhǔn)分別采用20、100、200年一遇洪水標(biāo)準(zhǔn),江安河與錦江的洪峰疊加問題,原則上不考慮洪水傳播時(shí)間,認(rèn)為在設(shè)計(jì)情況下洪峰疊加情況為同頻率疊加,同時(shí)明確不考慮江安河對(duì)匯口上游錦江河道的頂托效應(yīng)。具體的洪水組合情況如表3。

表3 洪水工況表Tab.3 Flood condition table
3 計(jì)算結(jié)果分析
本研究通過一維水動(dòng)力模型計(jì)算河道水位及涵洞分洪量,通過二維水動(dòng)力模型計(jì)算涵洞入口流速及水位情況。
3.1 一維水動(dòng)力模型計(jì)算結(jié)果分析
涵洞入口位置從上游往下分別為樁號(hào)21+40、22+20、23+20,對(duì)應(yīng)入流角分別為12°、16°、33°,涵洞寬度分別為15、18、20 m,高度分別為6、8 m。選取涵洞尺寸、入流角作為影響因素分析涵洞分洪流量、分流比的變化情況。
3.1.1 分洪流量變化
圖4表示3 種入流角時(shí)各條件下涵洞分洪流量情況,可以看出:入流角為12°時(shí),分洪量最大為524.42 m3/s(200年,尺寸20×8),最小為249.47 m3/s(20年,尺寸15×6)。涵洞高度為6 m時(shí)分洪量在不同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相差6.4%,而當(dāng)涵洞高度為8 m 時(shí)相差20%,表明涵洞高度越大分洪量的波動(dòng)也越大。在涵洞高度不變、寬度增加時(shí),各工況下分洪量變化曲線均勻增加。同時(shí)考慮寬度和高度,對(duì)于20×6與15×8兩種尺寸,涵洞斷面面積相同,滿流時(shí)分洪流量相近;涵洞面積增大時(shí),其分洪流量也成比例增加,分洪量大小受斷面面積控制。入流角為16°、33°時(shí)分洪流量變化情況與12°相似,入流角為33°時(shí)分洪流量最大為584.88 m3/s,最小為260.37 m3/s,相較于前兩種方案,此時(shí)涵洞入口位位于方案2 下游100 m,其入流角更大,最大和最小分洪流量相較于前兩者分別有約11.5%和4.4%的提升,在其余條件相同時(shí),入流角是影響分洪流量的主要因素。入水口方案相同時(shí),來洪流量越大,涵洞的分洪流量越大。

圖4 各涵洞尺寸分洪流量變化情況Fig.4 Variation of flood discharge through culverts
入流角作為涵洞設(shè)計(jì)的重要參數(shù),選值的合理性對(duì)分洪效果至關(guān)重要。不同洪水標(biāo)準(zhǔn)各入流角對(duì)應(yīng)分洪流量變化情況如圖5,入流角為12°、16°時(shí)對(duì)分洪流量影響一致,且分洪流量幾乎相同。入流角為33°時(shí),在20年工況下,較前兩種方案的分洪量最大值分別提升了8.87%和10.3%,最小值分別提升了1.3%和2.5%;50年工況時(shí)對(duì)應(yīng)數(shù)值分別為12.1%和12.8%、5.9%和6.4%;100年工況時(shí)對(duì)應(yīng)數(shù)值分別為12.6%和13.2%、5.2%和5.6%;200年工況下對(duì)應(yīng)數(shù)值分別為13.5%和14.0%、6.5%和6.8%。

圖5 各入流角對(duì)應(yīng)分洪流量Fig.5 Flood diversion flow corresponding to each inlet angle
3.1.2 分流比變化
本研究定義涵洞分洪量與河道來洪量比值為分流比,作為分析涵洞分洪能力的重要參數(shù),為:

式中:Q涵為涵洞分洪量,m3/s;Q為主河道洪水流量,m3/s。根據(jù)計(jì)算結(jié)果得到各入口方案時(shí)分流比變化情況分別如圖6。

圖6 各洪水標(biāo)準(zhǔn)分流比變化情況圖Fig.6 Variation of split ratio of different standard flood
分析可知,涵洞情況相同時(shí),分流比隨著來洪量的增大而減小,20年一遇洪水時(shí)分流比最大,200年一遇洪水時(shí)分流比最小。在相同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涵洞高度越高分流比越大,對(duì)比20×6與15×8兩種尺寸,對(duì)于3種不同入流角,涵洞高度為8 m時(shí)的分流比均大于高度為6 m時(shí)。在所有工況中,2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入流角33°、涵洞尺寸為20×8 工況下獲得最大分流比0.362,該入流角對(duì)應(yīng)的最小分流比為0.149;2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涵洞尺寸15×6、入流角為12°和16°時(shí)分流比最小值均為0.139,該入流角對(duì)應(yīng)的最大分流比分別為0.357、0.353。涵洞入水口位置和斷面尺寸相同時(shí),來洪流量增大,涵洞的分流比下降,但33°入流角對(duì)應(yīng)的分流比均大于其他兩種方案。當(dāng)洪水標(biāo)準(zhǔn)較高時(shí),分洪涵洞已為滿流狀態(tài),其分洪流量隨水位增加提升較小,造成其值隨洪水標(biāo)準(zhǔn)增大而減小,故在滿流狀態(tài)下討論涵洞的分洪能力時(shí),不應(yīng)單純以分流比作為指標(biāo)考慮,而應(yīng)該綜合考慮河道來洪量,分洪流量大小等因素。
3.2 二維水動(dòng)力模型計(jì)算結(jié)果分析
基于一維計(jì)算分析,對(duì)20×8 尺寸的涵洞進(jìn)行二維計(jì)算,探究在該尺寸下河道、涵洞入口附近流速及水位的變化情況,同時(shí)與未加涵洞時(shí)的計(jì)算結(jié)果進(jìn)行對(duì)比。
3.2.1 河道水位變化情況
圖7表示了100年和2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河道水位沿程分布情況。結(jié)果表明涵洞分洪后河道水位明顯下降,且三種入流角度下河道水位下降幅度基本相似。1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時(shí),錦江大橋至觀音灣大橋段、通濟(jì)橋至南湖大橋段水位下降了約0.8 m,觀音灣大橋至雙華橋段水位下降了約1.4 m,最大處達(dá)到1.66 m(樁號(hào)22+20),南湖大橋至二江寺大橋段水位下降0.6~0.8 m;2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時(shí),錦江大橋至觀音灣大橋段、通濟(jì)橋至南湖大橋段水位下降約1 m,觀音灣大橋至雙華橋段水位下降了約1.5 m,最大處達(dá)到1.95 m(樁號(hào)22+20),南湖大橋至二江寺大橋段水位下降0.7~0.9 m。二江寺古橋附近壅水不明顯,下游水面寬闊(約為160 m),完全滿足行洪要求,水位變化不大。

圖7 河道水位沿程變化圖Fig.7 Variation chart of water level along the channel
由于涵洞的影響,3種方案下涵洞入口處水位均有所下降,100年工況下涵洞入口附近水位計(jì)算結(jié)果如圖8所示。入流角為12°時(shí),樁號(hào)19+66 至21+50 存在低水位段(較上下游存在約0.2 m 水位差),低水位段下游為分洪涵洞入口,最低處水位473.5 m,較上下游水位低了0.5 m,在河道彎曲段末端,流場(chǎng)變化劇烈,河道兩岸流速分別為3.6 和2.4 m/s,流速相差50%,流場(chǎng)變化較大。入流角為16°時(shí),涵洞入口范圍內(nèi)亦存在水位較低區(qū),但該段分區(qū)不明顯,僅存在約0.1 m 水位差,此處河道順直,橫向環(huán)流作用較小,兩岸流速分別為3.2 和2.6 m/s,涵洞分洪時(shí)河流流態(tài)穩(wěn)定。入流角為33°時(shí)涵洞入口處相較于前兩者存在較大水位波動(dòng),河岸左側(cè)較河岸右側(cè)存在0.2 m 水位差,涵洞入口上游水位均勻分布,當(dāng)流經(jīng)涵洞時(shí)流場(chǎng)發(fā)生急劇變化,河岸左側(cè)在分流的作用下迅速降低,右側(cè)由于河底高程升高水位迅速抬高,形成左低右高的趨勢(shì),流速左急右緩,流速大小相差約45%,水位不穩(wěn)定。

圖8 1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涵洞入口附近水位計(jì)算結(jié)果圖Fig.8 Calculation result of water level near culvert entrance under 100-year flood standard
3.2.2 流速分布情況
100年和200年工況下各方案涵洞入口處流速矢量分布計(jì)算結(jié)果分別如圖9~圖14。1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入流角為12°時(shí),主河道流速均勻,涵洞入口上游流速維持在3.2 m/s,下游急流區(qū)出現(xiàn)在河道左岸,流速約為2.4 m/s,緩流區(qū)出現(xiàn)在河道右岸,流速為1.6 m/s。涵洞入口處流速由3.2 m/s升高至5.6 m/s,水流方向從平行河道轉(zhuǎn)為向涵洞入口方向。入流角為16°時(shí),入口上游平均流速為3.0 m/s,經(jīng)過涵洞分洪后,河道主槽流速降至2 m/s,右岸伏龍橋橋墩上游50 m 處存在緩流區(qū),流速為1.5 m/s。涵洞入口處,流速從3 m/s 變化至5.5 m/s,水流流向從順直河道漸變至沿入流口方向。入流角為33°時(shí),涵洞上游段河道主槽流速為2.5 m/s,左岸流速3 m/s,右岸流速2.75 m/s,存在局部急流區(qū),涵洞下游存在緩流區(qū),流速為1.7 m/s。河道在涵洞入口斷面處存在河底高程迅速增高區(qū)域,主槽內(nèi)流速在涵洞入口斷面由2.5 m/s迅速下降至2.25 m/s,河底地形左低右高,河水存在由河道右岸往左岸流動(dòng)的趨勢(shì),在涵洞入口斷面靠近河岸右側(cè),主槽流速從2.25 m/s 下降至2 m/s,且該處存在明顯橫向流場(chǎng)。在200年工況下,該流態(tài)有加劇的趨勢(shì)。相較于方案1、2,方案3 中橫向流速變化大,同時(shí)在沿河道方向出現(xiàn)縱向流速急劇減小的現(xiàn)象,結(jié)合河底地形左低右高的特征,對(duì)主河道分流至涵洞有積極影響,認(rèn)為方案3 利于獲得更大分洪流量。涵洞下游出口處水流流速在3種不同工況下相近,分洪后,原河道左岸的緩流區(qū)成為了分洪涵洞泄洪區(qū),緩流區(qū)消失,并出現(xiàn)流速約3.2 m/s的順直流場(chǎng)區(qū)。分析認(rèn)為,分洪涵洞在二江寺橋下游泄洪產(chǎn)生了頂托作用,下游水位雍高,流速減緩,使原本流速較快的橋墩范圍內(nèi)的流速顯著降低,同時(shí)避免了古橋下游由于河寬增加、河底高程降低而導(dǎo)致的水位急劇下降、流速迅速升高而帶來的河底沖刷掏蝕問題。

圖9 1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方案1涵洞入口流速矢量分布圖Fig.9 Vector distribution of culvert inlet velocity under 100-year flood standard

圖10 1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方案2涵洞入口流速矢量分布圖Fig.10 Vector distribution of culvert inlet velocity under 100-year flood standard

圖11 1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方案3涵洞入口流速矢量分布圖Fig.11 Vector distribution of culvert inlet velocity under 100-year flood standard

圖12 2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方案1涵洞入口流速矢量分布圖Fig.12 Vector distribution of culvert inlet velocity under 200-year flood standard

圖13 2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方案2涵洞入口流速矢量分布圖Fig.13 Vector distribution of culvert inlet velocity under 200-year flood standard

圖14 200年洪水標(biāo)準(zhǔn)下方案3涵洞入口流速矢量分布圖Fig.14 Vector distribution of culvert inlet velocity under 200-year flood standard
4 結(jié) 論
本文基于MIKE11 和MIKE21 進(jìn)行一二維水動(dòng)力模型耦合計(jì)算,對(duì)成都錦江華陽段河道在不同涵洞布設(shè)方案時(shí)河道流速分布、水位變化情況進(jìn)行分析計(jì)算,并得到對(duì)應(yīng)的涵洞分洪流量及分流比,為錦江華陽段的行洪治理提供了設(shè)計(jì)基礎(chǔ),并為城市被侵占的河道治理提供了技術(shù)支撐和參考。計(jì)算結(jié)果表明。
(1)涵洞入口布置于彎曲河道末端較布置在順直河道處可獲得更大分洪量,但分洪效果提升不足1%,河道橫向作用力在分洪時(shí)影響并不明顯。
(2)本研究中選取3種入流角方案進(jìn)行分洪,結(jié)果表明在相同來洪流量時(shí),入流角越大,分洪流量越大,入流角為33°時(shí)的最大分洪量,較入流角12°、16°的最大分洪量提升了約13.5%和14%,最小分洪量提升了5.9%和6.4%;對(duì)于相同入流角度,來洪流量越大,涵洞分流比越小,但33°入流角對(duì)應(yīng)的涵洞分流比均大于其他兩種方案,最大分流比分別提升了約1.4%、2.5%,最小分流比分別提升了約7.2%、7.2%。
(3)涵洞分洪流量的大小主要受斷面面積控制,低洪水工況下,較大的涵洞寬度能獲得更好的分洪效果,在高洪水工況下,較大的涵洞高度能夠獲得更好的分洪效果,但高尺寸涵洞會(huì)導(dǎo)致涵洞入口處水位變化、涵洞內(nèi)分洪流量值波動(dòng)較大的問題。
(4)研究表明布設(shè)涵洞后河道沿程水位下降0.6~1.95 m,大尺寸涵洞可以用于提升侵占型城市河道行洪能力,發(fā)揮防洪減災(zāi)的。
(5)在樁號(hào)21+40、22+20處布設(shè)涵洞入口時(shí)水體流速均勻,入口上游流速穩(wěn)定均一,下游存在急流區(qū)和緩流區(qū),并存在局部回流;而在樁號(hào)23+20布設(shè)涵洞入口時(shí)流速變化劇烈,入口段斷面橫向存在流速急變區(qū),并隨著洪水標(biāo)準(zhǔn)增加有增大的趨勢(shì),結(jié)合河底地形左低右高的特征,此入口位置可以獲得更大的分洪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