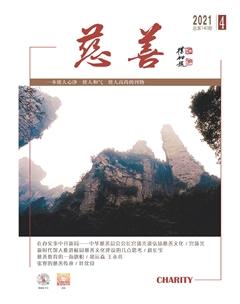蘑菇頭
黎子林
在儲木場小屋,我們日常的工作,一是歸楞,二是裝火車,其實在這是一碼事兒,就是抬木頭,或者說是抬蘑菇頭。“冬采夏流外帶蘑菇頭”,是林區人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意思是冬季采伐,夏天放排,還有抬木頭,這幾種活計最掙錢。至于為什么抬木頭又叫作蘑菇頭,那可能是因為抬木頭的人后脖頸上,會壓出一個暗紫色的肉疙瘩,大小如雞蛋而形似蘑菇。其實這些掙錢多的活計,在人們嘖嘖稱羨的背后,無一不是與危險和艱辛為伴,人們多是為了生活,才走上這條道路。然而諸如此類的利害得失,對于涉世不深的我們來說,當時還“不在話下”,就算“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也說不到錢上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才是那個時代青年人的精神風貌。不管怎么想的吧,總歸是抬木頭抬的,我們原本光滑的后脖梗子上,也壓出了厚實的蘑菇頭。于是,我們也能哼著低沉而雄壯的號子,身負重荷行走在高高的跳板上,成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隊伍的迅速成長,有賴于我們自己的努力,也得益于儲木場幾位工人師傅的悉心指導和傾力幫助。這幾位工人師傅,是親如兄長的錢鎬欽、姚守熙、石玉鵬和付世堯。
錢師傅是南方人,老家好像是無錫,身材不算魁梧但很結實,英氣勃發的,是個班組長。他告訴我們,抬木頭,不是人抬著木頭走,而是木頭牽著人走。這話聽起來似有哲理卻不合常理,不過以錢師傅“三鐵蘑菇頭”的江湖地位,他的話又不容置疑。這三鐵蘑菇頭的稱謂,可能是來自錢師傅姓名中的三個“金”字,也可能是蘑菇頭們對錢師傅這種硬漢的推崇,鐵肩、鐵腰和鐵腿,是為三鐵。將信將疑地按錢師傅的要求抬木頭,結果進步顯著,沒過多久我們抬起木頭來就像模像樣了。在林區還流傳這樣一句話,說是“小興安嶺的木頭嚇死人,大興安嶺的木頭壓死人”,看起來粗細長短差不多的木頭,大興安嶺的落葉松要比小興安嶺的紅松魚鱗松重得多。一聲“長(音,掌)腰”,抬起一根六米長三十幾個圓的落葉松,那感覺就是“剎肩”。木頭會隨著大家起身的動作,擺向身后,我們探身向前,把木頭拉回來,借助木頭前沖的力量,抬腳邁步。腳一落地,上身接著牽拉擺向后面的木頭,擺回來的木頭則又拉著我們的腿向前。如此周而復始,在旁人看來,人的上身前后擺動,腿的動作像是機器人,木頭則是一竄一竄的,像是安了引擎,拽都拽不住。如果木頭不這樣悠蕩起來,重壓之下,人是邁不動腿的,可不是木頭牽著人走嗎!哥八個抬著大木頭上楞,一個個挺胸收腹,臀部略翹,步履穩健,隨著姚師傅的一聲“撂”,齊齊地肩膀一松,放下木頭,各自抓上家伙什,返身下楞,那叫一個沙愣(利索),帥得像是舞蹈。抬上一氣兒木頭,吼上一通號子,感覺四體通透身心愉悅,似乎也算一種享受。
倘若錢師傅跟著自己的一幫兄弟干活,那可謂是配合默契隨心所欲,而調教我們這幫生荒子,言傳身教的,操心費力不說,自己還容易受傷。所以我對幾位師傅總是心存感激,師傅們有什么需要幫忙的,我也是盡力而為。一天,石玉鵬石師傅對我說,老錢的房子明天要動工了,想讓你帶幾個人過去幫個忙,能行吧?我自然是滿口答應,這是回報工人師傅的一個機會,在我心里早有這樣的期待,當然也是儲木場小屋弟兄們的心愿。
錢師傅的房子建在什么地方,已經完全不記得了,五十年前的事情,要是也能說得一清二楚,那肯定是胡扯。沒有被歲月磨平的印象,是林區蓋房子,更是像是搭積木,平地起屋,不打地基。建房子的木料早已備好了,七梁八柱的按不同用途作了標記。我們這些小工,主要是搬搬扛扛,協助大工們把木料裝配起來。建房的進度很快,傍天黑時,房架子已經搭好了,屋頂的魚鱗板也釘了大部分。收工回來的路上,石師傅告訴我,老錢的家屬要從關里來了。我不善攀談,只是應了一聲。你知道老錢為什么要把家屬接來,石師傅自問自答,因為阿龍山的水土好,很多在關里沒孩子的,到了這里就有了。還能這樣,我沒有吱聲,心想以后再碰到這種情況,就推薦這個方法,總好過燒香磕頭拜菩薩。不過開始是沒碰到對癥的,后來是自己也含糊了,不敢隨意建言誤人子嗣,所以這個治療不孕癥的偏方迄今未得驗證。
姚守熙姚師傅是山東人,身材高大魁梧,性情直率剛毅,他的女兒生病,還是我給她打的青鏈霉素,這些在“儲木場小屋的故事”里已有敘述,不再重復。付士堯付師傅,東北人,不愛說話,他大不了我們幾歲,能記起來的,是吃過他的結婚喜糖。還有石師傅,河北人,喜歡嘮嗑,這幾個人里他的歲數最大,是個忠厚長者。幾位師傅,來自天南地北,因為蘑菇頭的緣故而相知相惜。他們患難與共,互相幫襯,那兄弟般的情誼讓我感動。同樣是因為蘑菇頭,我們兵團戰士與林業工人的友誼,也是日益深厚,交往便多了起來。
一天晚上,我去石師傅家里喝酒。順便提一句,到阿龍山當地人家里喝酒,這是我僅有的一次。我的老家在河北定州,和石師傅算是同鄉。那時沒有地域歧視一說,大家都是革命群眾,不過老鄉見老鄉,還是覺得親切。東北人請客吃飯的習慣,女人和孩子是不上桌的,我沒看見孩子,就說讓嬸子一塊兒吃吧,于是炕桌上又加了一副碗筷。席間石師傅講了他的故事,大約是他的兄弟姐妹在關里如何了得,感覺那也是一個革命家庭。師母則小兄弟大兄弟地叫著,一個勁兒地勸酒勸菜。我心里高興,喝得有點兒多。吃罷飯告辭出來,石師傅要送,我沒讓。路過林業局的儲木場時,酒勁兒上來腳下不穩,我一下子滾進了絞盤機旁邊的道溝里。沒覺得疼也不覺得冷,只是心里想笑,還不由得笑出聲來。奈何困勁兒上來,眼睛想睜也睜不開。不知道躺了多久,倏地,一個不好的念頭閃過我的腦海,我可不想就這樣睡過去。我抓起一把雪擦在臉上,讓那冰冷的雪水使自己清醒些,隨后我站起身來,踉蹌而行。夜深人靜星斗闌干,周邊是黑魆魆的楞垛,眼前是模糊難辨的小徑,朝著儲木場小屋溫暖的燈光,搖搖晃晃地,我終于走了回來。
“事無不可對人言”,這里能對人言的其實都是好事,像喝酒過量險些凍斃這樣的糗事,我只能埋在心里。人們都說,酒品即人品。事后想來,所謂酒品好,大抵是自不量力來者不拒。果如此,酒品好的人,怕都凍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哪里還有什么人品!還能活著喝酒的,也還是好人多。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后來喝酒時,我也知道了量力而行適可而止,什么酒品好人品好,無非是浪得虛名。
這一節本來是說蘑菇頭,不知怎的,扯到了喝酒上去。抱歉,跑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