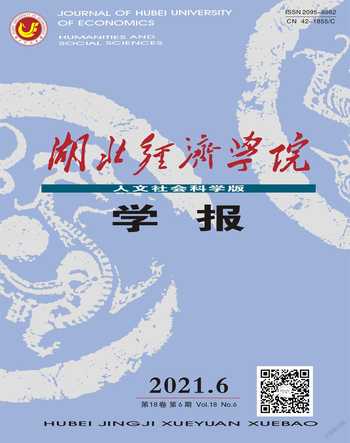淺析債權多重讓與的理論基礎
黃春虹
摘 要:在我國民法體系當中,作為動態財產關系的債權,被人們視為一種觀念上的物,債權讓與是債權人對該觀念之物進行的轉讓行為。迄今為止,關于債權讓與制度,民法界中形成了不同的基本理論及性質學說。該多重讓與行為被定性為準物權行為、合同行為、事實行為,并在不同性質下有各自理論基礎。德國、法國、日本,以及我國在債權多重讓與中基于不同的理論基礎,構建出不同性質的債權多重讓與制度。根據當前司法案例,我國存在債權多重讓與公示性不足,債權歸屬模糊等問題。以及為解決問題,債權人應當重視設立保證條款,嚴格要求合同形式等建議。
關鍵詞:債權多重讓與;債權讓與性質;基礎理論;物權變動
一、債權多重讓與的概述
(一)債權多重讓與的概念
債權多重讓與是指同一讓與人分別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受讓人將同一債權作出讓與的情形[1]。簡單地從概念上分析,債權多重讓與與物權的多重讓與都是對財物的讓與行為,對處理方式應該一樣,但因物權具有天然公示公信原則,不易發生多重讓與,即使發生,該公示方法也可明確物權的權利歸屬。相比之下,債權作為觀念之物,又不具公示方法,使得債權多次讓與的行為在市場經濟中屢見不鮮。
(二)債權多重讓與的構成要件
要解決債權多重讓與的問題,首先要對法律關系的構成要件了如指掌。在現行法律體系中,債權讓與的一般法律構成要件有三點:
第一,客觀存在的債權。當簽訂債權讓與合同后,一方當事人發現該債權在客觀事實上并不存在,或者該債權無效,此轉讓合同就會被認定無效。
第二,債權具有可轉讓性。對于轉讓性,我國法律上有明確規定,例如禁止轉讓的債權、合同性質上禁止轉讓的債權[2]。
第三,讓與合意。在簽訂一般合同之時,雙方應當表現出真實的債權讓與意思表示,且其合意不得存在瑕疵情形。如若出現虛假的讓與表示,將會導致合同無效或者撤銷。
除了以上構成要件,部分學者認為應當加上一點,就是讓與人對所轉讓債權具有處分權。但是筆者不完全贊同以上學者的觀點。例如票據等證券化債權的讓與。其與一般債權不同,具有獨特的外觀形式。權利的行使或讓與,都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的形式[3]。換句話來說有價證券擁有一種類似公示證明的能力。對此,德國民法也保持一致[4]。因此,筆者認為,對于是否應當具有處分權,我們應當根據債權的不同分類進行不同規定。對普通債權,構成要件應該包含處分權,但對于特殊債權,處分權就沒有必要作為硬性條件。
二、債權多重讓與的理論構成
(一)債權讓與的性質
在債權讓與制度中,不同區域,出現對同種讓與做出不同解釋的現象,主要源于各國對其定性不同,學者均堅持己見。也就是因為學者們的各抒己見,觀點的難以統一,致使債權讓與諸多法律問題存在爭議。因此要真正地深入了解債權讓與制度,就必須明確債權讓與的性質。
1. 準物權行為說
王澤鑒先生指出:“準物權行為,指以債權或無體財產權作為標的之處分行為,如債權或著作權的讓予、債務免除。”[5]雖說債權并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物,但是在中國普遍被認定為某種特定權利,準物權的一種。在對該特殊物進行處分時,就應當解釋為對準物權的處分。學者認為,對應當被視為轉讓行為對象的債權,進行的讓與行為,自然就如對物權進行處分一樣應被認定為準物權行為。
德國著名民法學家薩維尼先生創造了物權行為理論。該理論是將法律行為劃分成兩個種類。設立新債務關系的負擔行為,與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的處分行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出現準物權新概念,處分行為也就包含了準物權處分行為。
該理論的第二個原則就是第一個原則所區分出來的法律行為之間的關系,簡稱抽象原則(無因性)。具體內容:負擔行為的缺少、瑕疵不影響處分行為的效力[6]。當負擔行為因為欺詐、脅迫、顯失公平等瑕疵原因而導致合同無效,那么,根據抽象原則,將不會影響處分行為的效力。再用以上例子論述:甲乙之間房屋買賣合同生效后,也完成房子變更登記和交付。后如果基買賣合同有瑕疵而導致他們之間的買賣關系無效時,對房屋的處分是否要撤銷呢?根據抽象原則,乙對房屋權利不會受到影響。
該說的內容核心是將債權定性為準物權,那么自然應當產生于有準物權概念的國家。例如德國。對于我國來說,雖然不使用物權理論,但實際上有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區域劃分,承認準物權的合理性,使得少量學者支持該觀點。
2. 合同說
以法國代表的國家,否認物權行為理論的存在,在不對法律行為進行劃分的前提下,將債權讓與直接認定債權讓與合同。該行為不對二者進行區分,直接視為同一法律范疇,所以研究讓與行為就是研究其讓與合同。債權讓與合同是雙方當事人之間以意思自治為要素而訂立的,以債權為標的物的一種無名合同行為。
采取該學說,自然默認其隱含的物權變動模式。“債權意思主義”是債權讓與中債權歸屬的判定原則。因此,讓與合同簽訂后,合同立刻生效,債權也發生轉移,屬于受讓人。因為債權無公示方法。因此不討論債權是否有真正交付給受讓人,如果未交付,受讓人可用法律手段保護債權。
該學說觀點只存在采取債權意思主義理論的國家中。雖然該學說的債權歸屬及法律關系極其清晰,但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說,簽訂合約之后,權利就變動。當再次進行處分時,會因對已轉讓的債權無權,而使第二個合同無法律效力,最終難以解釋債權多重讓與的存在。
3. 事實行為說
同前面學說相比,該說法律邏輯思維更嚴謹與周密,其將讓與和讓與合同看作不同的概念。該說認為,債權讓與合同是雙方通過意思自治達成一致,設立新的債權債務,而債權讓與是指轉移債權的一個動態過程,也可以說是履行義務的方式。
例如說:甲有意將債權轉移至乙,他將實施了兩個行為,其一是訂立讓與合同。其二是交付行為。只有兩個行為都完成,才稱完成一次債權轉移。從中可知,債權讓與則被認定為是為履行基礎合同的法律義務,轉移債權的事實行為。
該“事實行為說”在效果上與“形式主義”為模式的物權變動非常相似。就是單純的簽訂債權讓與合同不會直接導致財產的轉移,標的只有經過公示方法才可以真正發生轉移。因此,有學者說:債權讓與中的事實行為說也被視為合同說與準物權行為說之折衷[7]。
(二)債權多重讓與的基礎理論分析
1. 德國于債權多重讓與的理論
德國在物權變動模式上采用“物權形式主義”。該模式強調的是,在物權被進行處分之后,應當對物做出轉移公示,才可認定物權發生變動。該模式又有人稱之為“處分行為加公示效力”。因此,就債權讓與來說,一個債權只有經過準物權處分行為,再加上債權交付的公示作用下,才可發生法律效力下的債權轉移。
上文已對德國的民法基礎理論進行論述,那么對于德國而言,債權讓與是何性質?就如王澤鑒老先生所說,對某些特殊權利的處分屬于準物權處分行為。所以,對德國民法而言,既然承認物權行為理論,那么債權讓與被視為準物權的處分行為也是無可厚非,自然就應采用準物權學說。
至于德國是如何運用民法基礎理論,將債權讓與視為準物權行為,并利用該學說解決多重讓與問題,下文將采用例子進行闡述。甲乙之間存在合法債權債務關系,甲為債權人人,后因甲與丙達成合意,將債權讓與丙。后甲又與丁簽訂讓與契約,多次處分后,根據德國的債權讓與性質,誰最終能得到債權呢?因為真正轉移債權的是甲的準物權處分行為,與債權讓與合同具有無因性,所以,不管甲訂立了多個債權讓與契約,均不會使債權轉移。而債權最終歸屬的一方就是甲最早進行準物權處分行為的一方。所以,在債權多重讓與中,對于沒有公示力的債權,以時間為標準,債權就歸屬最早訂立合同的乙方。其余的受讓人只能通過違約來追究讓與人的責任。如若其他人得到債權,那么法律權利人可以通過不當得利追回屬于自身的權益。
2. 法國于債權多重讓與的理論
法國在物權變動上采用以“債權意思主義”為核心的模式。該模式是在無物權行為理論下,表示合同行為意思一致,那么物權就發生權利的轉移。也就是說除了當事人意思表示外,物權變動無須其他要件,無須另行登記或者交付[8]。雖說該合同學說,在債權轉移上只需讓與合意,不需要登記,變動十分簡易。再來分析:甲將債權讓與乙,訂立債權轉移合同。合同一旦生效,甲的債權就立即轉移給乙,但該效力不能對抗第三人。比如說,債務人在沒有收到告知之前可以不履行義務,第三人也可對該債簽訂轉讓合同,因為對他們來說,債仍屬于讓與人。
因此,合意在雙方達成之后,沒有進行通知,債轉移只能產生于合同雙方之間,對他人不產生對抗作用。[9]因此也解釋債權多重讓與的現象的存在。所以,在法國民法基礎理論下選取“合同說”,面對債權人進行多次讓與合同時,采用“通知優先”的效力原則。多個合同中的哪一方受讓人在訂立合同后,進行了通知,就會對他人產生的對抗,得到債權。最后,取得債權之人可向他人請求履行義務,未取的他人應通過違約條款請求承擔責任。
3. 日本于債權多重讓與的理論
日本的多重讓與理論基礎是結合德國與法國,獨創出一派理論。首先,日本在物權變動模式的問題上,與法國得做法是一樣,選擇了“債權意思主義”模式。但是就從在債權讓與的問題上說,日本在“通知優先的”突破法國的做法,采取升級通知債務人的方式,對抗第三的人。告知債權人的方式有多種,效力不同。例如:口頭告知,郵箱告知,日期證書等。當發生債權多重讓與時,假若具有確定日期證書形式的通知或債務人承諾和普通狀態的通知或承諾都出現時。以日期證書的形式作出的債權讓與通知或者承諾都具有排他性的優先權[10]。
4. 我國關于債權多重讓與的理論
基于我國的法律現狀,我國所采用的民法理論與德國,法國均有不同之處。雖然說法律明確表示不采納物權行為理論,但是并非全盤否定,而只是不同意兩種行為之間的無因性。至于區分原則,我國的法律法規中表示認可,將法律行為區分為兩種,同時堅持它們之間有效力關聯性。在我國,如若債權行為因各種緣由被視為無效之時,物權處分是不會繼續生效,而是會因其合同無效隨之失去效力,簡稱行為之間的關聯性或有因性。舉個例子:甲與乙訂立一個手機買賣合同,甲將手機支付給乙,同時乙也交付了相應的款額,后期發現簽訂的合同是屬于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合同被判無效,那么甲對于手機的物權處分行為也視之為無效。可以通過不當的利等請求返還原物。除此之外,我國民法上學說上仍存在準物權的,對于特殊權利等,用準物權進行定義,所以,我國有少量學者堅持“準物權行為說”的觀點。但是該性質學說難以解釋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又利用準物權學說的沖突。
在認可該物權變動模式下,我國的諸多學者與法國持相反觀點,將債權讓與合同當成兩個法律問題。他們認為債權讓與是物權變動的一種形態,因此被認定為事實行為。所以,“事實行為說”在我國還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經過以上學說分析及我國的民法基本國情,筆者堅持采納“事實行為學說”。
基于我國民法的基礎理論下,我國立法上制定了一些關于債權規定。相對集中在《民法典》第545條至550條,除此之外,我國《擔保法》也出現了債權讓與。例如:《擔保法》第22條表明當債權轉讓后,除非有特殊情況的事實外,否則保證人只在原有范圍內承擔責任。擔保法》的司法解釋也有涉及。以上法條羅列有限,債權讓與制度內容又極其龐大,難以窮盡,例如,企業合并、清償代為等,因其原因發生的債權讓與并沒有明文的法律條文規定,一般直接適用合同權利轉讓相關規定。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總而言之,我國合同法只針對個別問題進行規定,但是,合同法卻無關于債權多重讓與時債權歸屬效力原則等規定。由此可見,我國的債權讓與制度在今后發展空間仍較大,應加快步伐完善該制度。
三、我國關于債權多重讓與制度的法律問題及完善
(一)我國關于債權多重讓與歸屬的司法實踐
1. 讓與時間在先,得債權
根據相關案例分析,有些法院的觀點:“債權只有一個,原債權人將債權轉讓給先受讓人后,其對債權即不再有處分權,即原債權人對債權的二次轉讓不能發生債權轉讓的效果。因此,在確定債權雙重轉讓的法律后果時,應當依照‘先來后到的規則確認。”
具體案例如下:
A. 王根旺與宋君、北京鑫暢路橋建設有限公司債權轉讓合同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2015)懷民(商)初字第02191號】、二審民事判決書【(2016)京03民終2737號】;
B. 彭楨與遂寧市茂園建材有限公司等債權轉讓合同糾紛上訴案二審民事判決書【(2017)川09民終347號】;
C. 東莞市順豐紙品制造有限公司、鶴山市卓越紙品包裝有限公司與東莞市天勝紙品有限公司、東莞市智森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一審民事判決書【(2013)江鶴法民二初字第474號判決】等。
2. 通知時間在先,得債權
如上,以時間在先的觀點:“對于債務人而言,債權轉讓對債務人發生效力應以通知為準,未經通知的,債權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法律效力。因此,如第一受讓人及轉讓人均未對債務人進行債權通知的,轉讓人又將同一債權轉讓給第二受讓人且進行了債權轉讓通知,則第一受讓人不能以其債權對抗第二受讓人。”
具體案例如下:
A. 李敬堂與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人民政府、蘇建華債權轉讓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5)東中法民二終字第972號】;
B. 閆麗與李柏桂債權轉讓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2016)蘇03民終字第272號】;
C. 方強與河南瑞田機械制造有限公司、河南瑞創通用機械制造有限公司債權轉讓合同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2018)豫0204民初1237號】等
因此,從實務見解的梳理可知,我國司法在處理債權多重讓與的歸屬問題上,仍存在不確定性。接下來,筆者將進行分析與建議。
(二)我國債權多重讓與制度存在的問題
1. 債權多重讓與中公示性不足
經過以上分析,就可知道我國在物權進行處分過程中,物權轉移是憑借物權擁有完整的公示原則。債權雖然在觀念上可以作為一個“物”,但是其與構成物權客體的有體物有較大的區別。在物權變動方面,一般是采用交付與登記來作為標志,只有這樣,他人才可知悉到物已經轉移的法律事實。
而債權說白了就是一種觀念物,無任何公示方式加護自身,其緣由在于債權讓與行為的內部效力及外部效力。內部效力體現在讓與人與受讓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自治。而就外部效力而言,是指告知債務人,才能對第三人產生對抗。外部效力并非是真正法律意義上的公示公信力,該效力并不表明債務人具有對其他第三人說明該債權已經被轉移的事實的義務,如果說有義務,也只是道德義務。故而該外部效力也并非能從根本上取到債權讓與對外的公示作用。[11]對于公示性極弱的前提下,增強債權讓與的公示性,將會引起大幅度降低多重讓與的發生率。
2. 債權多重讓與中的債權歸屬原則
從我國民法理論來分析,可知我國學者對債權讓與的性質采用“準物權行為說”與“事實行為說”。按照這兩種學說的觀點,債權在被視為準物權時處分給了第一個受讓人。或者是為了履行合同義務,將債權處分給他人。該兩種學說均是采用“形式主義”模式,將債權當成物權法中之“物”進行處分。
本應在交付或登記的公示下才可有轉移之效,但因債權實際上沒有像物權擁有明確公示方法,因此當債權讓與給在先受讓人時,讓與人就失去權利了,至于之后的讓與人再次進行讓與行為,應當定性為無權處分。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在得不到相關人的追認時,對無權處分,應自始視為無效。
根據以上我國在司法實踐案件,可知我國不僅采取“時間優先”,也采取“通知優先”模式,其中不具有確定性。因此,確立債權多重讓與的歸屬原是處理該制度問題的重要步驟,也是保障受讓方權利的重要一環。
(三)完善債權多重讓制度的建議
經分析,我國在該體制仍然不完善,還有較大的完善空間。因此,筆者提出想法與建議:
1. 嚴格要求債權讓與合同形式
中國合同法規定,訂立合同可采取任意形式,無嚴格要求。例如:口頭形式,書面形式,公證形式等。合同的諸多形式是為了市場經濟發展,但是針對債權轉讓合同,一味追求合同形式的多樣化并非明智之舉。讓與人進行多重讓與就是為了擴大自身利益的,此時口頭等非嚴格形式的方式將會導致讓與人的肆無忌憚,只有書面或公證等嚴格形式的合同,才會更好地保障善意的受讓人。如果只是口頭合同的話,一味追求利益的讓與人很有可能直接不承認債權已讓與,并實施再次讓與行為。更通俗說,當得不到債權的受讓人苦苦尋找曾訂立生效合同的證據來保護自身權利,還不如提前預防。
對于未取得債權人來說,一個嚴格形式的合同相對一個任意形式的合同,保障權益的幾率高很多。因此,在中國債權讓與制度中,筆者認為法律規定的債權合同形式,應當將解釋必須采用書面,公證,登記等嚴格的制定形式,以此來規避多重讓與。
2. 設立債權人保證條款
訂立債權讓與合同中,讓與人應向當事人保證其內容,或者標的是無瑕疵的,又或重新訂立新的保證合同等等。有該保證條款下,即使我國采取不承認物權行為理論,那么也會增加債權人履行法律義務的自覺性。相比以德國為代表的國家來說,因處分行為與負擔行為具有無因性,債權讓與又被視為準物權行為,那就不需要在雙方訂立合時增設債權保證條款以保證債權的實現。換句話說,正因為中國沒有認可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無因性,才需要在負擔行為中增加保證條款,以促使當事人實現轉移合同的法律效果。
因此,在簽訂讓與合同時,增設保證條款不僅會督促義務方履行職責,也可在讓與人違約時,提供被違約方權利得到保障的機會。
3. 明確債權歸屬效力原則
迄今法律界對債權多重讓與效力規則學說有三種。不同規則的價值取向、保護方向,必然產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要明確采取哪種債權歸屬效力原則,要正視我國關于債權讓與的基本國情。
就如之前關于我國的物權形式變動模式所言,我國的物權變動均要經過公示效力的作用下,才屬于真正的轉移,如果沒有設立相應的公示效力原則,債權就因為被認定為觀念的物而在訂立合同后發生轉移,不就同債權意思主義相一致了嗎?因此明確解釋債權歸屬的效力公示原則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在我國的物權變動模式下,我們可以通過法條解釋債權的公示方法,最終確立債權的效力原則。例如從法律條文中關于債務人通知,我們可以解釋為是對抗他人的要件,也可以解釋為變動或者歸屬的條件。當合意在先的,無對債務人進行告知轉讓事實,而在后的當事人實施了通知,此時,我們就應該解釋為后受讓人在法律效果上得到了此債權。按照此規則,我們可以得知,得到不到債務人履行的一方,可以以違約賠償向讓與人求償[12]。
因此,筆者認為:對于債權效力原則要區分普通債權讓與和特殊債權讓與[13]。對于特殊債權讓與,我們應當采用登記或者占有的公示方法來確定債權的歸屬狀態,對于普通的債權,則可以直接采用通知的形式,來確立債權的效力歸屬。因我國的國情復雜,并沒在法律上確定規則。因此,在已有成熟規則中選取適合我國并在法律條文中確立下來是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 羅頂.債權多重讓與的效力分析[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3.
[2] 尹飛.論債權讓與中債權轉移的依據[J].法學家,2015,(4):81-94.
[3] 鐘薇.債權多重讓與法律問題研究[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4.
[4] 陳衛佐譯注.德國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40-145.
[5] 王澤鑒.民法總則[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263-254.
[6] 賈同樂.物權變動中交易安全的保護[D].吉林:吉林大學,2013.
[7] 周小鋒.定位債權讓與之性質[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9,(1):153-159.
[8] 李宇.債權讓與的優先順序與公示制度[J].法學研究,2012,(6):98-118
[9] Pothier,RJ.Treatise on the contract of sale[J].Leslie B. Adams,Jr.1988:333-334.
[10] 王文娟.論債權多重讓與下的權利歸屬[D].河北:河北經貿大學,2017.
[11] 王勤勞.債權讓與制度研究[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2.
[12] 王政.債權讓與論——以比較法為視角[D].河南:鄭州大學,2012.
[13] 虞政平,陳辛迪.商事債權融資對債權讓與通知制度的沖擊[J].政法論叢,2019,(3):8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