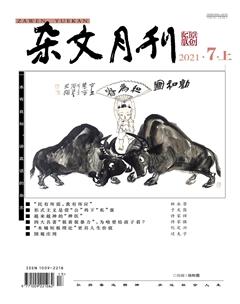“腸”“柿”定律
伍里川
到一家時尚快餐店點餐,饞蟲攪肚,點了一份肉圓子套餐,吃了就后悔,因為所謂的肉圓子吃起來是一種工業肉圓的味道——就像方便面那種味道,這么說,看官您就清楚了。
這種點了肉圓就后悔的事,基本上幾年里要發生一兩次。雖然打小就聽從大人的勸諭,自覺遠離“外面的肉圓”,但在極少數情況下,還是會有“偷食”的欲望。
我有肉圓情結,打小喜歡吃媽媽做的肉圓。時間在改變,肉圓子也在改變。今天的豬肉和往昔的豬肉不可同日而語,炸出來的肉圓子在鮮度上也就有了很大的區別,就算仍由媽媽親手做,也不能“昔日重來”了。但鮮度事小,安全事大。不僅媒體報道過“爛肉”做肉餡、炸圓子的事,我也多次見識過肉圓里的淋巴結等異物。這些來路可疑的肉圓子,滿寫著“我不是好東西”,令人愕然,令人生氣,令人后怕。
同樣的問題,還體現于香腸。幾天前,在一家生意很好的面館,點了一份招牌“九鮮面”——本地多的是六鮮面、八鮮面、九鮮面,這大概是一種“軍備競賽”的結果。我小的時候,只吃過三鮮面。所謂三鮮面,也就是香腸面的升級版,在香腸之外,加些肉絲、香菇之類。當時“嘆為觀止”,不想此后竟成了“小兒科”。好在這種數字上的升級有盡頭。當然,要是弄個“十鮮面”出來,咱也管不著人家。而無論“鮮面”如何發揚壯大,面條里照例是有香腸片片的,我又做不到次次都“照會”掌柜,請求不放入香腸,所以經常被面條里的香腸壞了心情。
這么說,好像是我這個人難講話。其實真不是這樣,我是被那些淀粉多于肉的“淀粉腸”和淋巴結、肉筋神出鬼沒的“鬼魅腸”整怕了。
我一個人的體驗當然不能說明問題,但媒體上,揭發香腸問題的報道,同樣可以用以印證我們共有的擔憂。
那天,我用筷子把那碗“九鮮面”里一堆香腸片全部挑出來。我還真的嘗了一下,滿滿的淀粉味和甜膩味,而我又一次看見了淋巴狀物。這個過程中,坐我前面的小孩子帶著驚訝的神情看著我。我覺得我不能暗示再多了。
我寫了幾句話,發在朋友圈,引來幾位朋友的共鳴。
我并不能說市面上所有的肉圓子、所有面條里的香腸都有問題,但作為個體,遭遇到它們的概率,的確在增加。這令人沮喪不安。
由于當時憤然而去,忘記留下證據,更沒有投訴給有關方面。只“晾曬”,不“維權”,可能是一種怯懦,這是需要檢討的地方。但我更想說的是,當這類“居心叵測”的肉圓子、香腸頻頻現世又很難得到一種強力的遏制時,個體的“抗爭”事實上是無力的。無疑,由于缺乏足夠力量的支撐和馳援,集體的沉默是經常發生的事實。
這些在市井里存在感十分微弱的懷疑、憤懣和失望,多數時候,喑啞在市井的角落里。但這種印象,以及由此生發的勸諭、自我提示,匯集成特別的經驗,包括適用于個體避險的“定律”——例如,我對它們就形成了“拒之口外”的條件反射,除非憨厚之人拿出證據證明肉圓子和香腸是自制的放心之物,我才會動一動嘴。這樣的“歧視”肯定有不當之處,但為了肚腑之安,也只能這樣謹小慎微了。
世上食材萬千,總有些不爭氣的家伙成為我檢驗餐飲店良心的“試紙”。肉圓子和香腸是這樣的“試紙”,西紅柿亦然。
西紅柿在我的鄉間記憶里,是美味之物,也是謙和君子。童年時,吃不起水果,常以價錢便宜的西紅柿“代果”,食之愜意。而我那時就知道,西紅柿易變質,不易存放。而變質后的西紅柿,有股特有的餿味,或淡或濃,一吃就能吃出來。即使是果皮磕破,味道也會異變,這就是西紅柿的“品質自保”:爛了就是爛了,不可能后天“修復”。比之通過種種“人工修復術”就能變成“美味”的變質肉,可謂高下立現。
正是這一點幫助了我。在店家吃飯,西紅柿炒雞蛋也好,西紅柿燴蛋湯也罷,只要西紅柿味道不對,我就能對此店的“厚道指數”有所了解,就此拉黑。有些店或許是偶一為之,但我從一些面館經常吃到壞西紅柿,足以證明,某些人做的是一種壞良心的生意。無非是專門買那些便宜的次品省些銀子罷了。這種成本節約法,也揭示了某些西紅柿賣家的貪婪無德。
說到底,食物本無“罪”。有“罪”的是那些扛著問題食品在世間作惡者。悲哀的是,很多時候,我們對他們無可奈何。是以有個幻想:天下的“爛肉”都如西紅柿一般,爛了就是爛了,任爾萬般“修復”,也難消“爛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