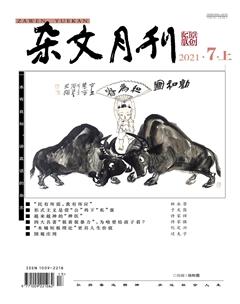開花,是展示自己的最好方式
草戊
清明節后的一天上午,我到我所居住的單元樓南側一塊空閑地帶閑逛。嗬!四五天沒過來,地上竟多了一道風景:櫻花樹下,冬青樹旁,雜草叢中,仿佛一夜之間,呼哧一下子冒出一朵朵、一片片的薺菜花,嬌小玲瓏,潔白如練,生機勃勃。
我被這些密集開放的薺菜花驚呆了,很想問上一聲:薺菜,你們前些日子,特別在冬季寒冷的日子里,都去了哪兒?我知道,薺菜們如果能聽懂我的發問,它們會十分爽快地作答:我們哪兒也沒去,一直就待在這兒——嚴冬,萬木凋零,我們與枯萎的野草一個顏色,匍匐在地上,你們人類不會注意我們;春寒料峭時,我們與野草一起復蘇,返青速度比不上對方,你們人類也不會首先發現我們;只有到了春光明媚的季節,碰上一場春雨,我們興高采烈,像急著趕赴一場盛會一樣,甩開膀子,開足馬力,披著綠葉,抽出花莖,爭先恐后地抽穗揚花。
地球上的植物,目前已經知道的有80多萬種,其中綠色開花的有20多萬種。我很想知道然而又無從知曉這20多萬種開花的植物中含不含薺菜。不過薺菜屬于野菜,日常入不了菜圃,也進不了《花譜》。它一直以來與雜草相伴相生,那些委身山口、崖畔、屋角、路邊、小溪旁、瓦礫堆里的薺菜們更可憐,未開花時,絲毫引不起人們的注意。
古人對薺菜的關注和情感,似乎要強于今人。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里將薺菜釋名“護生草”,告訴人們薺菜有清肝明目、利尿消腫之效。晉人夏侯諶在《薺賦》中,用“鉆重冰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舍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贊揚了薺菜不畏嚴寒堅冰的頑強生命力。南宋陸游在《食薺》中向人們推薦了吃薺菜時“小著鹽醯和滋味,微加姜桂助精神”的操作技巧。唐代高力士的那首《感巫州薺菜》,僅有“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都不改”四句二十字,可謂文字直白,釋義淺顯。不過,它名為詠物,實為抒情——寫的是薺菜,抒發的卻是自己坎坷經歷和那份對君王忠貞不二心的感情。作為宦官,高力士的這首詩,得到了宋朝大文豪黃庭堅的肯定,以這樣的文字功底,這樣的文采,也當得起李白的脫靴人了。而南宋辛棄疾的《鷓鴣天·代人賦》中的“春在溪頭薺菜花”,至今還被人們當作金句,傳承、使用著。
人類的許多思想感情和處世之道,與樹木花草有得一比:縱然你有志,有才,可當初,在你還沒嶄露頭角的時候,你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此時的你,是條龍,也要先盤著;在你還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時,除了楊萬里同志,你不會有多少觀眾和粉絲。這時候,你要穩住自己,繼續豐盈自己,逐漸把自己做大做強。
上世紀70年代末,我朋友農村老家的一個小學時的同學Z某,全家從當年逃荒的關東回到村里,一家兩代男女7口,借住在生產隊兩間不足40平方米的破舊屋子里,兄弟5個,都老大不小了,沒有一個娶上媳婦的,日子過得低于全村的平均水平。可這家人能吃苦,肯出力,一直咬緊牙渡難關,日子逐漸有了起色,兄弟5人,陸陸續續成了家。90年代,全村幾百戶人家連著幾年都考不上一個大學生。可Z家從90年代后期開始,連著走出3個大學生,有的還是被985名校錄取的。這下子,Z家聲名鵲起,令全村人刮目相看。
事情古今皆然。當年,白居易初到長安,被顧況嘲笑“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待展示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又被連連稱贊:“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金末元初的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元好問,雖7歲能詩,可16歲之前,名氣畢竟寥寥;16歲時,他在《摸魚兒·雁丘詞》中,寫出了“問世間,情為何物”的名句,就憑這千古第一問,將愛情這一人間至味言說得哀婉纏綿,蕩氣回腸,由是他名氣飆升,成了網紅,“天下誰人不識君”!
所以,還得信那句老話:你若盛開,蝴蝶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