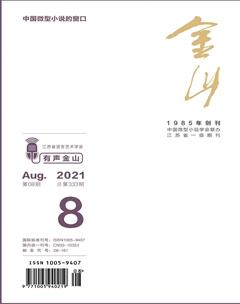從半世浮華走出的弘一法師
蔡曉偉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濤、字息霜,出身進士、鹽商家庭。早期藝術教育家,擅長書畫篆刻,工詩詞,曾赴日本學西洋繪畫和音樂。歸國后一度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今杭州師范大學)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南京大學前身)任繪畫、音樂教員。他是第一個向中國傳播西方音樂的先驅者,采用外國曲調重填新詞,創作歌曲《送別》等,對中國近代早期藝術教育具有啟蒙意義。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號弘一。后專研戒律,弘揚佛法,被佛教界尊為“律宗第十一代祖師”。
縱觀李叔同的一生,經歷豐富,多姿多彩,個性鮮明且特立獨行。正如他的得意門生豐子愷先生評論的那樣:“弘一法師由一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像樣。……都是‘認真的緣故。”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學者林語堂先生也認為:“李叔同是我們這個時代里最有才華的幾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個人,最遺世而獨立的一個人。”我們不妨從以下幾個方面探索分析。
出身富商,半世浮華;皈依佛門,半世苦行
李叔同出身于天津富商“桐達李家”,父親經營鹽業和錢莊,是一位典型的家境富裕、交游廣泛的世家子弟。他讀四書、習書畫、吟詩詞、精篆刻、彈鋼琴、演話劇,留學東瀛,才華橫溢,“二十文章驚海內”,同時還迷戀坤伶、詩妓和戲子,消遣秦樓楚館,寄情風塵聲色,享受半世浮華。人到中年,厭倦塵事,突然遁入佛門,一個華麗轉身,半世苦行,成就了一代大德高僧。那么這種涇渭分明,判若兩人,近似戲劇效應的嬗變又是如何產生的呢?我們就根據其人生發展的軌跡來作一次梳理分析。
出身庶子,地位卑微。李叔同在《初到世間的慨嘆》中寫道:“我是父親的小妾生的……在那時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為庶子,身份也就無法與我的同父異母的哥哥相比。從小就感受到這種不公平待遇給我帶來的壓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著,也許這就為我今后出家埋下伏筆。”這種壓抑,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他性格孤僻,脾氣古怪,特立獨行,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與他同時代的我國話劇藝術教育先驅之一、著名劇評撰稿人徐半梅就認為:李叔同脾氣太怪,“在社會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做和尚。”這是其出家的身份因素。
佛賜祥瑞,家庭熏染。李叔同出生時,據說有一只喜鵲口銜一枚橄欖枝放在產房的窗臺上,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佛賜祥瑞。而這枚橄欖枝也一直伴其終生。加上父親篤信佛教,家中設有佛堂,大娘和嫂子等都教其誦經,每到叔同生日必大舉放生,父親病逝時大做佛事,以及父親遺聯“今日方知心是佛,前生安見我非僧”的影響等,李叔同幼小時便用夾被或床罩當袈裟,玩起和尚念經和學放焰口等游戲,就有了敬佛親佛的傾向,甚至“很喜歡念經時那種空靈的感受”。這是其出家的家庭因素。
政見不一,背道而馳。父親去世早,長兄為父。而李叔同比哥哥小整整12歲,哥哥的管教比較嚴厲。但叔同認為,哥哥言行不一、表里不同、攀權倚貴、嫌貧愛富,便漸生叛逆傾向,反其道而行之,有時還故意放浪生活、聲色縱樂,終于厭倦人生,看破紅塵。這是其出家的叛逆因素。
西湖任教,清幽絕俗。李叔同曾在西子湖畔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多年,非常注重為人師表的道德修養。那種忙碌而充實的生活,將其年輕時沾染的所謂名士習氣洗刷干凈,使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靜和平淡,一種空靈的感覺油然而生,清澈明朗。這從曾先后在該校任教的沈鈞儒、朱自清、俞平伯和葉圣陶等名儒大家身上均能顯現,他們大多是清幽絕俗的淡泊文人。漸漸地,李叔同的生活狀態也變得內斂起來,喜歡離群索居、獨處一隅、息交絕游。他,心有所屬。而明鏡般的西湖,“笛韻悠揚”“山色空濛”“鐘聲林外”,恰恰滿足了他的需求,他曾在詩中寫道:“一半勾留是西湖”。一次與好友在湖心亭吃茶,夏丏尊對李叔同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李叔同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加之杭州濃厚的佛教氛圍,也讓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歸宿,最終遁入空門。這是其出家的遠因。
家道中落,消極悲觀。隨著國勢日蹙,曾經富甲天津的“桐達李家”也不可避免地逐步走上了下坡路。1911年,李家經營的最后一爿錢鋪歇業,經濟地位徹底喪失,終于家道中落。于此同時,李叔同搬出老宅,奉母南下。家族的分離,也給他帶來情感上的裂變,莫名傷感。不久,母親又不幸病逝,維系封建大家庭的最后一絲希望也不復存在。家庭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的巨變,加之家族內部的變化,多多少少在青年李叔同的內心漸生消極悲觀遁世的情緒。出家,也就成為他尋求精神慰藉,或者說是一種“自我人格的完善”的方法。這是其出家的外因。
精神導師,熏陶漸悟。1902—1903年間,李叔同與馬一孚相識并頻繁交往,兩人的友誼一直延續到弘一圓寂。馬一孚曾游學日美,飽讀經書,學貫中西,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國學大師,又是佛學家。李叔同對其很是推崇:“自去臘(去年)受馬一孚大士之熏陶,漸有所悟。”馬一孚可謂是李叔同的“精神導師”,是其學佛道上的引路人。這是其出家的誘因。
道德為本,儒釋相通。李叔同的父親為進士出身,本人也曾以監生資格兩次參加鄉試,雖兩度落榜,但他始終認為“以孝悌為本、才能為末;器識為先、文藝為后。”李叔同最后由儒入佛、由塵世而歸于空門,或許與此種追求有關。他在留日學生創辦的《醒獅》雜志上發表的詩句就可以佐證:“誓渡眾生成佛果,為現歌臺說法身。”后來,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一文中曾說:“沒有比依佛法修行更為積極和更有意義的人生之路。”在他看來,佛教是積極的、救世的。這一點,儒道和釋教是相通的。這是其出家的內因。
斷食修行,除舊換新。夏丏尊曾給李叔同推薦了一篇關于斷食修行的文章,稱可以幫助其身心更新,從而達到除舊換新、改惡向善的目的,使人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李叔同年幼時體弱多病,患有肺結核、神經衰弱癥等,便也想以此一試,既能治病,又能修身養性,何樂不為呢?!于是,1916年,李叔同在西子湖畔的虎跑寺開始斷食三周。斷食期間,他感覺“身心輕快了很多、空靈了很多,心的感受力比以往更加靈敏了,并且頗有文思和洞察力,感覺就像脫胎換骨過了一樣。”李叔同內心澄澈干凈,自覺已然重生。他在斷食期間還寫下了一篇《斷食日志》,不過直到他圓寂后,才于1947年刊登在上海《覺有情》雜志上。這是他出家的近因。
兩受刺激,終下決心。就在斷食體驗后不久的那一年除夕,李叔同沒有回家與親人團圓,而是在虎跑寺過的年。有一天,馬一孚的朋友也入山習靜,沒幾天,竟毅然絕然地剃度出家,皈依佛門。李叔同目睹其受戒的全過程,內心受到強烈刺激,心生向往,遂于1918年2月25日(農歷正月十五)發心皈依三寶,拜了悟禪師為師,法名演音、法號弘一,成為一個在家修行的居士。由于考慮到出家的種種困難,李叔同本打算“先做一年居士,轉年再行剃度”,因此經常是寺廟——杭州——南京間來回奔走,非常辛苦。夏丏尊很是后悔,一次激動地對李叔同正話反說:“與其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不如索性出家做了和尚,倒清爽!”一句氣話,不想竟再次刺激到李叔同,促使其下了最后的決心——剃度出家!同年8月19日(農歷七月十三),相傳是大勢至菩薩的圣誕日,李叔同到虎跑寺落發受戒,由慧明法師剃度,正式成為一名僧人。這是其出家的直接因素。從此,半世浮華半世僧,塵世再無李叔同。其實早在他做居士后的一個多月,李叔同在給學生劉質平的信中已經流露出了剃度的念頭:“不佞近耽空寂,厭棄人世。早在今夏、遲在明年,將入山剃度為沙彌。”朋友的一句氣話,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罷了。
現實苦海,早求解脫。李叔同遁入佛門苦修,在客觀上是對自己過去生活和現實世界的一種否定。從世家子弟到風流兒郎,從披發佯狂到洗盡鉛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一旦醒悟,苦悶不堪,但又無可奈何,只能遁入佛門,潛心修持,超越現實,以求解脫。同時在主觀上,因為自己身體自幼羸弱,經常生病,入佛門苦修,是為了自我生命的完成。弘一法師曾袒露心聲:“弟子出家,非謀衣食,純為了生死大事。”出家以后,時為疾病所苦,每次生病,都給他帶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雙重苦痛,總會流露出早脫苦海、往生極樂的愿望。這也是其出家的主要因素。
當然,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很多,也很復雜,以上只是淺略歸納分析了十種。其實,其中最重要的,或者說起決定性作用的也就是兩三個方面,其他都是從屬因素而已。
精研戒律,重光律學;發誓朝宗,終未如愿
出家后的弘一,一開始就對佛教戒律學的研究執著專注,這在僧人中是非常少見的。原因是馬一孚居士送給他的兩本書:《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和《寶華傳戒正范》。前一本書是明末高僧藕益智旭法師的律學精神旨要,而后一本書則是明末寶華山見月法師為傳戒所制定的戒律標準。由于當時佛門戒律廢弛,很多僧人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戒律可以遵守,長此以往,佛法將無法長存,故弘一法師受戒后下決心要學習律學,“每日標點研習《南山律》約六七小時”,以戒為師,戒行精嚴,完全嚴格按照南山律宗的戒規行事。
中國佛教律宗的實際開創者是隋末唐初的鎮江(丹徒)人道宣。他從律學大師智首學習各種戒律,尤其學得《四分律》的精髓,著有《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拾毗尼義鈔》《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和《四分比丘尼鈔》等律學五大部,皆為律學之要義。因其長期居于終南山,并在山上構建起他的律學規范,故后人稱南山律宗,道宣則被尊為南山律師。明末,三昧律師分燈于鎮江寶華山,整修寺廟,入主隆昌寺,并任見月為監院,使該寺得以中興。后來,三昧傳法席于見月,見月始精研律藏,并編定了《寶華傳戒正范》,影響深廣。他主山30年,為各方所推崇,使隆昌寺成為全國最有影響的律宗傳戒場所。因此,寶華山被譽為“律宗第一山”,而見月也被尊為寶華律宗第二代祖師。見月和尚墓,又稱見月律師塔,位于寺西北半山腰,建于清初,石冢為環形結構,墓塔由三塊巨石壘成,高約2米,上刻蓮瓣紋,中間石刻“傳南山宗中興止作寶華第二代見月律師塔”字樣,塔頂呈圓盆狀,是江南高僧墓葬形式的重要代表,保存完好,為江蘇省級文保單位。
弘一法師曾在佛前發誓,要重光律學。終其一生,都在學習、研究和傳授戒律,并用四年時間,于1924年8月撰寫完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這是弘一法師出家后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使淹沒七百多年的南山律學得以流布世間,成為自宋代以后律學的第一巨著。因此,他被佛門稱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由于見月律師所編《寶華傳戒正范》多用駢體文,僧眾難以理解,故弘一廣為傳講。同時他還重新校閱、標注見月老人所著自述行腳參學經歷的《一夢漫言》,并作《見月律師行腳略圖》。他曾在雜記中說:“臥床追憶見月老人遺事,并發愿于明年往華山(即寶華山)禮塔(即見月律師塔),淚落不止,痛法門之陵夷也。”弘一法師是一位追求“心口如一、表里如一、言行如一、醒夢如一,乃至生死如一”和“言必行、行必果”的大德高僧,但不知為何,這一愿望似乎最終并沒有實現。
一生名號,何其之多!隨境而生,寓意明顯
李叔同一生名號別署甚多,自述“生平易名字百十數”,可靠的即有70余個。他的學生、中國知名音樂家劉質平說:“(李叔同)所寫筆名同山名、寺名、院名,有曾住者,有未曾住者,有寺院名臆造者,有全部臆造者,均與筆名同時決定。”學者陳星推論,這種情況或許與李叔同的性格有關。也有人說,李叔同因為害怕為名所累,出家后便隨手簽署,故此別名很多。筆者則認為,李叔同的名號雖多,但并不都是隨手亂簽的,有不少是隨境而生,且明顯表達著某種寓意。現按年代先后,分述如下:
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出生,譜名“文濤”,乳名“成蹊”,典出《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天津名士趙幼梅取《佛經》中“伯叔壯志,世界大同”意為其取字“叔同”,學名“廣侯”,號“漱筒”。
1898年,李叔同初次南下上海就小有名氣,曾以“惜霜”“當湖惜霜”和“惜霜仙史”等名字先后在《春江花月報》《消閑報》和《笑林報》上發表作品,故有“二十文章驚海內”之說。
1900年,李叔同與“城南文社”的許幻園、袁希濂、蔡小香和張小樓志趣相合,詩文唱和,并拜為金蘭之好,結成“天涯五友”。李叔同應許幻園的邀請,搬進上海城南草堂居住。因客廳掛“醾紈閣”匾額,后許幻園又增題“李廬”二字,故李叔同又有了“醾紈閣主”和“李廬主人”的別號。
1902年,李叔同曾以“李廣平”為名,在杭州參加鄉試。
1905年,母親的去世,使李叔同失去了“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后就是不斷的悲哀和憂愁”,因此改名“李哀”,字“哀公”。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籌辦《音樂小雜志》,這是中國人創辦的第一本音樂啟蒙類刊物。他署名“息霜”為這本雜志作序。同年,又以“李岸”為名,正式進入東京上野美術學校學習。
1912年4月,李叔同從日本學成回國后,在上海與柳亞子、蘇曼殊和陳無我等一起擔任新創刊的《太平洋報》主筆,并負責編輯廣告和文藝副刊。在發刊祝詞欄中,他署名“江東少年”發表賀語。同年,還以“凡民”為筆名,先后在該報發表《廣告叢談》和《西洋畫法》等文。
1913年7月16日,在寫給好友許幻園的信中,李叔同落款“李息”,后又稱“息老人”。
1914年,李叔同曾在《樂石社社友小傳》中自述:“李息,字叔同,一字息翁。……生平易名字百十數,名之著者:曰文濤,曰下,曰成蹊,曰廣平,曰岸,曰哀,曰凡;字之著者:曰叔同,曰漱筒,曰惜霜(惜霜仙史),曰桃谿,曰李廬(李廬主人),曰壙廬,曰息霜。又自謚曰哀公。”
1916年,李叔同在虎跑寺斷食修行,體驗深刻,“能聽人平常所不能聽,悟人所不能悟。”這一次脫胎換骨的修行,被李叔同視若重生。為了紀念這個特殊的人生體悟,他取老子“能嬰兒乎”的語意,給自己取名“李嬰”。斷食期間,他還打算今后易名“欣”、字“倣同”、號“黃昏老人”等。這一時期,李叔同的信仰實際上并未定型,閑暇時常看理學書和道家書,案頭就放著《道藏》,還自稱“欣欣道人”。
1918年2月25日,李叔同在虎跑寺拜了悟法師為師,皈依三寶,為在家弟子,法名“演音”,號“弘一”。同年8月19日在虎跑寺正式落發為僧。
1920年,弘一以“曇防”名回信。
1921年又以“曇昉”名落款。
1924年,弘一先后用“勝臂”“善臂”和“勝髻”等名;同年11月又用“論月”名,后因名字歧異,郵局時生疑議,“希勿再用‘論月二字”。
1926年,弘一改用“月臂”名,并自刻“沙門月臂”“沙門勝髻”“沙門演音”和“沙門曇昉”等印章;又用“勝立”名。
1928年,弘一曾用“弘裔”和“僧胤”名寫信。
1931年,弘一改用“亡言”名落款。大概是有一次大師病重,曾手書偈語,其中一句“問余何適,廓而亡言。”
1933年,弘一請李晉章居士(弘一侄)制印,“其文字乞于下列數名中隨意選之:亡言、無得、吉目、勝音、無畏、大慈、大方廣、音、弘一。”
1934年,弘一用“髻目”名。
1935年,弘一又用“月幢”名。
1936年,弘一再用“一音”“月音”名。
1937年,弘一在《閩南十年之夢影》一文中說:“近來我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叫‘二一老人。……記得古人有句詩‘一事無成人漸老。清初吳梅村(偉業)臨終的絕命詞有:‘一錢不值何消說。這兩句詩的開頭都是‘一字,所以我用來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1939年3月25日是弘一大師亡母謝世34周年,他在一冊《前塵影事》上專門作了題記。這段時間,他深深陷入生命之初的回憶,經常夢見童年時的情景,因此也經常用“善夢”的名字。
1940年,弘一兼用“夢”“晚晴”或“晚晴老人”等名。
據李叔同次子李瑞回憶,有一年其父從上海帶回天津四個大皮箱,上面都有“李庶同制”的字樣。所謂“庶同”,實際上含有自己雖是“庶出”,但與其兄相同、平等的寓意。李叔同在為自己和母親正名分。另外,李叔同還曾用過“李良”“李布衣”“龍音”“髻嚴”“如眼”“瘦桐”“舒統”“廣心”“吉臣”“大心凡夫”和“化人幻士”等名。更有意思的是,李叔同年輕時喜歡養貓,1896年,他居然在信封上自己署名“天津貓部緘”。
李叔同與鎮江的不解之緣
雖然李叔同曾一度在杭州第一師范學校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兼職任教,經常經過鎮江而奔走于寧、杭之間;雖然他也曾發愿要上寶華山禮拜見月律師塔,可終其一生,筆者并未發現大師曾落腳鎮江的任何蛛絲馬跡。但這并不代表他與鎮江就沒有任何關系。實際上,大師與鎮江有著許多不解之緣。
李叔同在書畫方面頗有造詣。鎮江丹陽人,中國近現代著名書畫家、丹陽正則女子職業學校“正則繡”(又名“亂針繡”)創始人呂鳳子先生認為:“嚴格地說起來,中國傳統繪畫改良運動的首倡者,應推李叔同為第一人。根據現有的許多資料看,李先生應是民國以來第一位正式把西洋繪畫思想引介于我國,進而啟發了我國傳統繪畫需要改良的思潮。而后的劉海粟、徐悲鴻等在實質上都是受了李先生的影響,進而成為中國傳統繪畫改良運動的推動者。”劉海粟晚年也這樣講:“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個人。”呂鳳子曾任國立美專的校長,潘天壽是該校教員,吳冠中是其學生,呂先生還曾免費教授徐悲鴻學素描。所以,呂鳳子先生的話當在書畫界具有相當的分量和影響。
1900年,李叔同與朱夢廬、高邑之和烏目山僧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書畫公會(社)。而烏目山僧幼年曾在金山寺(江天禪寺)受戒,法名印楞,別號烏目山僧,又號楞伽小隱。1919年為棲霞寺(金山寺分宗)住持,與章太炎友誼深厚,與孫中山、蔡元培等交往也很密切,為同盟會成員。他活躍于僧俗兩界,且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一度還俗,出入豪門,交接權貴,涉足政治,被稱為“革命和尚”,且與“猶太財商的外國妻子有染”。后來重返金山寺,研習佛典。雖然李叔同賞識他在書畫方面的滿腹才華,但絕不接受他這樣子糟蹋不羈的品性,此后二人再無聯絡、不再往來。這也許就是李叔同鎮江之行未能如愿的主要原因之一。
1904年,李叔同在上海參加以“研究學術”“開通風氣、交換知識,圖謀學界之公益”為宗旨的滬學會。該學會由馬相伯等組織。馬相伯是鎮江丹陽人,中國著名教育家,中國現代文明的開啟者。他認為:“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于是,1903年,馬相伯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震旦學院。1905年,他又憑一己之力興辦了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并兼首任校長。該校先后培養和影響了蔡元培、于右任、竺可楨、李叔同、陳寅恪、黃炎培和邵力子等一批大師級人物。同時,馬相伯還曾助其弟馬建忠編著中國第一部系統性漢語語法著作《馬氏文通》。
大約是在1913年冬季的一個清晨,大雪狂舞,好友許幻園站在李叔同家院子里高喊:“叔同兄,我家破產了,咱們后會有期。”說完掉頭就走。李叔同站在雪地里整整一小時,然后返身回屋,把房門一關,揮淚寫下了:“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這首傳世佳作。其實,這首《送別》是李叔同受日本歌詞作家犬童球溪創作的歌曲《旅愁》影響,重新填詞創作的。《送別》無論是歌詞的句式還是意境,都與《旅愁》十分接近,應該說是受到《旅愁》直接的影響。而這兩首歌曲的旋律都是源于美國作曲家J·P·奧德威創作的通俗歌曲《夢見家和母親》。后來《送別》因在《早春二月》和《城南舊事》等影視片中多次被用為插曲,逐漸為世人耳熟能詳、盛名遠播,遂成為李叔同的代表作。其中“夕陽山外山”一句,便出自于清代詩人龔自珍所作的《己亥雜詩》第272首:“未濟終焉心縹緲,萬事都從缺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余情繞。”而李叔同是熟讀該詩的,他曾在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同學會上引用過這首詩。
1920年,“天涯五友”之一的袁希濂在調任前,去杭州玉泉寺與弘一法師道別。不想弘一法師對袁說:“你前生也是和尚,要朝夕念佛。有一本清朝人周夢顏寫的《安士全書》必須閱讀,不可忘卻。”當時袁希濂不以為然。1926年,袁在丹陽縣任內,得到一本《安士全書》,趕忙閱讀,始恍然于學佛之不可緩,于是在官署中設立佛堂,朝夕念經拜佛。同年3月,丹陽城內大火。袁希濂親臨現場指揮救火,井河皆抽干,大火仍熊熊,無計可施。袁希濂便默誦大悲咒,祈求火息。說也奇怪,一刻鐘后,樓房坍塌,火焰遂息。后袁希濂回上海,在太平寺皈依印光大師,成為居士。
鎮江焦山定慧寺住持茗山法師是中國當代高僧,曾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江蘇省佛教協會會長等職,還先后任棲霞山棲霞寺、寶華山隆昌寺和靈山祥符寺方丈等,精通三藏,戒律精嚴,定慧雙修,學識淵博。茗公十分敬佩弘一大師,在他生前日記中,有20多處提到弘一法師。譬如茗老一次對僧眾講經,就是以弘一開示后學的“惜福、習勞、持戒、自尊”八字為題,借題發揮,勉勵大眾;還有一次茗山準備講《四分戒本》,晚備課至12點,感嘆到:“受弘一大師教益不少”。畫家李亞曾往焦山拜望茗老,贈《弘一大師手抄阿彌陀經》一部,茗公如獲至寶,心甚感激。李老并請在準備送給新加坡凈宗學會的另一件弘一大師手跡上題字,茗老欣然以虛云老和尚的兩句話題曰:“問余終日渾何事,一句彌陀萬慮舒”。
至于李叔同出家后精研律學,推崇見月律師,發愿往寶華山禮拜一事,前面已經說過,這里不再贅述。總之,李叔同一生與鎮江有許多緣分,卻沒有留下任何到過鎮江的痕跡,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