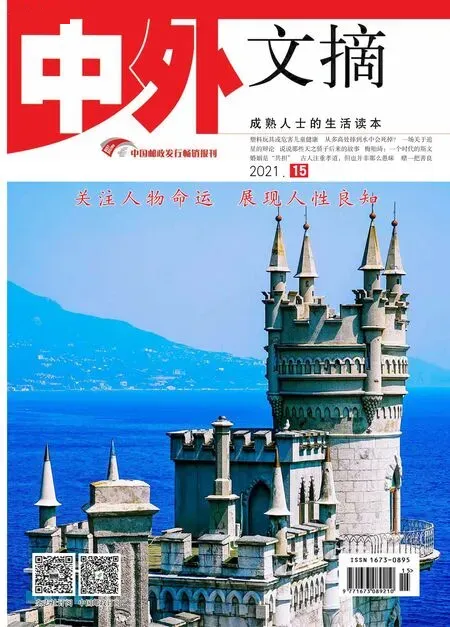這個世界的『安全感』在哪兒?
□ 鄧楚涵

自從十年前,我知道“安全感”這個詞之后,便越來越沒有安全感。
那年,我從家鄉去上海上大學,學習土木工程。我的家鄉是西南部的一個小縣城,那里沒有高樓,沒有地鐵,沒有電影院,更沒有咖啡館,所以我剛到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的時候,感覺眼前的一切都太摩登了。
剛開學的第一個月,我都不太敢和同學說話,即便非得聊上幾句,也極度克制,多不如少,少不如無。那種克制的感覺很不好,因為它總是伴隨著敏感和自卑。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聽到“安全感”這個詞,才恍然大悟——我缺的就是安全感!
當年在大學里受歡迎的人不是“高富帥”,而是每門課程都考90分以上的學霸。為了找到安全感,我決定提前三個月備戰期末考試。每天早上六點便到圖書館后面的河邊開始晨讀,八點圖書館開門,我就第一個沖進去,晚上十點才戀戀不舍地回到宿舍。這樣的節奏被我保持了整整一學期,以至于圖書館的大爺總夸我認真刻苦,不時還勉勵我拿年級第一。
大爺的心地雖好但眼光實在太差,我復習了整整三個月,只考了一個平平無奇的分數。我在家鄉做慣了學霸,在大學不僅淪為學渣,還和學霸低頭不見抬頭見,這下,我更沒安全感了。
一
過年期間,我躲在家里不出門,琢磨了一個寒假后又想到了一個方法:既然拼命學習考不了高分,那就盡早起步科研,發幾篇論文。
開學后,我立馬去了橋梁系,找到一位碩士學長的導師,軟磨硬泡請他帶我做科研,之后被安排去做實驗。實驗條件極其惡劣,夏天沒空調,冬天沒暖氣,一組實驗就要20 個小時,每小時還得人工記錄一次數據。彼時,我安慰自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論文一發,何愁沒有安全感?
半年之后,實驗終于結束了,可我興致勃勃地分析了數月,卻沒有一組數據能完全達到老師的要求,發論文的夢想徹底泡湯。
大一下學期的我很是懵懂,明明是自己道行不夠,反倒跑去橋梁系向老師抱怨成果不佳、缺乏安全感。在老師眼中,我肯定是又傻又天真,但他還是很紳士地鼓勵了我:“你剛開始做科研,沒有安全感很正常,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相信我,等你讀到博士就好了。”
后來,我到英國讀博。剛到學校的第二天,得知隔壁的實驗室出了29 個諾貝爾獎,尋思著指不定自己運氣好,也能撈個諾貝爾獎。入學第一周,我便去找導師確定了研究課題,課題一定,我就辭別導師回家,途中看到了徐志摩筆下《再別康橋》的美景:“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艷影/在我的心頭蕩漾。”白駒過隙,當年未曾料想我在康河的柔波里一蕩漾就是四年,如今變成了一棵水草。
學長學姐們通常做到第五組、第六組實驗,便可順利畢業,可我硬是破了極限,前后一共做了17 組。導師心中有苦,因為他這些年不僅費心,還費錢。我心中更苦,更沒有安全感了,因為最初的夢想早已灰飛煙滅。
有一天午飯時間,導師突然問我還掛念諾貝爾獎不,我趕緊認錯道:“只嘆當年太傻太天真,才落得如今這個既失落又沒有安全感的下場。”他特別認真地對我說:“讀博士必然會有不安全感,你別多想,趕緊帶著不安全感上路吧。”老師的話讓我意識到,學生階段大多數人都沒有安全感,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焦慮。我現在要做的,就是盡快調整好自己,繼續在被不安全感裹挾的求學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走。
不過不安全感這個東西,從來就不只出現在校園里。
二
后來,我參加一檔科學節目,擔任科學解題人。那是我第一次跨界工作。拿到臺本的那一刻,我心里踏實了,私下給略有些擔心的媽媽發消息:“這工作就是小菜一碟,所有的實驗都沒超出高中物理和化學知識。你放心,我都讀到博士了,能連這都搞不定嗎?”
然而,第一天錄制,我就和整個節目組“格格不入”。
第一期來參加節目的嘉賓一個是鋼琴家,另一個是魔術師,他倆不僅手靈活,腦子也靈活,我好幾次還沒反應過來,就被他們套出題目答案,嚇得導演不停地提示我不要多說話。站在舞臺上不說話會顯得很多余,我心里憋屈難受,好不容易熬到解釋科學原理,準備滔滔不絕,結果剛一開口,導演就喊:“停!看鏡頭啊!你看哪兒呢?”我趕緊找到鏡頭,從頭說起,剛說完兩句,導演又喊:“停!站穩了說,你別晃悠啊!”我立馬繃住身體,從頭再來,說了幾句,突然就不出聲了,全場安靜了十秒鐘后,導演弱弱地問:“你又咋啦?”
我好不容易憋出一句話:“導演,我有點兒緊張,講錯了。”我隔著四十米遠都能感覺到她的崩潰,就差捶胸頓足了。那期節目從中午十二點錄到次日凌晨四點,我沒少為嚴重超時作貢獻,導演、主持人、嘉賓和現場觀眾全都心力交瘁,我自己也精疲力竭。
回到房間,我心里三分自責,一分委屈,剩下的全是不安全感導致的焦慮。一個已經習慣了在實驗室看數據的人,突然被叫去電視臺錄節目,還一個勁兒地制造問題,如何能安然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節目組領導,開門見山說要停止錄制,并鄭重其事地說:“我太焦慮了,錄制過程中充滿了不安全感。”領導輕聲問是誰給了我不安全感,我說:“在場的所有人都給我不安全感,這工作我真做不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過你又不是不安全,你只是缺乏安全感而已。”領導沒計較我的冒昧和失禮,反倒給我盛了碗心靈雞湯,“這倆東西可不一樣,不安全可能會讓你失敗,但不安全感往往會讓你成事兒。當然,要不要繼續,你自己說了算。”
當然,我最后選擇了繼續,不過這并不是因為當時聽進去了他的話,而是我覺得要就這么走了,實在太丟人,所以只好忍耐著,繼續堅持在舞臺上跨界工作。
三
因機緣巧合,我開始擔任“科普中國形象大使”。雖說科研和科普都姓科,但二者迥然不同,前者講究深度,后者強調廣度。雖說前輩學者總是傾囊相授,各行好友更是鼎力相助,可我每次只要一走出自己的專業領域,就很缺乏安全感,因為學海無涯,短時間內為求廣度,只能放棄深度,甚至囫圇吞棗。
每每心中生出劇烈的不安全感,我都會想到當年節目組領導的勸誡:“不安全可能會讓你失敗,但不安全感往往會讓你成事兒。”然后耳畔仿佛又響起他的聲音:“要不要繼續,你自己說了算。”
歲月匆匆,從聽聞“安全感”到如今已十年,我雖然一直在費盡心思抵抗不安全感,但內心依然無法擺脫渴望安全感的念想。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句話:“生活諸多艱險,沒有安全感是活下去的必然代價。”猶如醍醐灌頂。
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安全感”。我們只能像個勇士,先摧毀“安全感”這個偽概念在心里的幻影,然后憑借責任感去直面所有的不安全感,最終堅定前行、永遠步履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