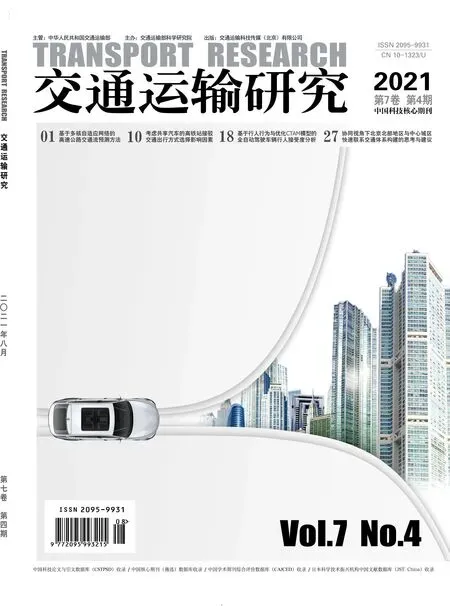考慮共享汽車的高鐵站接駁交通出行方式選擇影響因素
谷鑫鑫,趙勝川,羅歡歡
(大連理工大學交通運輸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
0 引言
隨著高鐵在我國的蓬勃發展,旅客城際出行體驗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很多高鐵站遠離市區以及部分城市交通與高鐵銜接不緊密的現狀已經成為人們乘坐高鐵的阻礙。“高鐵+共享汽車”服務應運而生,這是“中國速度”與共享經濟的結合:高鐵很好地解決了旅客城際交通問題,而共享汽車作為一種對傳統小汽車出行方式的創新,可以幫助旅客解決高鐵站到市區之間的交通問題。本文將通過分析影響旅客高鐵站接駁交通出行方式選擇的因素,探究共享汽車參與接駁出行的可行性。
共享汽車是傳統的汽車租賃與當前的共享經濟結合的產物,近年來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國外關于共享汽車的研究比國內起步要早。大量研究認為,共享汽車在提供多樣化出行方式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人小汽車的私密性和靈活性[1],還可以降低小汽車擁有率[2-3]。Tran 等[4]分析了影響出行者對電動共享汽車接受度的因素,發現出行者對出行費用較為敏感,減少共享汽車的使用成本和增加私家車的停車費用有利于提高共享汽車的使用率[5]。在市場方面,部分學者對共享汽車的會員數量[6]和時空分布[7]進行了研究,但這些研究沒有針對共享汽車的具體應用場景。Wappelhorst 等[8]調查對比了共享汽車在城市與鄉村的潛在使用需求,但是沒有發現城市與鄉村居民對于共享汽車使用的偏好差異。除了關于市內交通出行中共享汽車的作用研究之外,還有一些關于共享汽車在城際交通中的應用研究。Luca 等[9]通過行為調查(Stated Preference,SP),研究了城市間單程出行的共享汽車選擇行為,發現出行費用、到停車場所需時間、性別、年齡、出行頻率、是否擁有私家車和出行類型是最顯著的影響因素。國內目前關于共享汽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享汽車的用戶行為、市場和車輛調度等方面。用戶行為分析方面,國內學者主要使用問卷調查的方法,研究發現出行者對共享汽車站點的距離比較敏感,經濟性是共享汽車需要保持的重要優勢[10],隨著出行距離的增大和共享汽車收費標準的降低,出行者選擇共享汽車服務的可能性增大[11]。市場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從供需角度分析了共享汽車公司的定價策略[12]和出行者的共享汽車使用需求[13]。車輛調度研究方面,王寧等[14]提出了基于用戶激勵的共享電動汽車自適應調度,實證分析顯示,該方法能夠提高運營公司的收益及車輛利用率,節約成本并提高用戶滿意度。
綜上可知,國內關于共享汽車的研究沒有涉及共享汽車的具體使用場景,當前高鐵站接駁交通的研究對象也主要是公共交通[15],缺少出行者在高鐵站接駁交通中的共享汽車使用意愿影響因素研究。據知名咨詢機構羅蘭貝格預測,2025 年中國共享汽車的數量將達到60萬輛,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共享汽車市場[16]。共享汽車行業仍有遠大前景,提供場景化的“高鐵+共享汽車”服務,或許是共享汽車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本研究考慮共享汽車、出租車/網約車和公交車這3 種出行方式,選擇等待時間、行程時間、費用和押金作為效用函數的選擇方案特性變量,構建多項離散選擇模型(Multinomial Logit,MNL),分析在高鐵站接駁交通環境下,考慮共享汽車服務時出行者出行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以期為共享汽車場景化應用的實施和相關政策制定提供理論依據。
1 問卷設計及樣本統計分析
1.1 問卷設計
本研究旨在了解高鐵出行者對接駁交通中共享汽車的使用意愿及其影響因素。高鐵站接駁交通包括“到達高鐵站”和“從高鐵站出發”兩種類型。本研究采用實地問卷調查的方式,在高鐵站候車廳內對高鐵乘客進行調查,對“到達高鐵站”采用RP 調查,對“從高鐵站出發”采用SP 調查。參考現有文獻,結合專家意見和調查地點實際情況,調查問卷主要分為以下3 個部分。
(1)受訪者基本信息調查。該部分主要研究個人屬性對出行方式選擇的影響,調查內容包括年齡、性別、職業、月收入、是否持有駕照和是否擁有小汽車。
(2)受訪者出行特征信息調查。該部分主要調查受訪者本次出行的相關特征信息及對共享汽車的使用和了解情況,調查內容包括本次出行目的、同行人數、駕車喜好、日常通勤方式、對共享汽車的了解程度和使用情況。
(3)考慮共享汽車的出行方式選擇意愿調查。該部分為本次調查問卷的核心部分,出行場景假設為乘高鐵到達站點之后,需要前往一定距離之外的目的地,在共享汽車、出租車/網約車和公共交通之中選擇一種交通方式出行。共享汽車的出行特征主要包括等待時間、擁堵時間、還車方式、車輛類型和押金金額,具體水平值設置如表1所示。

表1 共享汽車特性變量及水平值設置
以大連北站為例,該站距市中心約12km,根據該站接駁交通情況,本調查選取6km,12km 和18km作為出行場景的出行距離。每個出行場景包括共享汽車、出租車/網約車和公交車這3 種出行方式,受訪者需要綜合考慮等待時間、行程時間和費用等各種出行方式共有的因素,以及還車方式、車輛類型和押金等共享汽車特有的因素,最終選擇一種交通方式出行。
1.2 數據收集與處理
為提高問卷填寫質量,保障數據的真實性、有效性和普遍性,本研究采用線下問卷調查的方式,分別在哈爾濱西站、長春西站和大連北站3個東北地區高鐵車站候車廳進行隨機抽樣調查,共收集到380 份調查問卷,刪除18 歲以下受訪者的問卷及不合理問卷(如無駕照、獨自出行且選擇共享汽車出行的問卷),最終獲得356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3.7%。每套問卷包含3 個情景選擇樣本,因此有效樣本個數為1 068 個,保證了模型結果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受訪者的基本屬性包括年齡、性別、月收入、駕照和私家車等,樣本的結構如表2 所示。受訪者的年齡集中在18~50 歲,男性受訪者略多于女性受訪者,月收入大部分在10 000 元以下,持有駕照的占比較大,而擁有私家車的占比較小。

表2 受訪者個人屬性結構特征
1.3 樣本統計分析
對用戶的出行特征進行交叉統計分析,可以初步確定影響接駁交通中用戶出行方式選擇的因素。經分析,年齡、同行人數和日常通勤方式等因素對于出行方式的選擇具有顯著影響。
(1)年齡。如圖1 所示,不同年齡段的群體在出行方式的選擇上存在很大差異。18~30 歲和31~50 歲群體選擇的出行方式相似,選擇共享汽車出行的比例分別為34.2%和36.27%,該年齡段群體更喜歡出租車/網約車出行,選擇公交車出行的比例較低;51~70 歲群體更喜歡選擇公交車出行,選擇共享汽車和出租車/網約車出行的比例之和小于50%。

圖1 各年齡段接駁出行方式選擇分布
(2)同行人數。如圖2 所示,出行時同行人數同樣對出行方式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受訪者為單人出行時,更喜歡選擇出租車/網約車出行,但是有同行人時,受訪者選擇共享汽車出行的比例大于選擇出租車/網約車出行的比例,有同行人時受訪者選擇共享汽車出行的比例要比沒有同行人時的比例高9.69個百分點。

圖2 不同同行人數下接駁出行方式選擇分布
(3)日常通勤方式。如圖3 所示,日常出行方式對高鐵站—市區出行交通方式的選擇同樣具有較大影響。日常出行方式為私家車的用戶更愿意在高鐵站接駁出行時使用共享汽車,比例為43.19%;日常出行方式為出租車/網約車的用戶選擇共享汽車出行的比例也較高,為36.16%;日常出行方式為公交車的用戶更愿意繼續選擇公交車出行(比例為48.96%),而選擇共享汽車的比例較低,為26.04%。

圖3 不同日常出行方式下接駁出行方式選擇分布
2 模型構建
2.1 理論基礎
本文采用MNL模型分析受訪者高鐵站接駁出行方式選擇行為。MNL 模型作為一種常見的離散選擇模型,廣泛應用于交通行為分析。
離散選擇模型是基于隨機效用理論和效用最大化假說提出的,即離散選擇模型的建立基于兩點假設:①消費者(決策者)是選擇行為的最基本的意愿決定單位;②消費者(決策者)是理性人,他們面對給定的選擇方案集,將會選擇效用最大的方案。
隨機效用理論將效用視為隨機變量,并將隨機效用函數U分為可觀測的固定項Vin和不可直接觀測的隨機項εin。同時,隨機效用理論認為Vin與εin存在線性關系。即,如果假設消費者(決策者)n選擇方案i的效用為Uin,則:

式(1)中:Vin為消費者(決策者)n選擇方案i的效用函數中的固定項;εin為消費者(決策者)n選擇方案i的效用函數中的隨機項。
所謂效用最大化假說,即消費者(決策者)在給定的選擇情景下,將選擇能讓其獲得最大效用的選擇方案。如果消費者(決策者)在給定的選擇方案集An中,選擇方案i的條件為:Uin>Ujn(i∈An,j∈An,i≠j),則根據效用最大化假說,消費者(決策者)n選擇方案i的概率Pin為:

其中,0 ≤Pin≤1,。
當效用函數中的隨機項εin服從獨立的同參數二重指數分布時,可以推導出Logit模型。采用線性函數作為效用函數形式,各出行方式的效用函數為:

式(3)中:β0為常量;βk為待定系數;為出行者n選擇出行方式i的第k個變量值。

出行時間價值VOT 可以通過MNL 模型中的時間與費用參數進行計算,公式如下:式(4)中:Vi為出行方式i的效用函數;ti為出行方式i的出行時間;γi為出行方式i的出行費用;λt為效用函數中出行時間的系數值;λc為效用函數中出行費用的系數值。
2.2 效用函數構建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影響出行者出行方式選擇的因素按屬性可以分為3 類,即:選擇方案特性變量、個人屬性變量和出行特征屬性變量。效用函數中的變量設置如表3所示。

表3 效用函數變量描述
其中,職業包括學生(CA-S)、企業職工(CA-E)和行政事業單位職工(CA-P);高鐵出行目的包括商務(TP-C)、回家(TP-H)、旅游(TP-T)和訪友(TP-F)等;日常通勤方式包括私家車(CM-C)、公交(CM-B)、地鐵(CM-M)和出租車(CM-T)等;對年齡、月收入數據進行重新賦值,對性別、職業等屬性變量進行虛擬變量處理。
3 模型結果分析
本文以出租車/網約車為參考項,借助R 語言,使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對MNL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剔除共享汽車還車方式、共享汽車車輛類型等不相關變量后再次進行模型標定,最終模型的選擇方案特性變量參數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參數估計結果

表4 (續)
3.1 選擇方案特性變量參數估計結果
等待時間、出行時間、費用和押金的系數均為負值,且變量參數顯著,表明等待時間、出行時間、費用和押金均對共享汽車的使用產生負效用,即:隨著等待時間、出行時間、費用和押金的增加,高鐵站旅客在接駁交通中選擇共享汽車出行的概率將減小。模型中等待時間和出行時間的單位為min,費用單位為元,押金單位為百元。根據各變量的系數值大小可以發現:等待時間增加1min 產生的負效用,相當于出行時間增加1.82min 產生的負效用;出行費用增加1 元產生的負效用,相當于押金增加181 元產生的負效用,旅客接駁出行過程中的時間價值約為51.7 元/h,與我國城市居民小時工資大體一致。
3.2 個人屬性變量參數估計結果
共享汽車和公交車的效用函數中年齡的系數分別為0.344 和0.948,均為正數,表明隨著年齡的增加,相比出租車,旅客更愿意選擇共享汽車和公交車作為接駁出行的交通方式,并且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年齡段由18~30 歲增加到31~50歲時,選擇共享汽車的概率增加6.1%。
收入水平系數均為負數,表明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相比出租車出行,旅客選擇共享汽車和公交車出行的可能性不斷減小。
分析職業的系數值發現,企業、事業單位員工的系數均為負數,說明企事業單位的員工普遍更喜歡出租車/網約車接駁出行。駕照的系數在共享汽車的效用函數中為正值,在公交車的效用函數中為負值,表明持有駕照會增大旅客選擇共享汽車接駁出行的概率,同時會減小旅客選擇公交車出行的概率。私家車的系數在共享汽車和公交車的效用函數中均為負值,表明擁有私家車的旅客選擇共享汽車和公交車接駁出行的概率都會變小,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擁有私家車的乘客選擇共享汽車接駁出行的概率比沒有私家車的乘客低6.3個百分點。
單獨出行的系數在共享汽車的效用函數中為負值,并且具有顯著性,說明單獨出行的人選擇共享汽車接駁出行的概率較小。
3.3 日常特征屬性變量參數估計結果
根據旅客日常出行方式數據的標定結果,可以發現日常出行方式為私家車的旅客選擇共享汽車接駁出行的概率最大,而日常出行方式為地鐵的旅客選擇共享汽車出行的概率最小,商務出行的旅客更喜歡選擇出租車接駁出行。
根據駕車喜好和共享汽車熟悉程度的標定結果,可以發現喜歡駕駛與否的系數具有顯著的影響,且系數為正值,說明喜歡駕駛的旅客選擇共享汽車接駁出行的概率更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喜歡駕駛的旅客選擇共享汽車接駁出行的概率比不喜歡駕駛的旅客選擇共享汽車接駁出行的概率高12.1 個百分點。是否使用過共享汽車同樣具有顯著影響,曾用過共享汽車的旅客再次選擇共享汽車出行的概率更大。但是對共享汽車的了解程度對于共享汽車出行選擇沒有顯著影響。
4 結論
本文基于實地問卷調查結果,使用MNL模型對考慮共享汽車的高鐵站接駁出行方式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
(1)目前市場上對共享汽車的使用率和了解程度均較低,而出行者對共享汽車的了解程度越高,選擇共享汽車接駁交通出行的概率越大,因此為推動共享汽車的發展需要加大宣傳力度。
(2)增加共享汽車在高鐵站接駁交通中的使用率,需要縮短共享汽車的業務辦理時間,保持共享汽車的價格優勢。
(3)“高鐵+共享汽車”的場景化共享汽車服務模式具有可行性,隨著接駁距離的增大,出行者選擇共享汽車接駁出行的概率逐漸增大。
共享汽車是一種創新的汽車消費模式,但是目前其在國內市場發展并不完善,在高鐵站接駁交通中的應用仍較少。考慮供需平衡和共享汽車企業正常運營的條件下,研究共享汽車在高鐵站接駁交通中的投放量和車輛調度方式,完善高鐵站接駁交通系統的建設,將是下一步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