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女兒
袁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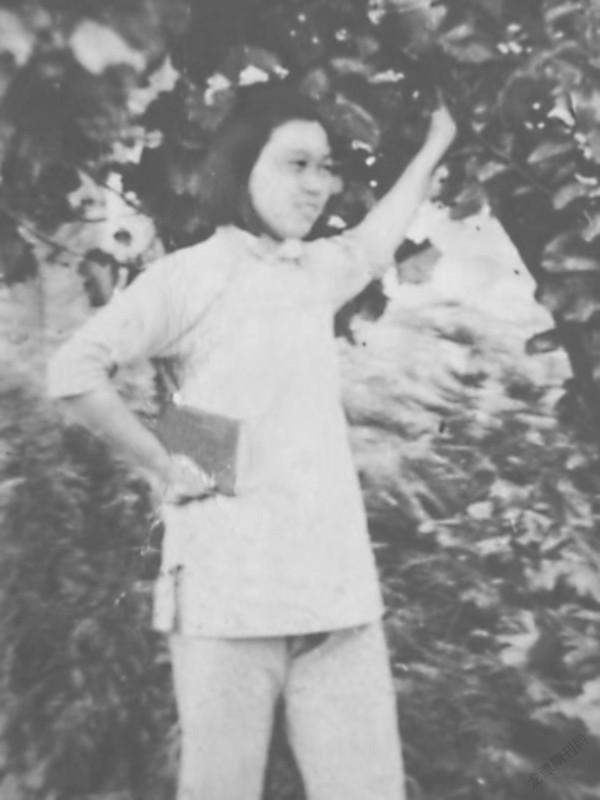
她是一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有81年黨齡的革命戰士;也是今年年初上海46位聯名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并作為10名代表之一在信上簽名的新四軍老同志。她就是我的母親石麗。
熱血青年投身抗戰
1922年1月,我的母親蔣淑云出生于安徽省淮河邊的五河縣蔣吳莊(1949年前歸泗縣管轄)。7歲讀私塾,后在泗縣界溝小學、上塘集小學就讀。她從青少年時期起就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1927年,她的兩個舅舅因參加農民暴動被國民黨殺害,表兄袁瑞生又血灑南京雨花臺。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表兄袁碩生(共產黨員)被釋放回家,在他的影響下,蔣淑云立志要“像花木蘭一樣從軍報國”。1939年冬,她耐心說服父母親和家族長輩,參加了中共領導下的泗縣一區工作隊,并于1940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為避免禍及家人和日偽軍的追捕,蔣淑云和早她幾個月參加革命的戀人袁民生分別改名為“石麗”和“石峰”,一直沿用至今。
1940年5月,石麗第一次離開家鄉、離開父母,和石峰一起參加皖東北區黨委在半城劉圩子舉辦的軍政干部“隨營學校”培訓。石峰是青干班長,石麗是婦女班長。兩個月緊張艱苦的培訓結束后,母親返回泗縣,先后任多個區的婦救會主任。當時泗縣一帶敵我斗爭形勢嚴峻。一方面,縣城已淪陷,日偽軍經常下鄉“掃蕩”騷擾,地方頑固勢力對共產黨的活動相當仇視。另一方面,不少農民不了解共產黨,被敵人散布的“共產共妻”等謠言所迷惑,見到工作隊進村就回避。母親不避艱險,深入群眾扎根串連,對貧雇農和同情抗日的地主、富農、開明紳士等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于堅持反共立場、迫害農民的頑固惡霸勢力,則堅決打擊。在她的動員下,有5名女青年沖破阻力,參加區黨委學習培訓,4個貧雇農青壯年參加泗西區武工小隊。

1942年3月,她與相愛多年的戀人喜結良緣。不久,母親調到泗西區趙集鄉任總支書記,配合時任區委書記兼區武工隊政委的石峰開辟新區工作。泗西區原是敵占區,敵我斗爭形勢復雜,日偽勢力強,群眾有顧慮,開展工作阻力大。減租減息使眾多貧雇農獲得切身利益,是動員民眾擁護抗日民主政權的重要環節。當時有些貧雇農怕工作隊站不住腳,在地主威脅下,白天實行減租,晚上又背著糧食送回地主家。我的外公12歲害眼病,雙目失明,依靠祖上留下的一些土地收租和算命為生。母親以身作則,以民族大義說服父親響應民主政府的號召,對貧雇農減租、減息、退地契。事跡傳開后,不僅提高了她在群眾中的威信,也有力地推動了減租減息運動的進程,受到區、縣委的表揚。
在堅持皖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烽火歲月,母親曾遭遇收編民團的反水嘩變,以及日軍接到漢奸告密后的撲村搜捕。她曾親眼目睹戰友被炮彈炸死在身邊的壕溝里。為了跟上隊伍,不給組織增添麻煩,她瞞過別人,在夜間獨自跑到野外,不停地拼命奔跑跳躍,強行將婚后懷上的第一個胎兒流產。她和戰友們經受住了淮北根據地最艱險的33天反“掃蕩”血與火的考驗。正是在根據地人民群眾的幫助和掩護下,她才死里逃生,躲過了一次次的劫難。
1945年3月,母親被任命為泗縣婦救會副主任、婦委會副書記。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當年12月,母親代表泗縣婦救會,去江蘇淮安參加蘇皖邊區政府召開的華中群工大會,與華中各根據地代表交流群眾工作經驗,還聆聽了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劉瑞龍等領導同志關于抗戰勝利后的形勢和工作的報告。
聽黨召喚砥礪前行
1946年夏,國共和談破裂,國民黨向淮北解放區發動進攻。華中七地委、七分區奉命北撤。石麗和石峰隨隊經泗陽、溧城,進入山東郯城。當時石麗已懷有身孕。不久,國民黨軍隊對山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北撤隊伍在途中常遇國民黨軍飛機轟炸掃射。1947年1月3日,在山東莒縣河陽,母親生下我和哥哥一對雙胞胎。戰爭年代顛沛流離,行軍打仗,生活艱苦,兩個嬰兒早產(7個多月),出生體重一共不足7斤。根據上級戰略部署,華中地區北撤干部繼續向膠東轉移。母親和父親商量,欲將一個孩子托付當地可靠老鄉寄養。但隨行人員堅決反對,他們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難,無論如何必須把兩個孩子保護好、帶出去。”當時華中軍區副司令員張愛萍的弟媳婦也有一個8斤重的嬰兒。母親和她商議后,湊錢合買了一頭架有兩個筐的毛驢,馱著3個孩子翻山越嶺,一路前行。
1947年6月,上級指令華東干部支援東北,父親當時是地委干部隊教導員。母親帶著不滿半歲的我們哥倆,隨大隊家屬行軍,北渡渤海抵達遼寧。隨后父親出任遼寧岫巖縣委常委、組織部長,母親擔任縣機關總支書記。在東北一年多時間里,父母親配合東北野戰軍建立和鞏固民主政府,發動群眾參加土改和剿匪,與當地干部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1949年8月,父母親又接受了新的任務,來到解放不久的上海。母親服從組織分配,先后任職新涇區、大場區、吳淞區婦聯主任和上海市婦聯農村工作部組織科長。她懷著堅定的使命和責任感,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很快就適應了與戰爭年代完全不同的工作環境,投身于上海郊區的新生政權建設、民主改革和恢復發展經濟的各項工作。
1957年6月,母親代表上海郊區婦聯參加全國農業展覽會,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1959年7月,國家副主席宋慶齡視察七一公社,母親當面向宋副主席匯報兒童福利工作、婦女“同工同酬”及托兒所幼兒保護和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此后,因工作需要,母親又由婦聯部門轉到工業戰線,先后擔任上海人民電器廠黨委副書記等職。幾十年來,母親以事業為重,從不計較個人名譽、地位和待遇得失。她先后2次主動讓出晉級機會給其他同志。母親在處級位置上干了28年,沒有一次“晉級”,但毫不后悔。幾次調動工作,領導有意讓她擔任正職,她卻認為自己身體不好,擔心影響工作,主動要求改任副職。
“文革”中,父母親分別在各自單位受到沖擊和迫害。兒女們為父母親擔憂,母親心情坦蕩地對我們說:“我和你爸爸參加革命28年,沒有歷史問題,不要為我們擔心。要相信黨和大多數群眾,你們都要正常參加學校活動。我們的問題遲早終歸會解決。”
與黨同歲初心不改
戰爭年代的殘酷環境和多年繁重的工作壓力,嚴重侵害了母親的身體健康。她患有美尼爾氏綜合癥、神經衰弱、高血壓等疾病,長期服用安眠藥。1979年后,大腿兩次骨折,痛苦難忍。1997年春節前后,失眠、高血壓、心臟病、胃病、腰椎疼痛疾病綜合發作,接踵而來,3個月臥床不起。
但母親熱愛生活,始終以開朗樂觀的情緒,頑強地與疾病作斗爭。無論住院還是在家里,始終保持健康的生活態度,以堅強的毅力對待病魔。從起床到拄拐杖在家里走,從室內到室外下樓,一年后能夠堅持行走兩站路,生活起居基本可以自理。離休后,她積極參加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活動和上海人民電器廠舉辦的發揚革命傳統的座談會,還應邀參加安徽淮北泗縣、五河縣等地組織的抗戰勝利紀念活動。
2000年,母親親自動筆撰寫了4萬字的《我的回憶》。在結束語中,她發自肺腑地寫道:“我參加革命和加入中國共產黨已經60年了,現在年近80歲。在黨的教育下,自己從一個追求理想的農村普通姑娘成長為一個黨的老干部,回首往事,百感交集。60年來的風風雨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經受考驗,無愧于黨的培養和人民的希望。我忠于黨和革命事業,不計較個人得失。雖然體弱多病,但還要繼續努力學習,發揚革命傳統,還要不斷提高思想覺悟。我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定能夠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國。”2006年6月,青梅竹馬、相濡以沫的老伴、老戰友石峰因病去世,母親悲痛欲絕。2010年,89歲的母親又完成近3萬字的《難忘的歲月——相伴六十七年》。這兩篇回憶錄,飽含了她的信仰和理想、情懷和品質,是留給我們子孫后代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2021年1月初,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根據廣大老同志的意愿,代表上海新四軍46位百歲老戰士起草了一份給習總書記的信,從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參與者和見證者的角度,結合自身經歷,敘述了只有共產黨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深切感悟,匯報了離退休以后積極參加黨史教育的情況,表達了傳承紅色基因、永葆政治本色,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的決心。信稿送到母親面前,她老人家欣然地簽上了自己的姓名。
2月18日,習總書記回信,老同志們歡欣鼓舞,市老干部局領導立即到醫院慰問。22日,母親在華山醫院又接受電氣集團慰問組采訪。盡管由于腸胃疾病,喝水都嘔吐,難以進食,連續兩周打吊針和輸營養液,身心十分虛弱,但是她堅持配合慰問組完成近一個半小時的預定采訪程序。她從習總書記回信的字里行間感受到深切的關懷,激動地說:“今年是黨的百年誕辰,也是我的百歲之年。習總書記的回信是對我最大的安慰。我是一個普通的老共產黨員,要不忘初心,永遠跟黨走,將革命傳統一代又一代地傳下去。”
(編輯 李三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