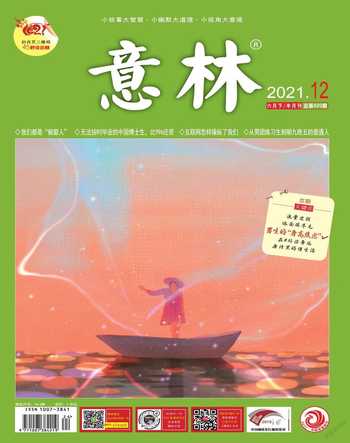掀開(kāi)鐵鍋蓋兒的那股驚喜,東北孩子都懂
王文靜

我對(duì)魚(yú)以及鮮味的味覺(jué)記憶均來(lái)自松花江支流的一個(gè)大水庫(kù)。
水庫(kù)位于連綿起伏的群山腳下,平日里金光閃閃,美不勝收。當(dāng)時(shí)我們喜歡把書(shū)本上一切關(guān)于湖泊的美好想象都放置在它身上。
它們從來(lái)不會(huì)讓我們失望,總是時(shí)不時(shí)地定期造訪。優(yōu)良的水質(zhì)賦予這些魚(yú)純粹的鮮味,人們總是用“與土腥味絕緣”來(lái)形容這種鮮。
每次它們出現(xiàn),仿佛一個(gè)小家庭里的人間盛事,要么貴客登門(mén),要么是一個(gè)平淡無(wú)奇的日子,家中某個(gè)成員突然產(chǎn)生了大飽口福的念頭,并在無(wú)意間獲得了其他成員的積極響應(yīng)。
不管怎么說(shuō),食物帶來(lái)的儀式感通常與人們鄭重的態(tài)度有關(guān),水庫(kù)魚(yú)在構(gòu)成味覺(jué)記憶的同時(shí),也在一個(gè)小孩兒的腦海里建立起一條時(shí)空隧道。
它會(huì)讓家庭氣氛非常和諧,尤其是廚藝較差但自我感覺(jué)良好的一方此時(shí)會(huì)變得謙卑起來(lái),比如我爸。雖然他放棄做主廚總以自己工作累了為由,廚藝精湛卻身為家庭弱勢(shì)群體的我媽絲毫不介意。
小小的我能感受到她的揚(yáng)眉吐氣,拎著一條水庫(kù)魚(yú)大步流星地進(jìn)入廚房,腰板始終挺得倍兒直,她知道,等她大功告成,我們所有人都將臣服于她的圍裙之下。
我們都要特別感謝那個(gè)灶臺(tái),是它讓這種傳統(tǒng)烹飪方式充滿辨識(shí)度,無(wú)論從嗅覺(jué)、視覺(jué)還是味覺(jué)上。灶臺(tái)上的大鐵鍋氣勢(shì)威嚴(yán),鐵鍋上方的墻壁往往是供奉灶王爺?shù)牡胤健?/p>
終日與慈眉善目的神仙相伴,大鐵鍋?zhàn)匀欢δ咳荆闪宋覌尩牡昧χ帧0做栆埠茫庺~(yú)也罷,從水庫(kù)打撈出收拾妥當(dāng),隨即被她放入蔥花熗鍋后的大豆油中。
在大醬還沒(méi)有向灶臺(tái)魚(yú)進(jìn)軍的年代,“貓把乎”,也就是藿香,統(tǒng)治灶臺(tái)魚(yú)的世界。這里的人們甚至形成了一種嚴(yán)苛的標(biāo)準(zhǔn),灶臺(tái)魚(yú)就是要跟藿香在一起,永遠(yuǎn)不分離。
我的任務(wù)是為我媽采摘藿香。
藿香大多野生,不知什么時(shí)候就在園子里迎風(fēng)招展。為了博得幾分關(guān)注,它們通常把家安在最受歡迎的葡萄架旁邊,這樣人們?cè)谄咸鸭芟鲁藳觥⑼嫠#蜁?huì)注意到藿香了,哪怕它的味道是那么讓小孩子一言難盡。
還好有灶臺(tái)魚(yú),藿香很快實(shí)現(xiàn)“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夙愿。在大鐵鍋里添加涼水之后,就和姜片、白醋、白糖一起幫助灶臺(tái)魚(yú)進(jìn)行滋味的提升。
香味就是從這時(shí)候彌漫了整個(gè)廚房,散發(fā)出灶臺(tái)魚(yú)的信號(hào)。當(dāng)然,還要感謝那些柴火,否則大鐵鍋不會(huì)釋放出自己的威力和魅力。
小時(shí)候,大鐵鍋對(duì)于一個(gè)小孩兒來(lái)說(shuō)是一個(gè)巨大的、驚喜的、神秘的存在。僅憑一己之力,你總要花費(fèi)很大力氣才能掀開(kāi)那只大鍋蓋。可是你又知道,當(dāng)你掀開(kāi)鍋蓋的一瞬間,一定有期望中的美味等待著你,驚喜就是,這種美味往往又超出你的期望值。
有時(shí)候,我們也會(huì)為灶臺(tái)魚(yú)加入一些配菜,粉條和豆腐,它們真是托了魚(yú)湯的福,平淡無(wú)奇的小綠葉立刻變得神氣活現(xiàn),總有人另辟蹊徑避開(kāi)那條魚(yú)向它們發(fā)起猛攻。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充滿挑戰(zhàn)的人生,在吃完兩個(gè)玉米餅之后,果斷要了一小碗白米飯。當(dāng)然,理由無(wú)非是:魚(yú)湯這么美味,你們?cè)趺纯梢岳速M(f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