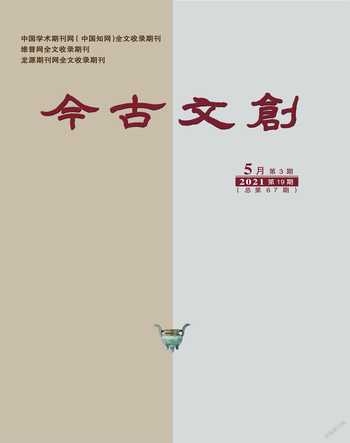抵抗、妥協、混雜
米微微 胡東平
【摘要】 后殖民主義思潮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其理論基石是顛覆二元對立的西方哲學傳統的解構主義。這場思想運動充滿著被殖民者對殖民文化霸權的負面情緒,一種是絕望,反映到翻譯活動中帶來的是妥協式的翻譯策略;一種是憤怒,帶來的是抵抗式的翻譯策略。妥協策略的代表是巴西食人主義翻譯,抵抗策略的代表是異化翻譯策略,霍米·巴巴的混雜性翻譯是異化策略的進化。
【關鍵詞】 后殖民主義翻譯;解構主義;食人主義翻譯;異化;混雜性
【中圖分類號】H315?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19-0114-02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從‘違和’到‘維和’:翻譯和諧倫理研究”(17ZDB12)。
一、引言
在后殖民時代,文化殖民策略被西方國家廣泛應用于第三世界。后殖民主義翻譯旨在破除殖民統治過程中殖民話語對自身的美化和對被殖民地歷史文化的歪曲,消解殖民統治給被殖民者帶來的自卑情緒,對本國歷史文化追根溯源,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其理論核心是權力關系。后殖民主義雖然是西方理論,卻被后殖民國家拿來作為反抗西方殖民霸權的武器。本文將分別分析后殖民主義的定義、其理論基石解構主義的誕生于發展、以及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與策略。
二、后殖民主義的定義
“后殖民主義”這一術語首次被正式提出是在印度學者斯皮瓦克于1990年所著的《后殖民批評家》中,斯皮瓦克是接受西方殖民者教育成長起來的殖民地土著,后殖民主義這一術語由這種身份背景的學者正式提出有歷史必然性。雖然“后殖民主義”一詞誕生于九十年代,關于后殖民時代相關文學理論的研究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
60年代以來,隨著美蘇兩極爭霸的冷戰格局建立并逐步升級,為了增加盟友數量和規模、擴大影響力輻射范圍、在全世界推廣自己的價值體系以對抗彼此,在兩個超級大國的支持下,第三世界諸多前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聯合國成員從五十多個國家增加到近兩百個。傳統歐洲帝國主導的全球殖民體系逐步瓦解,那些擺脫殖民統治取得民族獨立的國家便是后殖民國家。后殖民主義自誕生起,內涵和中心就在不斷變化,以適應不同的歷史時期、地理區域、文化定位、政治立場、國家民族地位以及文藝發展。到70年代初期,隨著各種西方思潮的涌入,尤其是解構主義的和文化學派,后殖民研究逐步發展成為一種多元文化批評理論[1]。后殖民主義借助了福柯的“話語——權力”關系理論,著眼于宗主國和前殖民地之間的話語關系,包括后殖民國家的新文學發展,后殖民國家本土話語權的構建和西方中心主義在后殖民時代面臨的挑戰和話語權消解。
三、后殖民主義的理論基石——解構主義
后殖民主義的理論基石是顛覆二元対立的西方哲學傳統的解構主義。20世紀60年代,從歐美的新左派運動到蘇聯的赫魯曉夫改革,全世界都在經歷社會變革,激進的思想不斷產生和發展。1966年,雅克·德里達在一次結構主義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向結構主義發難,標志著解構主義的誕生。他的思想與西方主流哲學格格不入,但當時的時代背景為其提供了絕佳的傳播土壤,其產生與擴散具有政治必然性。
解構主義批判了傳承兩千年的傳統西方哲學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二元對立、形而上學等思想,從內部瓦解了主宰西方思想近千年的哲學傳統。邏各斯中心主義堅持的“中心”導致了具有等級差異的二元對立的形成,例如種族對立中的本族優于異族,誕生了西方種族中心主義。解構主義認為事物不存在一個固定的、先在的本質,一切概念的意義都是變動的、不確定的。西方傳統哲學理論中的絕對對立的二元論和中國傳統哲學中相互包容互相轉化的二元論有著本質的不同。
解構主義思想體現在翻譯中,強調“存異”而非“求同”,其方法論引導和啟發了其他后現代文學理論,對翻譯中的政治權利問題的探討逐步發展為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翻譯被認為是構建殖民體系的工具,傳統的“忠實”翻譯觀是殖民統治的幫兇,殖民話語建立在西方/東方、文明/野蠻等對立之上,通過翻譯的歸化和去歷史化建立西方中心主義[2]。
四、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的演進
后殖民主義思潮是一場充滿情緒化的思想運動,比顛覆西方哲學傳統,以反抗權威為主旨的解構主義更加極端和叛逆,充滿著被殖民者對于殖民者文化霸權的負面情緒,本文將后殖民學者對于西方文化霸權的叛逆情緒歸為兩類,一類是絕望,這種情緒反映到翻譯活動中,所帶來的是妥協式的翻譯策略;一類是憤怒,帶來的是抵抗式的翻譯策略。
(一)“食人主義”翻譯理論
妥協式后殖民主義翻譯策略的代表是巴西“食人主義”翻譯,來源于巴西土著民族的食人儀式。在巴西食人族的傳統文化中,他們通過吞食強者來吸收他們的力量,這是行為是出于對被吞食者的尊敬向往和對自身的不自信的心理。巴西獨立之后,文化依然依附于歐洲殖民者,巴西翻譯家德坎波斯提出食人主義翻譯思想,認為巴西文化只有“吃掉”歐洲文化才能重塑民族文化身份,吸取來自殖民文化的精華,將使譯文的生命更加鮮活[3]。食人主義不但不拒絕外來影響,而且認為弱勢文化應該采取食人的方法來翻譯強勢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2]。
“食人主義”翻譯是建立在對歐洲文化的崇拜以及堅定地認為歐洲文化全面優于自身本土文化的基礎上,這種認知的前提是相信本土文化劣于歐洲文化且無論如何競爭不過西方中心文化,因此需要本土文化以歐洲文化為樣板去學習和改進自身文化,這是一種處于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恐懼而幾乎算是放棄抵抗的妥協式策略。
(二)“異化”翻譯理論
抵抗式后殖民主義翻譯策略的代表是韋努蒂提出的“異化”策略,這頗為諷刺,因為韋努蒂是西方中心文化的一員,他提倡的異化翻譯也不是處于弱勢文化的立場,而是站在強勢文化的立場上所做的自我反思式的思考。但是無論如何,就像西方學者提出的解構主義啟發了殖民地學者的后殖民主義思潮,西方翻譯界誕生的異化翻譯也給后殖民翻譯提供了抵抗工具。
韋努蒂認為譯文和原文的不連貫是文本背后權利關系不平等的體現,他反對譯者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掩蓋譯文的混雜性,以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為標準塑造外國文化作品的歸化翻譯阻礙文化間的平等交流。異化翻譯策略因此會故意用不通順流暢以及非慣用的表達方式,抵抗強勢文化的同化,使“失語”的東方文化能夠在文化交流中發聲。
(三)文化第三空間——雜合翻譯
后殖民主義第三大翻譯策略是霍米·巴巴的“混雜性翻譯”理論。“混雜指的是在話語實踐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只要你的狀態”[4],乍一看像是妥協式的翻譯策略,深入了解后會發現,雜合是異化策略的進化。
“雜合”這一術語最初指不同種的兩種生物雜交產生的后代,中國人最熟悉的是農業領域的雜交水稻。巴巴提出了翻譯中的雜合概念。在他看來,后殖民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含有殖民文化的影響,后殖民文學是本土語言和殖民語言的雜合體[5]。和“食人主義”只關注土著語言對殖民語言的吸收不同,土著語言也會影響殖民語言,他們相互混雜,難以劃分,形成文化的“第三空間” [6]。這個“第三空間”并非是兩種對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而是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相互滲透的地方[4],這個空間內不同文化交流、斗爭、創造。
巴巴的“混雜性”翻譯策略追求殖民文化的自我解構和土著文化的自我彰顯,對解殖民化有積極意義。在文化反霸權的斗爭中,放棄抵抗的妥協式策略固然不可取,但強橫的抵抗也有悖于文化間平等有效交流的目的。合適的做法是采取混雜翻譯策略,根據實際需求靈活選擇具體翻譯策略。
五、結語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獲得全面勝利,中華民族取得了民族獨立,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半殖民統治結束。然而,政治和軍事的獨立不代表經濟、文化等的全面獨立,尤其是在民族文化上,中國依然受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響,文化上的去殖民化尚未完成。在此之前,所有后殖民主義研究所探討的前殖民國家與獨立的后殖民國家之間的權利關系時,后殖民國家永遠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因此后殖民學者所提出來的翻譯策略要么是妥協性質的,要么是極端反抗性質的,要么就是放棄陣地(文化純度)開辟新陣地(第三空間)。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中國的總體實力已經在可預見的近未來即將與傳統的殖民勢力達到權利的平衡,甚至是超越。一個后殖民國家,即將在歷史上首次在綜合力量上超過文化中心的西方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后殖民主義的研究將走向何方,這將是中國的發展為后殖民研究以及翻譯學界,帶來的新視角和貢獻。
參考文獻:
[1]謝天振.當代國外翻譯理論導讀[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455-457.
[2]Robinson, Douglas. “Post Colonial Studie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St. Jerome, 1997:8-30.
[3]劉軍平.西方翻譯理論通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569-570.
[4]趙稀方.后殖民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08-109.
[5]陸巍.混雜性[J].國外理論動態,2006,(05):60-61.
[6]Bhabha, Homu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
作者簡介:
米微微,女,河南鄭州人,碩士研究生在讀,湖南農業大學,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胡東平,男,湖南益陽人,博士,湖南農業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