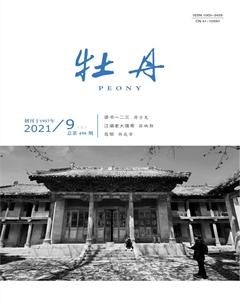白水有個樓背巷
奚同發,中國作協會員,河南省作協理事。出版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隨筆集等多部。作品入選各種年度選本,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等多家刊物轉載。曾獲全國年度小說評獎一等獎、《小小說選刊》三屆優秀作品獎、河南省文學獎、首屆河南省文學期刊獎等。
前些天,在朋友圈看見侄孫朗誦《我驕傲,我是中國人》的視頻,我告訴侄兒,詩歌作者王懷讓生前與我是經年好友。早已住進白水新居的侄兒傳話給小家伙,小家伙立刻“百度”了我與王先生,于是興奮極了,朗誦得更加起勁,聲情并茂……
一
1999年11月26日,《河南日報》發表了我寫白水的隨筆《故居的老巷》,那時報社的文藝處長正是著名詩人王懷讓,編輯包括如今的河南日報報業集團副總編高金光、省作協副主席張鮮明等文壇名將。
《故居的老巷》是我筆下第一次實名出現白水,其中的老巷指的是縣城南大街的樓背巷。在這之前或之后,我的小說世界肯定有不少對白水或零散或改頭換面的書寫,以至于故鄉在我的印象中有可能是虛構而不真實的。如果說一個作家的童年對他的創作起到決定作用的話,那么白水在我的童年是缺失的……
2017年的一天,大哥打來電話,說老宅和我筆下的老巷要被拆除,根據相關文件,屬于城中改造范疇。
一時間,我坐在書房,大腦一片空白,手足也無處安放,只有目光在兩塊“白水軒”的匾額之間來回逡巡。一塊掛在門額之上,系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且會前受到毛主席接見并征求意見的黑丁先生題寫;一塊掛于北墻書柜之上,由曾書寫了《軒轅黃帝之碑》《孔子之碑》《詩圣杜甫之碑》及韓愈、李商隱、司馬光等眾名人碑刻的李鐵城先生題寫。
什么也不能說了,大哥用平穩的口氣道出的是一個急迫的信息。那么,“五一”節前是否會被拆?應該不會吧!大哥這句并不肯定的答復讓我心頭發緊,腦海中頓時浮現出杜甫《彭衙行》中的詩句“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那其中因為想念“高義薄云天”的白水孫宰孫縣令,而生翅插翎立即飛往的焦急想象,正切合了我的要害。但愿吧!畢竟事發突然,也只能給自己一個模糊的心理安慰。
就這么定了!無論“五一”有什么事情,也必須給“回家”讓道。
這個家,對于我們離開白水的人,稱之為故鄉。她承載了家族一代又一代的生命與煙火的過往,銘刻著你我他的成長記憶,且是我們一代作為孩子的集體回望,時光隧道中處處能感受到歲月的氣息與基因。她是我們生命的原點與來路,哪怕東倒西歪、殘垣斷壁、余存片瓦,無論何時何地,我們也能不約而同把目光向她聚成一束——即使漆黑之夜,歸來時不用燈火也可以憑感覺慢慢走向她,直至輕扣門扉。如果漂泊異鄉飽受狂風暴雨,她,則完全可以在想象中把一個游子石頭般的心溫暖融化。這個家,被我們常常稱之為老家,是一個人的當初,是一個人站在人生舞臺上的背景,是一個人立足的根基,是一個人的堅實和信心。
我們無法抗拒自然衰老,卻對猝不及防的人為變故難以接受。如果老宅真的老到傾覆坍塌,相信大家不過是些許留戀與傷懷,“立新”肯定才是最重要的話題——在原址上蓋起新房,甚至比原來更氣派更有規模,有什么難的?如當年父母所言,有人在,什么都不怕。所以,才有了我們兄弟四人的階梯誕生和成長。可是,現今是統一拆遷,一個遷字,讓一切本質發生了改變。老宅一旦被拆除,她的過去,將被架空成想象和記憶,甚至從另一個意義講,有可能是對相關的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一次人為清除。那回眸的鄉愁,將連根拔起,無論是根與須,必被時間無情地曬干,后人與后人只能在陌生的文字或影像中漸漸忘卻。
但,瞬間便想通了,這就是時代,就是社會,就是進步與發展!當新的黎明和曙光到來的時候,我們應該欣然接受,并張開雙臂熱烈地去擁抱。
二
急忙聯系西安工作的二哥及侄子和銅川工作的三哥一家,以及河南漯河工作的侄女一家、尚在武漢念大學的兒子。“五一”回白水,成為大家共同的目標和急切的心愿。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困難,但說什么都是贅言。一旦老宅消失,想以此為背景拍一張全家福也不再可能。
與大家一一溝能的同時,后悔的情緒漸次彌漫周身!這么多年,在父母相繼離世后,兄弟幾人及家小竟沒有在老宅聚齊過。先是老宅空置幾年,有一次我回去,院內荒草一人多高,而后大哥調動工作回到白水,重新進住,終不如父母在時的方便,又因兄弟幾人天各一方,生活中總會出現不同狀況而影響全部到場的可能。許多事情,常常因為我們的“拖延”而造成無法彌補的缺憾,人生最大的錯誤之一就是,我們認為我們未來有的是時間……
聯系就緒,時間與空間瞬息靜止、凝固,心里空落落的,身子輕飄飄的。從書架上找出我的首部隨筆集《浮華散盡》,翻至《故居的老巷》——此文當時一經《河南日報》推出,《中華新聞報》《東方家庭報》《汕頭都市報》等國內各地報刊紛紛轉載,曾引起許多讀者共鳴。此刻捧書于手,一邊輕聲朗讀,一邊淚水熱熱地滾了一臉……
我故鄉老宅所在的巷子,絕對可以稱為老巷,至少有上百年歷史。說起來,離唐代詩人杜甫的縣尉舅父崔頊的府第及后世幾代縣衙設址不遠。
據老人講,老巷原是為清朝一位進士家專門修的,書有進士字樣的匾額一直掛到被“四舊”破走(這一點,還聽曾親眼目睹的中學老師郗進誠先生提到——他當年在白水中學上學)。
我家老宅位于巷子深處,居于同時一線磚砌的三孔窯洞之中。相傳當年一般人家多為土坯建材,或基礎以磚、腰以上土坯,磚石結構一孔極為不易,富不過兩孔,且要小得多……東邊本家系三五代前同祖,西邊則幾易其主。如此說來,這兩孔窯洞是進士昔日深深庭院的最后遺產,雖歷經滄桑,軒昂之勢絲毫未減,反而一派沉雄古拙、質樸渾厚、穩健從容的氣象,猶如一位久經歲月的老人,一紋一皺里都寫滿故事,給人以踏實與度量的仰視感。每一孔窯洞八米多長、五米多寬、近六米高,主體由灰磚自平地疊層構成,內里弧形粉以白頂,門與窗的拱券則裝飾著曲形磚石。前門后戶,實木寬板,尤其厚重的對開前門啟閉之間“吱呀”聲響,傳出去很遠。除了冬暖夏涼的窯洞,前后尚有二十四米長、近六米寬的一大一小兩座院落,讓人可以想象當初家景的殷實。
住在這兒的人總要一代代傳說老巷昔日的輝煌,也會為進士后人在衰敗中把房舍一塊塊發豆腐般賣掉、最終老巷成為大家的公用巷而嘆息。
父母一輩對老巷的記憶要比我們深刻,尤其父親大部分童年在此度過。我大學期間回去,巷內尚生活著一位父親童年的伙伴,須發如雪,慈眉善目,子孫繞膝……因父母過世早,我父親幼時隨叔伯生活多年,爾后離開老巷出外謀生,成年回來,同行的還有我的母親。
我出生在七八十里外的鴨口煤礦,乃父親工作之地,多年后因路遙小說《平凡的世界》創作原型而名聞天下,不僅建了路遙文學館,還以小說中的大亞灣煤礦命名酒店、商鋪,文學的力量和精神之外的實用功能,頓時滋養了同時代的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包括鴨口在內的一條渭北儲煤帶上,自西向東延伸著一座接一座新中國成立后興建的礦井,來自各地的農民后生因此變身為工人,而他們的另一半及子女,還生活在原籍,從而形成特有的“一頭沉”家庭。母親經常帶著我的兄長在礦區與故鄉走動,當時最作難的是到鴨口一家人的安住——好在,工友們不約而同自覺去尋找上班工友的宿舍“打游擊”。直到戶籍落至礦上,父親憑一己之力,利用工余時段在荒山溝畔一把镢頭一把锨硬打出一孔土窯,一個家人才算安定下來。據說,與父親同時掘土挖窯的幾位工友,多半中途而廢,足見父親的心勁兒與不易。
待老宅真正進入記憶,我儼然一個隨父歸鄉探親的少年郎。那時的樓背巷,巷口是兩家藥房,連排板門、木格窗欞、高屋脊、獸頭瓦當流水檐,一列列藍瓦間散布著塔形瓦松和蓬勃的蒿草。巷內的石子路面破爛不堪,兩側四五米高圍墻的深宅大院,加上巷道有一定彎度不能一目了然,雖長不過兩三百米卻顯得悠遠而深邃,神秘而幽靜。
中學時再回去,巷內老戶僅余五六家,由于北邊一家被征用蓋了某單位家屬樓,并且縣中學曾以磚墻封閉的校門再度打開啟用,出入的人多起來。路面重鋪了黑亮的柏油,夾道人家開了雜鋪、小攤,上學放學之際,成群結隊的學生熙熙攘攘。彼時,人們生活走向富足,開始享受改革開放的初步成果,老住戶的門房修得高大而漂亮、現代而又不失古典。水泥預制板為骨架的門樓雨棚,粘著白色的瓷片。屋頂周邊磚砌護欄,鏤空作寶瓶形、葫蘆形,最簡單的是菱形。朱門正面除了齊整的門釘,還貼了門神或福字,兩邊配以紅底墨字的對聯,內容或對時代的歌詠,對社會贊譽,或對孝悌仁義善美的傳統稱道宏揚,好詞佳句,比比皆是。
撫今思古,物是人非,昔日的一家興旺早已散去,化作眾人的繁榮、大家的昌盛,這是否預示著某種生活的啟示和哲理?或許正是這種啟示和哲理,老巷在父親心中一直是最美好的存在,無可替代,以致彌留之際惟一的遺囑是魂歸故里。那以后,我回老宅的機會明顯增加,樓背巷由此成為我在白水縣城走過最多的一條小巷。時不時像父親生前一樣站在巷內回憶他的過去,似乎要把往事與墻壁上此磚彼瓦的標記對號起來。母親則在我往長春讀大學時離開煤礦,獨自住回老宅,直到過世……
工作在外,回去少了,對故鄉的懷念愈加強烈。老巷的滄桑使我循著她的軌跡,在以進士的后裔衰敗來教育孩子時,也不免要想起張若虛的詩句:“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因為這種懷念,從那篇《故居的老巷》開始,我與“白水”這個詞條也由起初僅僅填寫表格“籍貫”而生發出更緊密的關聯,如書房名“白水軒”,印章“白水奚氏”“白水軒主”等多枚……為了對既熟悉又隔膜的故鄉更深入了解,還特意找來《白水縣志》置于案頭,作為日常必備。令我大喜過望的是大哥淘到了八卷本的《渭南歷史通覽》,外包布袋油跡斑斑,但書籍本身沒有受到傷害。后來,白水縣志重修,編撰人員通過兄長聯系到我,希望我提供材料以便納入,我雖心存忐忑,終是本著尊重編者的態度接受了。
三
2017年“五一”小長假,我們一家三代計二十四人,自八方返歸。老宅的窯洞和院子,迎來人口最多的一次團聚。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簡單,又那么觸目生情,充滿儀式感!陳年過往,如黎明前的海潮,慢慢浸來,橫無際涯。印象中高大寬綽的老宅,在大人的接踵摩肩與娃兒的大呼小叫聲中顯得逼仄,但是氛圍和現場卻勾起一幕幕久違的感動。那一磚一瓦,處處寫滿不舍,哪一個角落能不引來一番回憶……兄弟幾人禁不住雙目濕潤,歲月留不住的青春,日光掩蓋不了的成長,果真把成人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讓人生成為一場有來無回的旅行……在許多人家撤離后一片狼籍中,大哥默默手執掃帚,一遍又一遍,屋里屋外,轉彎抹角,清掃得一塵不落……
道別時,大哥鄭重其事地把兩塊磚遞給我——三哥說,是大哥耗時一整天小心翼翼又磨又鋸、輕敲慢刷,才拆下了八塊,分予兄弟四人,作為對老宅永久的紀念——人在哪兒,似乎老宅就在哪兒了。它們曾鑲嵌在老宅窗楣、裝飾著窯洞的前臉;曾在雨的夜,讓一條條水線滴滴答答伴著我們入眠;曾在風和日麗,美著一院子風景。它們既像一個久久的古老的象征,又像一個沉沉的心事的傳說。它們的曼妙曲線似一座座微型拱橋的身段,如今那么委屈地收斂著,昔日的莊嚴不再,肅穆盡失,體面全無。一顆顆淚珠連綿地自鼻尖緩緩滑過,濕在它們身上,兄弟四人彼此無語,相對默然。除了這八塊,其他與他們共度百年的伙伴,不久只能粉身碎骨、無形于世。來生遙遙,可再有相期之日……未來的曉風或殘月,老宅的一木一土、一門一窗,假以夢中有約,不知是否如許赴會?
侄子拆下的藍底白字的門牌號和一對黑色的鐵質螺紋門環,也被我一并帶走,擺進書房,成為最重要的收藏。這個門牌號上,曾駐留過多少人的目光,儲存了多少人間的密碼?這對門環,曾被多少親人扣響?以后晃動它們,就如同站在老屋門前嗎?
回到鄭州沒幾天,便看到侄子發來的視頻——老屋夷為平地,一片碎瓦磚礫。二哥嘆道,只有學校的水塔還能幫我們找到家的方位,其他皆無辨識……
老宅和樓背巷,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了。
眼前那張前后四排二十四人的全家福,大人與孩子的表情,訴說著各自世界內心的迥異。背后門樓及門縫里或隱或現的景象,就這樣被時代的車輪瞬間粉碎,虛幻到恍如隔世。而我能做的,卻只有左手右手各執一個再也無法扣響的空空的門環……
大哥及子侄搬進電梯洋房,通透的藍寶石玻璃窗,潔凈的大理石地板,雪白的墻壁,寬敞的客廳與緊湊的臥室,有限的空間得到最合理的分配與布局。廚房、盥洗室的水龍頭代替了往日桶裝缸儲,抽水馬桶、熱水器、空調等,讓昔日的一個又一個生活難題不再為難。一切都是嶄新的、現代的,夢境一般,讓人們前所未有地享受到工業時代及后工業時代所帶來的便捷與舒適、時尚與美好。
與此同時,坐在陽臺上,受限于鋼筋水泥的束縛,又難免懷念起木格窗欞、橫磚豎瓦的深宅大院,朝夕腳踩土地的踏實,身披雨露與陽光,推門閉窗間伸手可及的自然風景。心頭不免時不時涌上一絲淡淡的惆悵與落寞。如此密集的疊層人家,彼此距離近了,心與情感卻遠了,或完全陌生化。多年來舉足串戶、自家一樣隨便的農耕時代的鄰里關系,被徹底改寫。不僅窗戶裝了防盜網,有點作繭自縛之感,而且門口的防塵墊,入門換鞋的小節,阻擋了多少來者的腳步,更弱化了彼此走動的欲望。據說,有的老人,在陽臺上用花盆種了菜或莊稼,而有的老人被太過干凈的地板驚到,即使自家走路,也躡手躡腳,如履薄冰……她們懷念當初院內石礅或門坎前盤腿而坐,面前一個針線筐,或一把兩把待摘分的菜蔬,西家長東家短無拘的笑聲碎語的某個夏日……
一個時代結束了,新的時代到來了,什么也不能阻擋中國進入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一個小家,正被時代的洪流裹挾著前進,前進,前進!關照到每一個個體、每一個個人,又豈非如此?
不久的老宅原址,一定會林立起片片嶄新的大廈高樓,花園綠地,水流鳥語,迎著陽光,欣欣向榮。
白水,我的家鄉,無論身處何時何地,心中裝的只有一個念想,唯愿您好!祝福白水!祝福故鄉!
責任編輯 ? 楊 ? 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