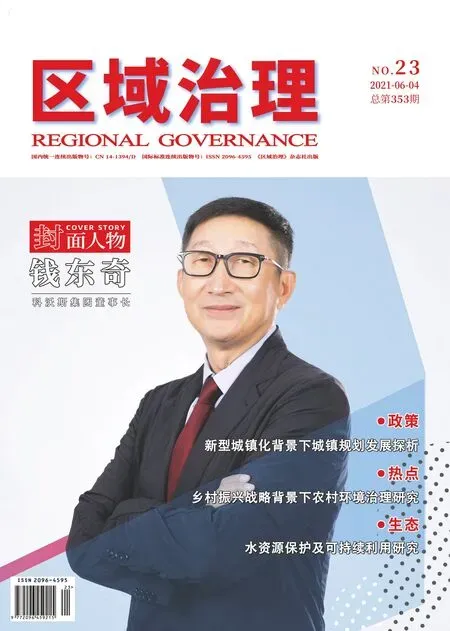探析老齡化進程中老舊社區(qū)公共空間的設計現(xiàn)狀*
蘇州大學城市學院 張智程
一、老齡化進程中老舊社區(qū)的問題
齡化進程中不僅僅是人在改變,社區(qū)也在隨著時間改變,我國20世紀末開始的社區(qū)改革沖擊了傳統(tǒng)的鄰里關系。社區(qū)中鄰里關系的淡漠導致了社區(qū)缺少活力,它們沒有健全的物業(yè)體系,沒有相對很好的綠化,規(guī)劃與設計上雖然公攤面積很少,但是沒有足夠的公共活動的空間。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汽車已經(jīng)成為城市中常見的交通工具了,社區(qū)公共空間常常會被臨時替代成停車位或是停車場,不僅給社區(qū)使用者帶來不便,而且給年長者的出行和活動帶來阻力。綠化景觀太過于注重形式感,忽略了實用性,景觀硬化多為直角,缺乏安全性。公共區(qū)域種植喬木與景觀小品,但是不足以達到遮蔭效果,使得一些可以休息的區(qū)域直接暴露在太陽底下。
總體來說,道路、社區(qū)公園、綠化景觀都存在一定的不健全,是當下需要解決的問題。傳統(tǒng)鄰里中的社區(qū)公共空間改造是以重拾傳統(tǒng)社區(qū)公共生活為目標,通過這一模式改善社區(qū)公共空間體系。通過對公共空間的構成要素進行歸納梳理,主要策略遵循追求公共空間為先、高密度、可持久性、可拓展性、生態(tài)優(yōu)先、人文關懷、促進交流等原則。其次,“在地老化”的高齡者對公共空間的使用也有一定的需求,包括對電梯的需求,政府方面也是很重視。
二、老舊社區(qū)改造現(xiàn)狀
老舊社區(qū)目前居住人群涵蓋了“在地老化”的高齡者、需要學區(qū)的家庭和CBD附近的租客。本文探討的是“在地老化”的高齡族群在老舊社區(qū)中的現(xiàn)狀與設計介入的方法,從而發(fā)現(xiàn)老齡化進程中設計給老舊社區(qū)帶來的改變。
關于老齡化,美國借助自己雄厚的經(jīng)濟實力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二十世紀60年代為起步階段,以護理服務的老年公寓為主;20世紀70年代為發(fā)展階段,大量老年建筑及社會養(yǎng)老設施開始興建,老年社區(qū)剛剛興起;20世紀80年代是成熟時期,經(jīng)濟穩(wěn)定增長,護理型社區(qū)過度開發(fā),形成了完整的養(yǎng)老體系;20世紀90年代為成熟后期,養(yǎng)老社區(qū)內設施種類更加齊全,包括獨立式公寓、介助式住宅、介護市住宅等;二十一世紀以來進入深入完善期,單一住宅式向多元社區(qū)式發(fā)展。這種完善的服務不會脫離群體進行交往活動(SusanB.Garland,JuleThompson,2012),可以減少獨處時的寂寞感(KatherineA.Marx&KaseyL.Burke.2011)。
日本是亞洲步入老齡化社會最早的國家,為了確保居住的安定性,也提供許多日常生活照顧服務,比如短期照顧、生活咨詢及緊急應對等。依照制度實施主體來劃分,日本公有高齡者住宅具有三個特征:(1)無障礙環(huán)境,(2)緊急通報系統(tǒng),(3)生活援助員。在多元化發(fā)展中,大量興建老人福利設施,加重了財政負擔,雖然滿足了老年人生理上的基本需求,但是阻隔了他們與家人朋友之間的情感,不能滿足他們參與社會的意愿,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末,日本積極推行了“住宅化”“社區(qū)化”改革,以家庭養(yǎng)老為中心,結合老年福利體系,以社區(qū)老年服務為補充的老年服務模式。
我國老齡化起步比較晚,養(yǎng)老服務體系還不夠健全,尤其是社區(qū)養(yǎng)老和社區(qū)養(yǎng)老配套服務方面。在《老年居住環(huán)境建筑》中,胡仁祿對老年人居住面臨的環(huán)境問題鼓勵“多代同居”,完善傳統(tǒng)的家庭養(yǎng)老模式。王江萍在《老年人居住外環(huán)境規(guī)劃與設計》中基于老年生理、心理、行為的需求特點,重點分析了老年人在戶外空間的行為。在養(yǎng)老無障礙設計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如陳佳緯和墨琳《主動式混合社區(qū)養(yǎng)老模式初探》《養(yǎng)老設施建筑設計標準》,這些規(guī)范和書籍中所介紹的養(yǎng)老空間和其他相關功能空間的設計原則與方法可給予我們在養(yǎng)老社區(qū)公共空間設計的借鑒。
在過去,城市老舊社區(qū)的改造運用的是一種簡單粗暴、大規(guī)模進行推倒重建的模式,與拆遷似乎沒有什么太大的差異。這種改造方式的弊端逐漸被大家熟知,微改造這種新模式的優(yōu)點在于首先基本不改變社區(qū)的建設格局,而是對建筑進行局部拆建,對外部老化進行修繕,進行功能轉換,對社區(qū)文化進行保護,對綠化景觀進行豐富,對公共基礎設施進行完善等,一般應用于目前的使用功能與周邊不協(xié)調、利用率低且整體環(huán)境不合格,在實施后基本不會影響城市整體建設格局的地塊。
三、老齡者對公共空間的需求
高齡者社區(qū)公共空間選擇必然要與鄰里社區(qū)空間有所關系,公園綠地為社區(qū)中最為重要與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間,2002年,臺灣師范大學教授林佳蓉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活動的安全性是阻礙老人參與休閑活動因素之一。大多高齡者會將家附近的空地與公園作為休息場所,故活動場地的方便性與安全性皆為老年人外出活動的重要考量。老齡者的活動空間大多以社區(qū)中的公共空間為主,而社區(qū)公共空間又是社區(qū)中重要的公共環(huán)境,需求比例大于其他場所,因此老齡化進程中社區(qū)公共空間的設計應給予必要的重視。
與此同時,高齡者養(yǎng)老問題也是社區(qū)需要關注的,大部分學者提倡建立在社區(qū)的基礎上長期照護,也有提倡以家庭為本的社區(qū)服務長期照護。在一定程度上社區(qū)是整個長期照護模式的核心,要以社區(qū)為依托堅持共同建設原則。社區(qū)的形式大致分為傳統(tǒng)型社區(qū)與現(xiàn)代型社區(qū)。傳統(tǒng)型社區(qū)為在農業(yè)社會中具有血緣關系的人集聚在一地共同生活,每一個個體的各種生活需求,可從家族或者部落等組織中獲得保障與滿足。而現(xiàn)代社區(qū)的居民追求多元化的共同生活利益,對生活品質有要求,因此社區(qū)中的居民彼此間需要互賴、互助、互惠。社區(qū)公共空間包括社區(qū)內的自然景觀、廣場、活動場地、公共綠化、庭院、道路與步行空間以及其他向公共開放、進行公共活動的輔助空間。當社區(qū)中的公共空間不夠理想時,老年人一般會選擇必要性活動。當外部環(huán)境相對改善和提升時,必要性活動時間就會隨之增長,同時,自發(fā)性活動和社會性活動發(fā)生的可能性也會大大增加。場所是有著明顯特征的空間,為老年人提供舒適的設施和安逸的心理感受,才能留住更多的老年人,才能鼓勵老年人出門行走交流。
四、設計在老舊社區(qū)公共空間的實例
MAD對位于北京前門東區(qū)的一座清末四合院進行修復、改造,項目“胡同泡泡218號”在恢復四合院原有三進格局的同時,創(chuàng)造性地加入了三個不同形態(tài),猶如天外來物的“泡泡”。藝術輕觸社區(qū),新與舊、傳統(tǒng)與未來在老城區(qū)內創(chuàng)造了新的對話空間。2006年,MAD在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上提出關于未來北京的暢想—“北京2050”。其中的“胡同泡泡”提案,提出舊城改造不一定需要推倒重建,而是通過加入猶如超越時空的“泡泡”,像磁鐵一樣更新社區(qū)生活條件,激活鄰里關系。
“泡泡”猶如來自未知時空的小精靈,在舊城環(huán)境中閃現(xiàn)“靈氣”—“泡泡”光滑的表面折射院子里古老的建筑、樹木以及天空,賦予了老建筑新的生命,形成了面向未來的全新的空間,同時與周圍的舊城環(huán)境相得益彰,以新穎的藝術筆觸讓社區(qū)的歷史與未來開啟對話(見圖1)。

圖1 “胡同泡泡218”
合作住房零號(Cohousing Numero Zero)位于意大利都靈共和廣場,是將廢棄的住房重新用于一個年輕的合作住房社區(qū),它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幾戶人家在建筑合作文化協(xié)會結交相識,由此萌生自行發(fā)展這個項目的想法。通過一些外力的支持,合作用戶有能力實現(xiàn)了夢想,可以生活在這個意大利中心區(qū)域,住在由自己設計、根據(jù)自己的需求量身定制的空間。在這個創(chuàng)建新型關系的環(huán)境中,住戶們設計了滿足居住需求的私人空間,同時設置了為共享活動和社區(qū)生活服務的寬敞的公共空間。這座經(jīng)過修復的歷史建筑無論從實體上還是視覺上都是對整座城市開放的。建筑地處最都靈活躍的地區(qū)之一,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區(qū),擁有歐洲最大的露天市場,為有興趣嘗試體驗合作居住生活的客人提供機會(見圖2)。

圖2 合作住房零號
五、結論
隨著公共衛(wèi)生的大幅改善和醫(yī)學科技的高速發(fā)展,人口平均壽命逐漸延長,加上經(jīng)濟及社會形態(tài)的轉變,現(xiàn)代人的生育率降低,在雙重因素的影響下,社會形態(tài)及家庭結構發(fā)生了改變,傳統(tǒng)家族主義的孝悌理論與“養(yǎng)兒防老”的價值觀隨著社會的變化開始松動,加上老人自主性與獨立性的需求逐漸提升,老人與子女同住的意愿逐漸降低,追求高品質的生活水準,對居住環(huán)境有一定的需求,在這樣的趨勢下,好的社區(qū)環(huán)境是非常重要的。
社區(qū)的公共空間是老年人集中聚會的地方,公共空間是一個信息集中和發(fā)散非常好的點。全球“終身教育”“就地老化”政策的推動,促進越來越多銀發(fā)族能夠在成功地老化,在社區(qū)設立樂齡學習中心,公共空間的職能越來越多,它們所要承載的信息量也會越來越多,因此,社區(qū)中的信息交流與信息管理將是公共空間設計必須要考慮的,通過空間的設計幫助老年人解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幫助社區(qū)更好地關注老年人的生活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