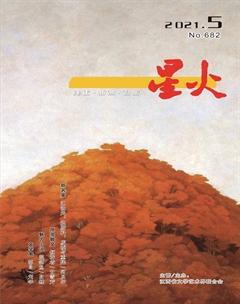都昌

都昌是我當編輯后的第一個采風目的地。那時它遠離南昌,遠至鄱陽湖東岸,遠至舟車勞頓。必須坐班車到星子縣過夜,第二天,再去正午的星子碼頭,等待九江過來的班輪。
載上啃餅干喝汽水的我與灼燙的風,班輪橫穿滿湖桅林帆影,經過神秘莫測的老爺廟水域,不時聽得鞭炮炸響,不時可見青煙騰起。長長的木排竹排從上游下來,過火車一般,很有陣勢,卻無聲息。更有成群結隊的江豬拱出水面,似乎在追逐張滿風帆遠去的一支支船隊。黑乎乎的江豬一旦出現,擁擠的船艙里便是一陣躁動。一位手指湖面驚呼“江豬”的陌生男子,激動之余,把江豬的身世告訴了我。當時,挨著我倆的幾個女孩正好奇地擺弄同伴胸前的金色飾物。
男子說,俗名叫江豬的江豚和非常罕見的白鰭豚,一個渾身黢黑,就像真正的漁夫,一個潔白俊秀,仿佛漁家的掌上明珠。傳說它倆是一對父女變的。那一家人的生活悲劇發生在女兒七歲生日那天。早晨,母親朱玉為女兒戴上親手繡的荷包,父親江珠去給女兒買漂亮的新衣裳。不料,他上岸不久,一隊來買魚的官兵見朱玉母女,頓生歹念。江珠回來后只見空船,連忙心急火燎地操起魚叉,上岸尋找妻女。找了三天三夜,喉嚨叫啞,眼淚哭干,人變得像個瘋子。此后,他賣掉漁船,給別人當船老大,吃喝嫖賭,玩世不恭,只想糊里糊涂打發一生。卻不知,女兒并沒有死,她被賣進了煙花院。
一晃十年過去,江珠已經四十多歲。在湖邊鎮上的酒館里喝醉后,他進了當地有名的白玉樓,點名牌上價錢最高的白琦陪夜。次日醒來細看白琦,問過身世,且驗證了繡花荷包,江珠頓時五雷轟頂。白琦見其失魂落魄,已是心知肚明,又羞又恨蒙臉沖出門,沖向湖邊。追著她的江珠眼看白琦縱身一躍跳進湖里,他跌倒地上,一邊呼喚女兒,一邊磕頭。風浪也是有情物。此刻湖天烏云陡暗,湖面巨浪翻騰,白琦的尸身在浪里漂來浮去。江珠萬念俱灰,也撲入湖中,白琦尸體隨之沉入水下,可江珠還是一撲一撲地尋找女兒。
大慈大悲的觀音娘娘聞知冤情,讓他父女變成水族,后人稱之為“江豬”和“白鰭”。白鰭惱恨人間不平,總是藏身水底,從來不肯露面;江豬只要一見天暗有風雨,就要拱出水面尋找女兒。所以,我們現在幾乎看不到白鰭豚,那貌若天仙、命比紙薄的女子了;所以,現在我們一旦看到江豬,便見它仍在水面上一拱一拱的,仍是那集深仇大恨與奇恥大辱于一身的苦命父親形象。
講故事的男子眼里仿佛有湖水溢出。一只不知名的鳥兒,避開逐浪翻飛的鷗群,落在他身邊的欄桿上。我不知道,是如此深沉的情感滋養了那些鮮活的故事,還是那些動人的故事培育了一顆顆情感豐富的心靈?我想,以船為家的人們,就像那只在湖面上飛倦了的鳥兒,需要蓊郁的山林,爛漫的花朵和堅實的峭巖,甚至,還需要可以遠眺的山巔。于是,在我看來,民間故事就是撒落湖中的一座座小島,人們飛臨其上,親密地依偎,自由地鳴唱,或者,任意用尖利的喙,啄擊世間的不平和人心的惡。幻想和語言是他們生活的另一處湖天。
“江豬拜風”的故事曾在湖區廣泛流傳。耕作在湖面的漁民、奔走在浪尖的船工、織補在湖灘的婦女、留守在湖島的孤寡,口授著凄慘故事,忘記了自己的悲苦。他們浩渺無垠的悲憫,彌漫在廣袤的鄱陽湖上,溫暖著眾多飄零的孤獨的心,也打濕了他們自己的眼睛。
班輪行駛了整整一下午。眼看都昌將至,但見煙波浩淼的湖面上白帆點點,波光粼粼的浪涌間江鷗翩翩。下了船,我竟逗留在擠滿夕照的都昌港,不忍離去。停泊在港汊里的擠擠挨挨的“夫妻船”上已是炊煙裊裊,卻仍有一些歸帆在湖上期期艾艾,它們大概還想捕撈跳躍在湖面上的金色光斑吧?然而,更多白帆從南山后面駛出來,遮住了夕陽晚霞。
第二次再去,鄱陽湖上的帆船已被機器船所取代,白帆消失得無影無蹤。一片也看不見!如此干凈徹底,令人咂舌,時隔最多不過兩年吧。丟失的速度怎么可以這么快呢?仿佛一夜之間。
都昌女兒的名字,時見鄱陽湖文化記憶的印跡。比如,作家楊廷貴之女叫楊帆,我同學國發之女名雨群。約摸十年前吧,打算以長篇散文記錄我對鄱陽湖的長期關注與體悟,結構有了,剛剛動筆卻擱淺了。像枯水季節的鄱陽湖,一座干旱的河成湖,水流不動,船行不得。其開篇正是從有關名字切入。
雨群,親近自然且富有詩意。從前不興去酒店餐館請客,到了都昌,便是國發家的客。在他家飯桌上,我不時品味雨群的意象。得來這一意象,需要開闊的視野、敏銳的發現,需要巧妙的聯想、豐沛的詩情。國發多次帶我去南山眺望鄱陽湖,蘇東坡說“水隔南山人不渡”,我去時卻有大堤為橋,蘇東坡說“春風吹老碧桃花”,我去時但見萬頃碧波。我覺得,惟有立足盡收眼底的南山之巔,才可以發現游走于浩浩大湖的雨之群。如我在《過去的雨》中所述—
我經常爬上山岡,眺望雨的行走。拖著風在曠野上行走,把風拖累了。在陽光里行走,把陽光淋濕了,融化了。
那么浩大的雨陣,在蒼茫無垠的天地之間,只是一團云和一束雨而已;而在它的襯托下,它前面泛黃的稻田更加明亮,它背后的陽光穿透雨陣,雨之林因此疏朗而溫馨。當陽光照耀著雨陣,當飄蕩的雨腳閃爍著陽光,這是不是某種寓言?
南山是好望角。望得見來往的船只,望得見浮沉的江豬,望得見密謀于天邊的積雨云,望得見各種形態的雨在廣闊舞臺上怎樣出場。我覺得國發為女兒取名的靈感一定來自南山,不管其承認與否。
國發調往星子后,我還見過他的雨群。頭天出差九江,我住在鐵路行車公寓,凌晨被遠遠近近的犬吠和空調主機的晃動驚醒,雖判斷應是鬧地震仍不管不顧昏昏睡去,天亮后外面的叫嚷證實九江附近發生地震。我與地震的消息先后到達星子。晚餐后去國發家看望,已是小學生的雨群雙手抱著書包,坐在靠門處,怎么也不肯去睡覺,老師說了,要隨時準備跑出大樓。那姿態那神情那語氣,真是可愛。
都昌人對地震有著深刻的集體記憶。盡管對于發生在公元421年的大地震所知不多,通常它被簡略概括為六個字:“沉陽,滂都昌。”到了鄱陽湖西岸,另有六個字,叫:“沉海昏,起吳城。”都昌縣志如此記載:“陽縣地大部分淪入湖中,陽縣撤銷,境域入彭澤縣,隸江州。”二百余年后,“安撫使李大亮謂土地之饒,井戶之阜,水陸之阻礙,遂割鄱陽縣雁子橋之南境置都昌縣”。浮出來的“鄱陽湖上都昌縣”,到了蘇東坡筆下,已是“燈火樓臺一萬家”。
關于那次地震的傳說千年流傳,民間的口頭創作是保存集體記憶的鮮活形式。都昌傳說,地震發生之前,苦于天機不可泄露,許姓道人扮作跛足行者,心急如焚地到處預警,他手執半邊瓷盤,邊走邊喊:賣邊盤呀賣邊盤。邊盤就是邊搬的意思,都昌口語管“搬”叫“盤”。人們都拿道人當瘋子,并不理會,結果蒙受滅頂之災,人或為魚鱉。其實,湖區各地都能聽到這一傳說以及多種故事版本。遙遠的大地震,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力,豐富了民間文學題材。耐人尋味的是,面對巨大災難,老百姓并不大肆渲染悲情,反而創造出諸如許道人、烏魚精等智慧形象,那些形象浸潤了古人對天地、自然的敬畏之情和力圖認識、把握它們的浪漫理想,同時蘊有啟蒙和教化的意義。關于它們的傳說故事,不僅僅是坐在顛簸的夫妻船上講給漫漫長夜聽的,也是講給子孫后代聽的。
都昌朋友領著我前往古陽,前往一千五六百年前的地震遺址,那兒現在屬都昌縣周溪鎮泗山村的地盤。因為干旱,原本沉入湖底的遺址完全袒露出來,其中有專家才識得的水下文化層。在我等眼里,很平常的堤岸,很平常的山包。
連年干旱,讓清代的千眼橋橫陳在夕照里,原來一湖之隔的都昌與星子是可以從湖底走著來往的;讓老爺廟下的沙灘交出了一船水泥,水泥已經固化,包裝袋上文字依然清晰,產于2003年,產地為蕪湖火龍崗鎮。
在老爺廟前,我與九江市文聯主席拍了合影。聞知行蹤,他特意追到老爺廟。我倆有同行澳洲經歷。當我們剛剛落地澳洲時,九江這邊又地震了,他接到家里報平安的電話,嘿嘿一笑:嘿嘿,震得我老婆掉到床底下去啦!在澳洲那幾天,他不時地嘿嘿兩聲:嘿嘿,好玩,把我老婆震到床底下去啦!
九江還有一次震級稍強于各次的地震,中國文聯曾派出團隊慰問災區人民。因為地震災害而接受慰問演出,在江西可能是絕無僅有。
我對都昌港印象深刻,上了岸,往左側看,便是造船廠。作家楊廷貴當過它的廠長。不過,我不認識當廠長的楊廷貴。如果認識,避風都昌那天,干脆讓水警巡邏艇開進船廠豈不更加安全?
那是師大作家班學員畢業數年后組織的鄱陽湖春游,從南昌出發經吳城星子到湖口,住一夜;次日折返經都昌和康山,康山尚存有舊時的打鐵鋪和剃頭店呢。豈料,遇上“打風暴”,應是伴有大風大雨的強冷空氣吧,不得不臨時決定到都昌上岸避避風頭。風雨來得急也走得快,一夜之后,返程途中風和日麗,早春的鄱陽湖風景讓我刻骨銘心,草洲漂浮在湖面上,牛群漫步在草洲上,還有一些水牛急切地往草洲鳧游,它們企望趕上那艘嫩綠的郵輪。
師大作家班由江西師大與省作協共同舉辦,后來,南昌大學也辦了作家班。兩個班基本囊括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江西文學的青年骨干,學員遍布全省各地以及各行業,巡邏艇便是證明。盡管畢業后不少學員南飛走了,但留下的作家班學員仍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是江西創作的中堅力量。
滿城魚腥的都昌,人才濟濟,居然沒人參加當時的作家班,真是一個意外。細細思量,忽然發現與身份有關。各地學員差不多都有固定的工作崗位,或為公務員,或為文化單位干部,使得他們可以如愿脫產學習兩年而工資分文不少。都昌不然,甚至整個九江市不然。都昌及九江作家仿佛是野生野長的,或者說,那片土地肥沃,到處都適合作家生長。比喻或有不當,真相的確如此。都昌及九江作家沒有工作的多,有工作而容不得“不務正業”的也多。
退伍回鄉的都昌青年陳永林,當年曾流落南昌街頭,睡在廣場紀念塔下。省作協主席陳世旭聞知心疼得不行,馬上請一家雜志社領導幫忙,陳永林得到進入雜志社當編輯的機會,之后靠著勤奮寫作,成為全國知名的小小說作家。要知道,陳世旭乃萬事不肯求人的性格。
也許執著于寫作吧,廠長楊廷貴索性調到文聯,寫小說寫評論研究地方歷史文化去了,后來曾被省里的《創作評譚》編輯部借調,聘為評論編輯,可惜因年齡問題未能正式調動。他的遺作《番人后裔》,是我了解都昌的門窗,想念了,便推開一扇,遠望南山周溪老爺廟……
都昌縣文聯曾打算召開“都昌現象”研討會。數一數,在外的都昌籍知名作家果然不少,那番景象構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現象”。八十年代初期,都昌縣僅有一位省作協會員,我強烈感受到周圍人群對他的敬重,且無不引以為豪,我就是被那種氛圍引領著去拜訪他的。如今成為“現象”了,還能維持當年一枝獨秀的氛圍嗎?
都昌的書法創作力量也很強,其中以“都昌三友”吳德勝、曹端陽、黃阿六為代表。早些年三位都曾入選書法“國展”,這在當年是很榮耀的事,對于一個縣份來說。吳德勝當縣文聯主席的時候,我又多次造訪都昌。看風景看古村也看人,看的就是吳德勝這個人。看他裝作盲藝人,看他表演鼓書,看盲人僅僅憑著眼皮和臉部肌肉怎樣表情達意。他的模仿能力極強,據說是從小學的。由此亦可想象,過去都昌城鄉多有茶館書場,多有走村串戶的民間藝人。
都昌有一位老作家長期呼吁建立“鄱陽湖派”。我覺得,有著深厚歷史蘊藏、豐富文化積淀、廣闊生活背景的鄱陽湖,無疑是江西作家得天獨厚的寶貴創作資源。一代代江西作家鐘情于斯,蘸著鄱陽湖水,寫出不少或描繪鄱陽湖風光或表現鄱陽湖生活的優秀作品。然而,坦率地說,拘囿于過去的時代氛圍和創作觀念,真正汲取了地域文化精神、捕捉到鄱陽湖獨有的氣質神韻、以鄱陽湖生活特色奪人眼目乃至攝人魂魄的力作卻是罕見。
所以,我回應道:鄱陽湖應是可以出大作品的資源寶庫,生活在鄱陽湖畔的一批作家真摯地呼喚鄱陽湖文學,其呼喚當然是有意義的。然而,確立文學流派的基礎,要有一定數量的作品和代表人物,有審美觀點一致和創作風格類似的作家群。因此,鐘情鄱陽湖的作家更應該立即出發,走向旱情愈演愈烈的鄱陽湖,走向民間記憶也將干涸的鄱陽湖,去尋訪上了岸的老人和船,去叩問水下文化層和農村的新生活。如此等等。
最近讀得汪國山的《家訓里的鄉愁》,百篇文章,九十座村莊的村落文化記憶。他還打算“孜孜矻矻,以勤補拙”,繼續寫下去,寫滿三百篇。村莊有各自的歷史各自的文化,眾多的各自構成歷史的完整真相。我一直鼓勵作家挖一口深井,我認為汪國山寫這三百篇只是挖井掘出來的土,將來,他或許能見到源頭活水。因為我覺得那土是濕潤的,甚至用力攥得出水來。
攥得出水,彌漫魚腥,那才可能是鄱陽湖文學。
劉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協全委。1982年初畢業于江西大學中文系,分配在江西省文聯《星火》編輯部工作,1995年10月至2002年4月任《星火》主編,曾任江西省文聯主席、江西省作協主席。著有長篇小說《車頭爹 車廂娘》(入選新聞出版總署第三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大地耳目》(系“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和長篇文化散文《靈魂的居所》等各類作品二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