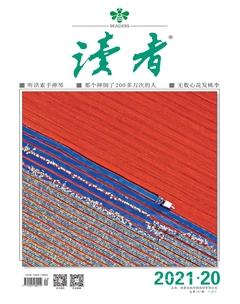輪回
范姜珊

在醫(yī)科院校讀書,免不了去臨床實習,而我去的第一個科室就是手術室。
帶我的張老師是護理團隊里為數(shù)不多的男護士,他年長我?guī)讱q,卻已經(jīng)在這里工作了好幾年。剛進科室的時候,我還不適應周圍的環(huán)境,張老師耐心地給我講解日常工作流程以及注意事項,幫我漸漸熟悉了手術室的環(huán)境。在張老師的帶領下,我開始嘗試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手術室工作繁忙,我經(jīng)常在工作結束后,雙腿酸困,疲憊不堪,張老師卻笑稱自己早已被磨煉成鐵人。我也不止一次問過他,為什么執(zhí)意留在這里工作,而他總是笑而不語。
元旦前的一個夜晚,是我和張老師的夜班,也是我在科室待的最后一天。正值北方寒冷之際,我迎著漫天飛雪快步走向醫(yī)院。到醫(yī)院后,我拍了拍身上的雪,抬頭看見張老師已經(jīng)精神抖擻地站在門口等我,不禁在心里感嘆:“他怎么一直都這么有精神!”
這天晚上,來了一位需要搶救的病人,初步診斷為急性腦出血,急需進行開顱手術。我們立刻開始做術前準備,所有參與搶救的醫(yī)生和護士都在與時間賽跑。手術開始后,電鋸“吱吱”作響,空氣中彌漫著燒焦的骨屑的味道,病人的顱骨被打開……初入醫(yī)院的我對這“血腥”的場面感到不適,轉身走了出來。
站在走廊里,我捂著胸口深呼吸,轉頭看到張老師火急火燎地朝我走來,他邊對我招手邊說道:“有個任務,你得和我一起,邊走邊說吧。”我疑惑地跟著他往外走,聽他和我說:“臨時搶救的手術,咱們要出去把病人的隨身衣物帶給家屬。”我不以為然地說:“這么點小事我自己去不就好了?”張老師看了看我,沒有再多說,我們就這樣沉默著繼續(xù)往前走。
當手術室的大門緩緩打開,映入眼簾的景象讓我愣住了。左邊是一對身穿婚紗禮服的新人,坐在等待區(qū)掩面哭泣;右邊站著一名焦急踱步的中年男子,坐在他后面的老婦不停地搓著雙手,不時地朝手術室里張望。張老師低聲和我解釋道:“在里面開顱的阿姨,是在她兒子的婚禮上突發(fā)疾病的,還是個單親媽媽,一個人把孩子拉扯大,卻發(fā)生這樣的事。右邊的家屬是里面做剖宮產(chǎn)的那位的,老婆早產(chǎn),還是第一胎……”話沒說完,就聽到手術室里傳來消息,剖宮產(chǎn)手術很順利,母子平安。右邊的中年男子聽到之后先是一愣,然后激動地轉過身對一位老婦說:“媽,太好了!母子平安!太好了!”老婦也激動極了,都說不出話來,只能用顫抖的雙手擦著眼角的淚水。
當我還站在原地發(fā)愣時,張老師已將病人的隨身衣物歸還給家屬并做了簡單的安撫,之后便忙招呼我進來。我在轉身要進去的時候,看見身后穿著燕尾服的新郎手里緊緊攥著母親的外套,他的眼淚不斷滴落在鮮艷的胸花上,已經(jīng)浸濕了衣襟,新娘俯在丈夫的肩頭啜泣,也早已哭花了妝容。
而另一邊,樸實的中年男子露出憨厚的笑容,激動的雙手無處安放,老婦人也沉浸在喜悅中,還在一遍遍擦著眼角的淚水。
在大門關閉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輪回,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離開,有人到來,有的人還會回來,有的人已經(jīng)知道再見太難。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心懷善念,盡己所能挽救每一個生命。
第二天清晨,我坐在值班室收拾東西準備出科,張老師突然走過來,微笑著說:“要走了?”我點了點頭,緊接著問道:“昨天那個阿姨搶救過來了嗎?”張老師默默地搖了搖頭,半晌,他緩緩開口:“之前你總是問我為什么一直留在這里,你看,在這里人生就是一場輪回,有的人永遠逝去,有的人重獲新生,而我們只有盡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用仁愛善待生命,尊重生命。”隨后,他遞給我一個精美的記事本,說道:“老師沒什么禮物送給你,留著做個紀念吧。”然后笑著走了出去。
我打開記事本,扉頁上是華茲華斯的詩句:“也曾燦爛輝煌,而今生死茫茫,盡管無法找回那時,草之光鮮,花之芬芳,亦不要悲傷,要從中汲取留存的力量。”下面是張老師蒼勁的大字:“生命在輪回,醫(yī)者本仁心。”
我望著他消失在走廊盡頭的身影,肅然起敬。
(曉 月摘自《中國醫(yī)學人文》2021年第7期,李曉林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