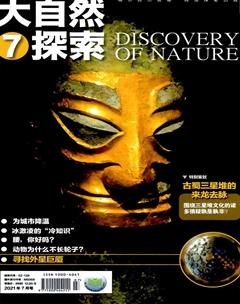三星堆文化發展脈絡
林壹
歷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使得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文化發展脈絡日益清晰,目前認同度較高的發展序列依次為:桂圓橋文化、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新一村文化以及東周時期的巴蜀文化。這些文化從新石器時代到秦漢,前后相承,延續不斷。
陶器揭示三星堆的發展脈絡
考古學家為什么要花大量精力和時間研究在三星堆遺址中不起眼的陶片?原因一方面是陶器量大樣本充足,另一方面是一代代工匠做出來的陶器成品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產生細微的變化,可為我們提供很好的定年依據,考古學家也就能夠借此串聯起一大批遺跡、遺物的年代。再者,在傳統定居農業社會中,這類最普通且廉價的手工業產品大多在本地制造和使用(貴重物品相對更有可能跨文化流通),更容易體現出不同地域間的文化習俗上的差異,因而基于陶器群劃分考古學文化也是考古領域的基本手段之一。以陶器為中心的文化傳統的延續性就暗示了人群的連續性,在更直接的古遺傳學證據出現之前這一認識很難被動搖。
陶片是最能反映一個文化發展遷徙的遺留物之一
總的來說,目前所知成都平原早期陶器的發展序列非常完備,演變脈絡清晰,其中已經沒有明顯缺環,就國內來說是同時期除了中原以外文化延續性最強的區域。三星堆在其中的定位也非常清楚, 源和流都沒有什么可爭議的地方。同時期中原還有嵩山地區—偃師—鄭州—安陽這樣的中心遷移,而三星堆遺址一到三期甚至連地方都沒變,社會發展的穩定性可見一斑。因此,三星堆文化不是突然出現,也不是突然消失,該文化的創造者更不可能是天外來客。
三星堆的四個時期
三星堆遺址的主體文化遺存,傳統上根據陶器的變化和地層關系分為四期:
遺址第一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其時代跨度、文化面貌與同處于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基本相同,被學界廣泛認知為“寶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或“三星堆一期—寶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陶盉(hé),盉是古人溫酒的器具
遺址第二、第三和第四期文化遺存為青銅時代文化,或被統一認知為“三星堆文化”,或被分別命名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第二、第三期)和“十二橋文化”(或“三星堆—金 沙文化”,三星堆第四期,也即金沙遺址的繁盛階段)。
但是三星堆遺址每一“期”相對于中原地區同時期遺存的考古學分期來說時間跨度都要大得多,所以隨著發掘工作的進行,未來可能會劃分出更多分期。
二里頭文化陶盉
早期發展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施勁松研究員的研究,在三星堆第一期(距今4500~3700年)的時候,已經出現規模很大的聚落,卻沒有營建城墻。 這一時期沒有出現青銅器制作技術,生產力水平較低,社會沒有出現多層分化,從考古材料中完全看不到王權和太陽神崇拜的跡象。此時成都平原至少有八個以上的古城(其中寶墩面積最大),這些古城的周圍還密集散布著同時期的村落。
在三星堆第二期到第三期(距今3700~3200年)的時候,之前的寶墩文化古城及其附近村落全都被廢棄,三星堆成為成都平原唯一的區域性中心。從遺址數量、密度和分布范圍來說,第二、第三期是四川盆地先秦文化發展的一個低谷期。據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孫華先生推斷,三星堆城內的貴族曾瘋狂掠奪附近地區的財產,并搶奪人口,使這些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受到了極大破壞。三星堆的城垣大約建于三星堆遺址第二期,城內在月亮灣、真武宮、倉包包等地還有7道城墻,結構比寶墩文化的城址更為復雜(由單環或重環轉變為分隔式結構),城內可能存在功能分區,如城的北區布置青關山宮殿等世俗建筑,城的南區安排神廟等宗教祭祀場所。
三星堆四羊方尊(局部)
十二橋文化太陽神鳥金飾
逐漸衰落
在三星堆第三、第四期,三星堆從中心都城跌落至普通聚落,原先的宮殿、神廟和城墻此時都已經毀棄,原先神廟中的像設和用具都被毀壞并掩埋于地下,遺址范圍內只有部分區域發現有這一時期的遺存,一些先前的特殊場所(如三星堆宗教場所和青關山宮殿基址)還出現了這一時期普通民居的堆積物。種種跡象顯示,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從三星堆遷移到了金沙。
三星堆金面具
三星堆在第四期(距今3200~2900年)的時候,只是一個普通聚落。在整個四川盆地及其周圍地區出土了大量十二橋文化的遺址,其密度甚至超過寶墩文化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治中心是金沙遺址,在其祭祀區內出土的遺物與前一階段三星堆的兩個器物坑出土遺物顯示出很強的共性,金沙青銅立人像上的太陽形冠、太陽神鳥金飾、青銅眼形器等,依然突出表達了太陽崇拜,與三星堆金杖圖案完全相同的金冠飾等仍然代表著王權。葬俗上的延續性也很明顯,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絕大多數墓葬沒有隨葬品,包括青銅器在內的貴重物品同樣不作為隨葬器使用。墓葬的這一共性,表明當時雖然出現了社會分層,甚至可能形成了原始的國家形態,但神權居主導地位,社會財富可能為整個統治集團而非個人占有,全社會將貴重物品集中用于宗教活動而不是個人的喪葬活動。沒有厚葬習俗,不以貴重物品來體現個人的身份和地位,從墓葬中也看不出社會的分化,種種習俗和同時期的商周文化截然不同。
三星堆陶人頭像
三星堆的末期
在新一村文化時期(距今2900~2500年),三星堆聚落仍有人類活動,只是面積可能縮小。
東周時期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是從三星堆到金沙都大量存在的青銅器、金器、玉石器和象牙等祭祀性器物全部消失。雖然暫未發現都邑性聚落,但墓葬材料表明,從春秋晚期到戰國,成都平原的墓葬的規模和隨葬品的多寡出現嚴重分化。考古學家可以根據這個特點,鑒別墓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同時,還出現了可能分屬不同族群或政治勢力的大型墓地。墓葬中普遍出現大量兵器,這表明當時的社會局勢動蕩不安。此前的太陽崇拜等信仰已不復存在,青銅器的功能由祭祀用器或宗教用品變為實用器和喪葬用品,新出現的是大量的青銅制容器、兵器、工具和印章等,銅器上還出現了“巴蜀符號”。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統治權力的表現形式都發生了顯著變化,這個新的價值體系不是完全從成都平原原來的文化和社會中自然產生的,而是與東周時期當地文化的衰落和楚文化、中原文化的西進相關。
位于三星堆遺址東北角的三星堆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