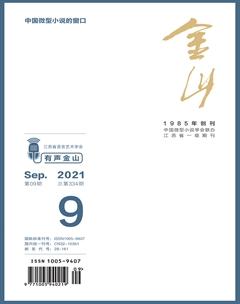對峙與倒錯——《行過洛津》的對位式書寫
邱彥琦
施叔青的“臺灣三部曲”以《行過洛津》拉開帷幕,其中涉及性別隱喻、禮俗戲曲等議題,研究界已多有涉及。本文試圖另辟蹊徑,由“對峙與倒錯”為切入點,關注洛津城中各色人物的生存狀況,揭示不同力量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通過結合薩義德“對位式閱讀”理論,試圖探討《行過洛津》“對位式書寫”的特征。這構成了施叔青建構臺灣歷史的獨特之處,也使小說呈現出更為復雜的歷史視野。
《行過洛津》以伶人三次來臺為線索,而由主要情節輻射出去的,便是有關帝國與邊陲、外來者與本地人(包括朝廷官員與洛津百姓、移民與原住民)的不同卻又部分交叉的雙重視野。以下主要從“天朝棄民”的代表(富商)、權力核心的官僚階層(同知)和原住民三方面闡釋外來與在地的雙重視野。
“天朝棄民”:對清廷的錯綜情結
洛津作為海港,依托貿易活動興起,形成了與傳統“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秩序不同的重商文化。洛津泉郊的首富石煙城,是《行過洛津》中富商的代表人物。作為社會暴富的上層,富商取代了官府,石煙城等人幾乎執掌了洛津的生死命穴,成為地方舉足輕重的角色。施叔青以一句俗語:“郊商興,洛津興;郊商敗,洛津敗”點明了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在滿清帝國輕視邊陲臺灣的背景下,施叔青通過富商石煙城獻金建造城門的事件,凸顯了“天朝棄民”的自主意識。
滿清政府將臺灣納入帝國版圖,但仍將其視為邊陲蠻荒之地。一方面實施海禁政策嚴加管束,另一方面無心治理經營。洛津雖曾發展為臺灣第二大海港貿易城市,但地方仍呈現自治狀態。其中,清廷以臺灣多地震為由,不許臺地筑造城墻,實則唯恐本地居民擁城屯兵,但這也讓當地治安缺乏保障。在經歷了幾次起義反抗后,清廷不得已準許府城以磚建城。洛津首富石煙城有意獻金建造被焚毀的彰化城門,于是宴請理番海防同知朱仕光商議,這一情節卻恰好暴露了清廷的統治問題和官商角力:
石煙城一方面親自迎接朱仕光前來,另一方面,其真實目的卻是讓朱仕光見識到石家的萬合行有如城中之城的氣勢。主人——富商石煙城安適地坐在三間開六門扉的寬敞氣派的正廳中,空氣中似乎還可聞到新漆的刺鼻味道。客人——同知朱仕光悄悄用余光打量萬合行中的擺設,將視線投在正中墻壁上一幅巨大的威勢十足的螭虎彩繪上,暗暗感到坐在一旁的富商在俯首卑恭之中帶著倨傲與輕蔑。
石煙城頭戴瓜皮帽,身穿簇新的淺灰對襟馬褂,浮著泥金團花,長度只到肚臍。此種樣式正是當時嘉慶一朝新近流行的,不僅馬褂的衣料用了最名貴的金陵織造的云錦,顏色也正是京官時興的淺灰與泥金。相比之下,同知朱仕光身上的這件團花馬褂,已是乾隆年間的過時樣式,顏色也顯得黯淡發黑。某種程度上,顯示出石煙城比朱仕光更接近帝國中心。
富商既模仿又試圖凌駕權力中心的官府,建造城中之城,又對帝國派遣的官員表面尊重實則輕蔑。他們與帝國關系的曖昧還體現在石煙城等人在政治上的見風使舵。從其對臺灣起義軍的態度上可見一斑。
林爽文痛恨清廷官吏橫征暴斂,揭竿造反。這是當時臺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中最大的兩次事變之一。一開始起義軍勢如破竹,石煙城等人便依附林爽文這方。而后乾隆派軍渡海鎮壓起義,富商們又立馬率領族人做清軍的向導,功成之后欣然接受清廷頒授的“盛世良民”之旗。有關石家的發跡史的鄉土想象因此呈現超出經濟方面的復雜面貌。
而關于石家的敗落,當地流傳的說法也充滿對豪門招嫉的想象——傳言是敗在朝廷的陰謀,由嘉慶皇帝一手主導:
皇帝也接到福建巡撫的奏折,府城、洛津、萬華三城的官員不斷向他投訴,郊商勢力凌駕于官府之上,致使官威不振,阻礙政令之推行。朝中有一大臣獻計……前往洛津勘察萬合行之地理,暗中設計破壞。
實際上,以清廷對臺灣的忽視,哪怕是福建巡撫都極少踏足臺灣,更不用提皇帝的關注。這種想象,透露著洛津豪族自詡形成威震帝國的地方勢力,既盼望帝國的注目,又擔心帝國將之消滅,帶著“天朝棄民”對帝國的錯綜情結。
官僚階層:權力核心與身處邊緣
從帝國與邊陲的角度看,朝廷派遣的官員是與在地力量相抗衡的外在勢力。從臺灣內部階層的角度看,海防同知父母官朱仕光,自然是居于洛津社會上方的官僚階層。
清廷和派遣的官員都將孤懸海外的熱帶島嶼視為窮山惡水的蠻荒之地,認為此地除了終年不斷的瘴癘蠻雨和野蠻血腥的出草生番外并無他物。在清廷和朱仕光等官員的想象中,臺灣是與原始、野蠻和疾病相聯結的。帶著帝國視域看待臺灣,臺灣也成了某種奇觀,令官員們驚異、不安又厭惡,深感離開了文明世界。朱仕光自詡揚州名士,講究品茗和賞花,嫌棄臺灣當地的食物粗俗不堪、難以下咽,不及家鄉細膩烹調的萬分之一:
他舉起象牙筷,滿桌菜肴卻不知從何下手。青瓷盤碟的蝦猴……挾了一只放入嘴里,嚼都沒嚼,連忙整只吐出,舌頭還是咸到發麻。青蒜炒鯊魚片,雖然時鮮,揚州人的同知嫌太腥,難以下箸,他吃不來海魚,除了腥味重,魚肉也粗。
坐在石煙城金銀堆砌的廳堂中,朱仕光不僅難以下箸,還蔑視石家的“暴發戶”氣質,認為石家雖也靠販賣海鹽發跡,但與揚州兩淮鹽商在品位格局上實在是無從比較。朱仕光自幼受中原的士大夫雅文化熏陶,認為臺灣的庶民文化太過粗俗,嘗試以禮教為秩序對其進行規訓。以往的歷史書寫中多提清朝官員對臺灣荒漠般的文化生態做出的巨大貢獻,卻很少提及官方對移民世俗文化的強行閹割。施叔青通過朱仕光對《荔鏡記》的改寫,展現了官方的傲慢與野蠻。
改寫潔本《荔鏡記》的過程中,首先被改動的便是戲文所用的閩南方言。由于閩南語地處邊緣,遠離中華文化的中心區,朱仕光認為其是“南蠻鴂舌之音”,要求書吏將戲本中的“土語”一律翻譯成官話,還將對白中的生動口語刪除,并加入堆砌的辭藻作為修飾,將戲文原有的活力刪改殆盡。這種語言刪改背后是中原主流文化對邊緣移民社會的傲慢,亦是士大夫文化對庶民文化的干涉與收編。
但朱仕光觀看《荔鏡記》之后,竟為之傾倒,甚至強暴了演戲的伶人。這些前后矛盾恰好顯示了邊緣地方民情對中央政府官員的潛在影響——朱仕光把無法填滿的欲望歸罪于洛津的天氣水土,“被腥咸潮濕的海風熏得懶散”,“喝多了帶鹽味的井水”所致。此處朱仕光站在帝國的視域中看邊陲臺灣,怪罪這一化外之地誘發他的欲望。一如西方殖民者認為熱帶殖民地的風土天氣誘發罪惡,卻不知那是殖民者自身的欲望被殖民地的文化所擊敗的結果。
另有一個微妙的細節更是直接體現了朱仕光的潰敗——當地頗有名望的郭舉人拒絕了朱仕光的飲宴邀約,卻轉頭去參加當地民俗活動的出巡儀式。在衙府外歡騰的喧鬧聲中,唯有墻內的同知朱仕光產生了被遺棄在歡樂之外的感覺和被冷落的失落感。海防同知代表滿清朝廷,是當地的權力核心,三進的磚造同知府,也是洛津最高的權力中心,本不應讓人感到“身處邊緣”。但在這一晚,朱仕光感到他的百姓置他于不顧,這種寂寞與失落帶來一種不安全感,一種“中央”反被“邊緣”排除在外的虛懸擺蕩之感。
原住民:苦難的記憶
相對于朱仕光等外來統治者觀點,施輝、潘吉等則展現在地觀點。
雖然《行過洛津》以男旦許情三次來到洛津串聯情節,但施叔青的筆觸也涉及到更早的洛津,即漢人移民還沒來到之前的、以原住民平埔族為主的歷史。也正是在這一敘述中,《行過洛津》超越了一般的漢人移民開發史,展現了更加宏大而復雜的洛津城面貌。
落魄文人施輝是漢人移民的后代,其祖先開墾洛津有功,使該地成為泉州人地盤,還捐地建造天后宮,被當地稱為“施大善人”。施輝引以為傲,常常對人講述先祖的光輝事跡。他的同居人是已漢化的平埔族女人潘吉。她勤勞務農、樸實能干,在日常相處中和施輝因族群文化差異也鬧出了不少哭笑不得的故事。
但施輝真正理解平埔族的遭遇和傷痛,還要等到他深入濁水溪尋找高人,在森林中與原住民山胞相遇之后。施輝在山上碰到獨行、黥面的山地人,他們“面目猙獰、遍體刺青,背上刺了盤旋飛翔的鳥,從肩膀到臍部盡是網狀的纓絡,兩臂各刺青一串骷髏頭,從手腕到手肘戴了幾十個鐵鐲,耳朵也戴了一對大鐵圈”。施輝先是被嚇了一跳,但進而了解到他們的歷史——平埔族人先是被“紅毛番”(荷蘭人)騙取土地,又被漢人用武力侵墾。原住民失去活路,被驅逐趕往深山林內,不得已不斷遷移,越過中央山脈到后山開墾找生路,施輝開始心生同情。
隨著對平埔族歷史的進一步了解,施輝的同情轉變為了對祖先的憤怒。他發現漢人先是向平埔族人租用土地,繳納“番大租”,后脅迫原住民出讓地權,徹底把土地據為己有。當平埔族夜祭阿立祖時,在憂傷的歌聲中主持祭亡靈儀式的女巫會沖向田埂,倒地翻滾地抖唱,揪心揪肺地唱出一段段族人的歷史故事。施輝原本以為平埔族在夜祭時的嚎海,是哭祭當年漂洋來臺時死于海難的先民,現在他終于懂得這哀慟欲絕的歌聲,也是在悼念他們失去的土地和家園。
并且,施輝發現,與原住民簽訂賣契的,正是他曾引以自豪的祖先、被稱為“大善人”的施世榜。他也因此產生了深深的困惑和震撼,反省今后是否還以施世榜的直系子孫為榮?這呈現出一種由漢人的自我反省思考:原以祖先為榮的漢人移民施輝,經過上山溯源的旅程,發現了祖先榮耀的背后充滿了殘酷與殺戮,對原先的自我認同產生了質疑。此處對于原住民歷史以及漢人移民剝削壓迫原住民的描寫,改寫了帝國對原住民的單面看法。作者此時附身于施輝之上,表達了她對山地人苦難族群記憶的同情,也從另一個立場敘述了歷史。
結語:對位式閱讀與書寫
《行過洛津》在臺灣獲得了很高的評價,施叔青的書寫具有一種建構臺灣歷史的別樣特色,甚至和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提出的后殖民對位式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有異曲同工之妙。薩義德的理論認為,讀者經常只關注帝國歷史敘述或文學,或恰恰相反,只關注反抗帝國的敘述。但兩者實則相輔相成、緊密聯結。他以西方古典音樂對位法中不同主題輪番出現,彼此交響,最后多音齊鳴做喻,指出后帝國時代的知識分子應同時關注帝國與昔日殖民地社會之間重疊的社群,以對位的方式檢視不同經驗如何構成一組交錯重迭的歷史,將之脈絡化、系統化地進行理解。
而施叔青的《行過洛津》恰好將多種觀點并置、對照,在對峙與倒錯中構成了對位式歷史書寫。一方面小說顯示了帝國影響邊陲:大陸移民貿易開發了商港,清朝官員帶著帝國視域來到臺灣,而地方豪族也盼望帝國的注目……另一方面,從臺灣中心的角度,小說以移民社會作為臺灣的共同想象,采取鄉土想象歷史化的方式書寫臺灣:官方忽視臺灣且無力經營,反而成就了郊商的特殊地位,在地漢人因與原住民女子通婚而發現漢人墾殖者對原住民的欺壓……
此一書寫方式與施叔青從當代重建歷史的取角有關。不同于以清政府收編臺灣的帝國觀點歷史敘述,也有異于只強調本土反抗的在地觀點歷史敘述,她讓兩者交錯出現,甚至出現許多重疊,而形成對位、交響關系。它著眼于移民鄉土意識的生成與不同身份的人群之間的關系,借此提出了更復雜的歷史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