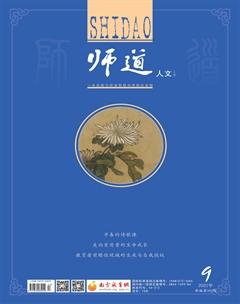以什么樣的態度面向未來的語文教學
凌明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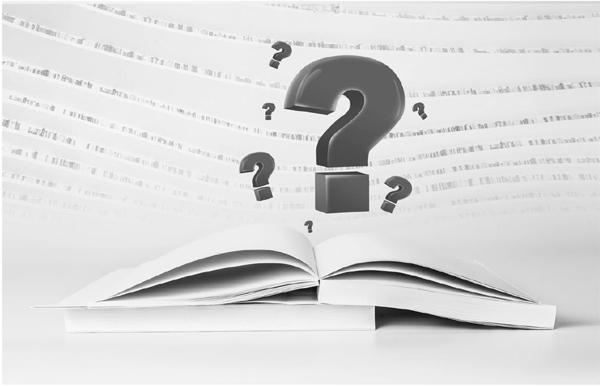
先從語文圈的一場爭論說起。
《福建基礎教育研究》2021年第8期刊發了復旦大學附屬中學黃玉峰老師(以下簡稱“黃”)的一篇文章《一場關于考不考“閱讀分析”的爭論——答詹丹教授的批評》。黃在文章中說,他在上海圖書館作了一個講座,提出考試不應該“考閱讀分析”的建議,并在微信朋友圈發表了這觀點。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詹丹(以下簡稱“詹”)在朋友圈里說:“雖然我很尊敬一些名師獻身中學語文教育的熱情,但他們時有一些主張偏激、邏輯混亂的觀點,實在不敢茍同。比如,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的議論為支撐而要求廢除‘閱讀分析的老師,先就要考考他的閱讀能力:‘不求甚解和‘不求解有無區別?”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趙志偉(以下簡稱“趙”)看到了,寫了一篇文章在朋友圈反駁詹:“去問問中學生,閱讀分析已導致了多少人文理不通,捫心自問,你們語文是這么學的嗎?這種閱讀分析,恕我偏激,是一種從小學到中學的課堂公害。誰不知道不求甚解與不求解不是一回事?”
我沒有查到趙的文章,詹接著寫了《“閱讀分析”是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評黃玉峰師和趙志偉兄的一種觀點》,文章主要意思有三:一是說自己要“考考他的閱讀能力”是“沒有趙兄所謂的‘嘲諷本意”——只是“想輕松地幽他一默”;一是認為“‘閱讀分析,或者用一個更具廣泛指涉性的詞語‘文本解讀”是“教學內容的重心”,“這樣的訓練重在問題意識、重在思維方式”,“時下有各種機械的乃至可笑的閱讀分析或提供參考答案自身,沒有經受過嚴謹的閱讀分析的思維訓練,而那些把差的命題等同于閱讀分析題乃至閱讀分析活動本身,也說明了他們自身正品嘗著沒有經過這種訓練而帶來的惡果”;三則是對“不求甚解”的語義辨析。
詹寫出文章后,黃發表了上面提到的文章,主要的意思有二:一、是說詹誤解他的意思,他認為閱讀分析還是需要的,“在課堂上必須講解,講得越生動越好”,他只是說語文教學“被‘閱讀分析標準化試題搞壞了”,他說:“我不是說不要分析,只是說不‘考分析!”二、黃老師也對“不求甚解”作了語義辨析。
從詹、黃的文章,及他們所引趙的言論來看,大體可以得出一個判斷:這樣的爭論,算不得真正的學術爭論。
首先,這是一場“雞同鴨講”式的爭論。詹不斷地說閱讀分析很重要,趙說“這種閱讀分析”“是一種從小學到中學的課堂公害”(按黃玉峰老師說“‘這種指的是那種蹩腳宣傳文章、說假話的文章、一看就明白的文章以及那種碎尸萬段、故作高深、故弄玄虛的分析。”),黃則說“問題是不能以您的分析去‘考他們”,如上所引,他主張“不‘考分析”。三人各自說的是各自的話題,詹說的是“要不要閱讀分析”,趙說的是“這種閱讀分析是中小學課堂公害”,黃說的是“不要考閱讀分析”,各說各話,連個共同的靶子都沒有,這算什么爭論。論辯的首要條件是論題或所立事,首先是要有一個確定下來的共同的題目,要圍繞著這個題目表述各自的觀點。連共同的題目都沒有,確實如詹在文章里說的“比如老友趙兄(指趙志偉)不止一次舉例說,我們可以出題來問這個人長得美不美,但現在出題者老是在問,這張臉長得對不對?”這樣的爭論,也確實像詹在文章里說的“這不是莫名其妙嗎?”詹倒是在文章里談到黃所說的閱讀分析的考試問題,指出有些閱讀分析考試機械化、標準化,兩人的爭論總算有了一點交集,但輕掠而過,并未深入探究原因,也未能具體論述如何科學地進行閱讀分析考試。兩人真正可以進行學術探討的機會一閃而過。他們忙啥去呢?
其次,這是一場各逞意氣的爭論。學術爭論的另一個重要原則是客觀、科學、冷靜地表述自己的觀點,將學術問題的探討引向深處。但是很可惜的是幾位老師要么擔心壞了圈子友情,要么進行道德攻訐,完全不是學術辯論該有的態度。按黃的說法,“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趙志偉看到了,憤憤不平,在朋友圈反駁詹丹”,兩人深厚情誼可見一斑。趙大概是覺得詹想考考黃的閱讀能力是一種侮辱,作為朋友得拔“筆”相助。一場轟轟烈烈的學術爭論竟然因為學術面子而起,也真是趣味。詹顯然也覺得自己的“想輕松地幽他一默”不妥,于是文章一開始就稱黃是“我所尊敬的滬上名師黃玉峰先生”,稱趙為“老友趙兄”,文中也一再以“趙兄”相稱,他之所以語氣如此謙遜,大概正是他在文中所擔心的:“這樣的閱讀分析看似只是一個小問題,但也許會影響到對人的基本評價和人物關系的和諧相處,‘茲事體大,又不能掉以輕心了。”最后他引用了孫歌老師的一段話:“在鶴見俊輔那一代經歷過戰爭的知識分子里,這種不計較他人對自己評價的大度,保證了他們在論戰時有能力通過激烈交鋒保持問題的思想含量,而不會陷入個人恩怨。”他說:“我相信,這些意見,是能夠在不傷害朋友情誼的前提下,推進對閱讀分析的意義認識的。”結果這些話大概是惹惱了黃,他在指出詹的論辯不對題之后,就開始用了主要篇幅辨析“不求甚解”的含義,他一再問“錯在哪里?”一個中學老師對這么常見的詞語的理解如果有錯誤,黃大概認為是極失面子的事情。他感到憤憤不平的是:“君子和而不同。詹丹兄是厚道之人,怎么就不能容許不同意見,而斥之為‘不懂呢?”最后他說:“玉峰不顧他人的嘲笑譏諷,乃至打壓,為之呼喊,希望我們的學生不要學得那么苦而沒有收獲。”他又說:“您不但是有話語權的人,而且是在有話語權的人里面是有學問的人,我希望您對上面吶喊,救救語文,把‘閱讀分析從考卷里清除出去。”話說得很重,以斗士的形象自許,那么不同意見者就大有反動之意了,而說到話語權,則牽涉到權力層面,跟學術位置就有關了,甚至已經不是意氣了。那么“不求甚解”的原義究竟是什么似乎也不重要了,三人都用了大篇幅來闡述,看起來是學術爭論,是哪一種理解正確,其目的只是在語文圈中是你對還是我對。
語文教育是在爭論中發展起來的,老師在具體的教學中時時都會有不同的見解,不同的教法,共同探討,取長補短,各個語文大家對語文問題也各有不同的思想,相互辯詰,彼此相長,語文學科建設才取得今天的成就。未來的語文教學中還會有很多爭論,如果都是這般文不對題,這般意氣為先,大概是根本無法有真正的語文教育的進步的。意氣的另一個代名詞就是狹隘,以詹、趙、黃的爭論來說,意氣一來,自然無法謙遜,說多少敬詞都會變成諷刺,自然也無法以開放的心態去傾聽對方的觀點,更無法客觀辨析對方的觀點有多少學理依據,也無法客觀陳述自己的學術論證。我一個朋友去美國讀了五年比較歷史,回來我問他讀了五年書有什么收獲,他愣了一下,然后說:“說話要有證據。”我大受震動。“說話要有證據”,意思是要表述自己的觀點,應該有學術論據的支撐,要客觀,不能主觀臆斷,不能意氣為先。
說到如何為未來而教的問題,作為老師,我覺得首先是要有一種謙遜、開放的教學態度。每一個老師都是一個在不斷成長的個體,從大學畢業,并不是說就已經完全擁有教學中所應具備的全部知識,也掌握了成熟的教學技能,有了先進正確的教學思想。從大學畢業,只是說有了入職當教師的心理準備,有一定的教學技能和專業知識儲備,初步接觸了一些基本的教學思想,真正的成長是在具體的教育教學實踐中通過不懈的學習獲得的。真正的學習是在爭論中完成的,與過去的自己爭論獲得新知,與錯誤的經驗爭論獲得真知,在書籍中與大家爭論獲得卓見,與同行爭論獲得獨見。如果狹隘己見,只見獨木不見森林,只能囿于固陋,自然無法進步,以謙遜、開放的態度去爭論,總能汲取到讓自己進步的營養。比如要不要有閱讀分析,三位老師如果能不固執己見,謙遜地思考他人意見,以一種開放的態度去分析對方的觀點,很容易就能理解到這個問題本身就不是能夠一概而論的。文本不同,有的文本文字優美情韻悠長,可能需要不斷吟詠誦讀,有的文本涵義蘊藉晦澀艱深,則需要剖析探究;同一個文本,教學的目的不同,采取的教法也會不同,出于吟詠體會或了解大意的目的,則不需要剖析探究,出于辨析理解歸納推理的目的,則需要剖析探究。這個道理其實很淺顯,可惜一葉障目,難免不見泰山了。認識到自己是狹隘的,是一個需要成長的個體,永遠是需要學習的不成熟的個體,始終秉持著學術的熱情和敬畏的態度,就是一種為未來而教的態度。教師以謙遜、開放的態度面對未來,意味著個體將始終走向不斷豐熟的道路上,不斷在成就著未來的自己。
教師以謙遜、開放的態度面對未來,也意味著在學習中能與學生以一種爭論的狀態存在。黃就能以民主的謙遜和開放態度對待學生,他尊重學生主體性體驗。這一點是很值得贊許的。每個學生有各自不同的生活體驗、思維特質、稟賦、個性,尊重學生的多元性,正是面向未來的教育的根本要求。黃在他的文章里說了這樣一段話:“你的紅樓夢分析得很有味,我受益不淺,但我的紅樓夢和你不完全相同。你考我,我不及格,把我的作標準答案,也許你也不及格。上課可以也應該分析,好的老師的分析講解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啟發他們的思考,但如果一定要作為‘標準,那就索然無味。”這是很動人的一段話,讓人看到黃具有謙遜和開放的態度,從他這樣說話,我們就能知道他應該是深受學生歡迎的一位老師。這樣的老師現在受歡迎,未來也同樣會受歡迎。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他這樣說是為了反對以“標準化試題”(準確地說是“標準化答案”)考閱讀分析,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閱讀有兩種,一種是限制性閱讀,也就是從文本入手,最大可能地貼近作者表達的本意,一種是開放性閱讀,讓讀者的經驗和感悟介入文本,從而獲得自己的閱讀感受。黃所說的閱讀是開放性的閱讀,要尊重學生的開放性閱讀,因此他說的話并沒有錯。他沒有理解的是閱讀文的考題的設置其實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限制性閱讀,也就是說考查學生從文本本身能否理解作者的表達,另一種才是黃所說的開放性閱讀,即通過閱讀文引發自己的主觀感悟。安伯托·艾柯在《開放的作品》里說:“觀賞者有可能——選擇自己的方向和聯系,選擇自己的優先角度,以個人的表現特性為背景去選擇和欣賞其他可能的表現特性,這些表現特性是排他性的,但卻是同時出現的,是不斷相互排斥、相互影響的。”黃特別注重這種開放性閱讀的考查,但他忽略了中學語文教學中限制性閱讀也不能忽視,從語文的工具性角度說,甚至是更重要的。會閱讀是中學生基本的能力要求,閱讀為寫作奠基,懂得閱讀分析才能寫得好,這是基本常識,反對機械化的閱讀分析考試是對的,但反對閱讀分析考試則肯定是錯的。詹之所以會寫文章與黃爭論,顯然是看到這樣的觀點有偏頗之處。黃之所以會犯這樣武斷的錯誤,正因為他不能客觀地辯證地看待問題。
面向未來的教學更需要一種客觀性,在我看來就是一種學理建設。我的一個同行轉發黃的文章時引用了他的導師的一段評論,他的導師說到閱讀分析的教學時說:“語文教學到現在沒有形成科學系統。”其實語文是有其科學系統的,也就是有其科學性客觀性。舉個簡單的例子,可能不同的讀者會喜歡不同風格的語言,但同一種風格的語言,好的和壞,其實這里面的分野是很清楚的。所謂客觀,就是對紛繁蕪雜的語文現象進行觀察,對之進行分析、歸納、概括,探究語文現象的規律,構建語文學科的知識系統和能力架構,最終完成語文知識系統的建構,形成良好的語文素養。教師要在教學實踐和自身的語文學習中去探究語文學科的客觀性,并將自己的理解在教學實踐中落實,讓學生也循序漸進地建構起自己的語文知識系統,培養語文能力,養成良好的語文素養。比如言語技能這一項來說,章熊、張彬福、王本華曾寫過一本書叫《中學生言語技能訓練》,“前言”里有這樣的表述:“作為語文能力因素之一的言語技能,有層次高低之分,然而就其整體而言,屬于心智技能。言語活動具有高度的創造性和創新性,在言語運作的過程中,人們的思維是相當活躍的。……思維指揮著語言,語言又刺激著思維,而我們的思想,也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清晰化、完善化。”這是對言語活動規律的客觀認識。作者還說:“言語技能有層次高低之分,而且這種發展有著一定的程序性。……在這本書里,特別是第十節,我們試圖勾勒出言語技能發展的大致輪廓。”書中像“長短句轉換”“語句的靈活調整”“句子的鏈接與銜接”等專題都極具啟發性,在“言語運作”這個語文課題上作出了極具價值的探索。
時代的發展如同飛輪,語言也在時代的繁弦急管中急劇發生著變化,語文學科教學同樣要因應變化,語文教師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成不變是教不好書的,以謙遜的態度對待語文教學和新時代的學生,以開放的心態迎接新變化,以客觀的態度研究語文現象,這正是面向未來的語文教學的基本要求。
(作者單位:福建廈門市湖里實驗中學)
責任編輯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