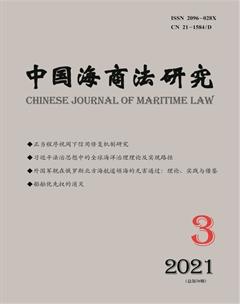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視域下無居民海島治理法治路徑探析
摘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推進無居民海島治理的核心要義。無居民海島開發利用受生態規律的制約,具有環境與資源一體化的生態特征,該特征決定了無居民海島治理適合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作為價值基礎,而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轉化為治理體系和治理效能則需要借助法治化路徑加以實現。在治理體系層面,以綜合立法統攝無居民海島治理,核心要義是尊重生態系統自身價值和無居民海島生態系統完整性,統籌無居民海島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規則體系。在治理能力層面,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需要修正無居民海島監督管理模式,推動無居民海島治理由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過渡,適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推進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以實現無居民海島治理制度化、規范化、高效化。
關鍵詞:無居民海島;綜合立法;生態系統完整性;社會治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
中圖分類號:D922.6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28X(2021)03-0076-14
Legal paths of uninhabited islands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integrity
MA Jin-x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issue of uninhabited islands ecologic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integrity.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uninhabited islands are restricted by ecological laws and have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which determine that the uninhabited islands governance is suitable to take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integrity as the value basis, and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integrity needs to be solidified through legislation when it is reified 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In terms of the system for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legisl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cosystem integrity, the core essence is to respect the self-value of the ecosystem and the integrity of the uninhabited islands ecosystem, and to coordinate the isl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rules system. In terms of the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it is suggested to modify the mode of uninhabited islands management, and to promote the uninhabited islands governance from social management to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should be used in uninhabited islands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lead to systematized,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way.
Key words:uninhabited islands; integrated legislation; ecosystem integrity; social governance;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無居民海島具有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一體化屬性,海島與周邊海域的生態構成具有完整性。
《海島保護法》規定對無居民海島實現綜合管理,2019年《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完善陸海統籌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
。優化無居民海島治理,已然是海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居民海島治理是在綜合管理基礎上,對無居海島的開發利用及生態保護施行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因此,無居民海島治理的行為對象既包括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也包括生態環境保護。依法治理的核心是推進治理法治化,即經由構建法治秩序將相關政策主張及具體規則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通過治理理念、規則機制和治理方式相互配合及補充,提升無居民海島治理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其中,治理理念是規則機制、治理方式的本源和基礎,在推進無居民海島治理法治化進程中,具有牽引和塑造無居民海島規則機制、治理方式的作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逐步成為海洋綜合管理領域的主流理念,[1]87《21世紀議程》明確指出“包括海洋及其臨近的沿海地區在內的海洋環境構成一個環境整體,需要以一種綜合的方式來進行保護和管理”。在當代,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已經成為海洋領域立法活動及政策制定的價值基礎。無居民海島資源與環境具有一體化特征,利用與保護相伴而生,海島資源開發利用不應損害生態系統完整性和海島生態環境承載限度;由于無居民海島類型千差萬別,不同類型、區位無居民海島的環境屬性也各不相同,海島生態環境保護需要明確一般指導意義和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治理理念。生態因素是無居民海島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的交集和連接點,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推動無居民海島治理法治化進程,是在遵循法治化評價尺度和標準的基礎上,實施多層次多領域的治理活動,構建互補均衡的現代治理結構,以規則制度建設提升治理效能,推進無居民海島治理現代化。
一、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內涵及立法吸納
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的產生歸功于環境倫理理論的革新。環境倫理理論將提高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作為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則,并以此為價值基礎確定公共環境政策的目標,倡導以環境倫理觀指導人類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
(一)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的基本含義
生態系統完整性,是指生態群落每個參與主體以相互依存關系表示的整體性。生態群落中任何一個關鍵主體的損壞將破壞整個系統的能量流動,破壞復雜的食物鏈網絡,從而侵犯了完整性。[2]生態系統完整性強調生態進程(ecological processes)的重要性,其重點是保護生物多樣性,包括生態系統的功能、結構、特性和修復能力。[3]一般認為,當代對生態系統完整性的關注緣起于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所倡導的現代環境倫理。20世紀中葉,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A Sand County Almanac)中闡述“完整性”時,認為“……一個事物,當它表現出保持生態群落的完整、穩定和美的時候,這個事物就是對的,當它表現為其他的時候就是錯誤的”。[4]1981年,詹姆斯·卡爾(James R. Karr)、丹尼爾·杜樂(Daniel R. Dudle)將生態系統完整性定義為“是支持和保持一個平衡的、綜合的、適宜的生物系統的能力”。此后,1993年史蒂芬·伍德雷(Stephen Woodley)提出:“生態完整性是生態系統對其所處的地理區位進行優化(能量輸入、水分和養分留存、定殖歷史等),促使生態系統發展的狀態”,[5]這是完整性保護思潮演變史上首次出現“生態系統”視角。[6]1821其后,在環境及資源政策及立法領域,生態系統完整被作為一種考慮到包括人類在內的整個生態系統的治理理念加以討論,目標是保障生態系統可持續地為人類提供物質及生態服務功能,維護生態系統的健康、恢復性及多樣性。
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內涵具有演進性。由于生態系統本身在物理、化學、生物及其各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十分復雜,不同時代、不同學科領域和不同學術觀點在界定和解釋生態系統完整時,有著不同的研究視角和認識,對生態系統完整有不同的定義,概念內涵也呈現多樣化特征。代表性的定義包括:將生態系統完整定義為“支持和維持平衡的、完整的、適應的生物群落的能力,這個群落具有自然生境條件下可比的物種結構、多樣性和功能組織的能力”;[7]或將生態系統完整定義為“生態系統完整性是
指在正常干擾范圍內維持森林結構、物種組成以及生態過程和功能的進程”。[8]而上述定義的共同特征是承認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不同方面,反映了人類對生物多樣性的價值、重要性和作用的主觀認識。雖然不同理論及各國實踐對于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理解各有側重,但總體普遍認可“要素—結構—功能”的分析框架,[6]1822即在構成要素層面,不同區域生境所應包含的全部本土野生動植物種群及其生存環境、景觀構成具有完整性;在組成結構層面,生態系統具有區域自然生境所需包含的所有本土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學進程,其結構沒有受到人類活動的不利影響;在功能運行層面,本地物種處在能夠持續繁衍的種群水平,在外部條件不斷變化時抵抗干擾并維持最優化運作,以及繼續進化和發展的能力。[9]概言之,生態系統完整性并非絕對排斥人類活動介入區域生態進程,其核心是在維持生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減小或克制人對環境的破壞作用,實現生態系統在特定地理區域的最優化狀態,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二)環境資源立法對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的吸納
生態系統完整性概念創設之初系生態學概念,其后被生態系統管理學作為分析生態系統穩定性和自組織能力的評價工具,[10]并由生態系統管理學領域跨界進入法學領域。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跨界進入環境資源立法,其現實表象是技術規則法律化,而實質則是生態價值法律化的發展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生態保護日趨受到重視的背景下,環境資源立法內容和法律體系結構方面,有關生態系統完整理念的立法表述逐漸增多,以生態系統完整為價值基礎、平衡人與自然關系的規則設計,在環境資源立法中的比重逐步提升。
一是立法價值及理念層面。人類對環境資源的識別和開發利用呈漸進式發展過程,環境資源蘊含的經濟價值可以很好地為當地人創造更好的生活、生產條件,凡是能夠被人利用的環境資源均是立法設定使用權的客體,[11]274-282從自然之物轉化為法律之物,并賦予其經濟屬性和經濟價值。長期以來由于人類對環境資源生態屬性的忽視,已經造成了環境資源的經濟性與生態性之間的沖突碰撞。20世紀70年代以來,將人類與其所處的生態環境視為一體,摒棄以往為了人類自身利益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生態正義”價值觀在全球范圍廣泛傳播,而在“生態正義”價值觀下如何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現狀,法學領域給出的回應便是法律生態化。[12]法律生態化以生態正義等為主要價值取向,即由單純注重調整當事人對環境資源進行占有和支配時所產生的社會關系,擴展至在尊重環境資源自然屬性和經濟規律的基礎上,考察其中可能涉及的人與生態系統的關系。[13]但是,傳統法律領域的生態化只是在局部對生態利益的引入和接納,二者協同的前提在于二者之間形成共性的交集。[14]同樣,環境資源法生態化有具體限定性,即圍繞直接支配環境資源取得經濟利益的立法、司法、執法、守法過程中,要求調整對經濟利益的片面倚重,對既定法律價值進行修正,在局部引入和接納生態利益訴求。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是生態化的內容之一,在環境資源立法中吸納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意圖在價值層面肯定環境資源不是由私主體享有完全支配權的財產,而是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利用同時負擔著巨大經濟利益和維持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公共利益。[15]例如,《2017年荷蘭環境與規劃法》(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制定過程中將生態系統方法作為主要范式,而生態系統方法要求環境治理在保持生態系統完整性的同時,整合不同利益與空間用途。[16]
二是制度規則層面。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在立法中有不同的規范設計,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以地理區域為基礎的制度規則,如自然保護區、功能區劃制度等;另一類是以技術標準為基礎的制度規則,如生態風險監管、環境管制等。總體而言,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規則化是以法律為原本、為基礎,其著眼點和落腳點都在于如何通過制度調整功能上的“進化”,促進和加強對環境資源的法律保護。[17]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的實現依賴于立法對環境資源治理規則的涵攝,由于生態理念通常被用作環境政策管理領域的一種評價工具,立法將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貫穿到規則制定、修改和健全過程時,必然需要糅合生態系統評價指標與管理規則,運用理性的抽象形成各種形式化的法律概念和規則,適用于環境資源治理法律關系之中。例如,在美國生態系統完整理念經由《1972年美國清潔水法》(Clean Water Act)被
立法首次認可,該法將“恢復和保持國家水域的化學、物理和生物完整性”作為立法的唯一目標。《1988年加拿大國家公園法》(National Parks Act)將維護生態系統完整性確定為國家公園分區和使用管理的首要原則,并使用評估生態系統完整性的基本框架評估各個國家公園的相對生態完整性,[18]該法將生態完整性定義為“一種被確定為其自然區域的特征并可能持續存在的條件,包括非生物成份、天然物種和生物群落的組成以及豐度、變化率和支持過程”。《1996年加拿大海洋法》(Ocean Act)規定了改變海洋治理的方式,包括:促進和發展政府組織機能,以加強聯邦政府內部和與其他各級政府協調合作管理海洋;通過實施綜合管理,在考慮生態系統完整性和保護的同時,考慮經濟和社會問題,讓公民參與其中;提升管理和公眾意識。[19]《加拿大海洋法》將“考慮生態系統完整性”作為海洋治理方式,實際上也是認可將生態系統完整性作為一項原則或基本政策,以指導其改變海洋治理的方式。《2015年桑給巴爾環境管理法》(Zanziba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t)第6條規定:“就本法案而言,每個人在履行本法案賦予他的職責時應考慮以下原則:……(c)生態系統完整性原則;……”。《2009年坦桑尼亞水資源管理法》(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ct, Tanzania)第五節同樣將生態系統完整原則作為基本原則加以規定。《2015年新西蘭環境報告法》(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ct)則使用了“生態完整”(ecological integrity)的表述,該法第1部分第4條將生態完整性定義為“土著生物和非生物特征及自然過程的全部潛力,在可持續社區、生境和景觀中發揮作用”。
(三)無居民海島治理法治化與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的相洽性
無居民海島治理法治化旨在從國家管轄的無居民海島及其周邊海域的資源、環境的整體利益出發,通過法治的形式組織協調、綜合平衡各方主體在開發利用無居民海島中的關系,以達到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合理開發海島資源,保護無居民海島及周邊海域生態環境,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目的。
無居民海島是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復合體。20世紀60年代末,麥克阿瑟(Robert McArthur)及威爾遜(Edward Wilson)發表的《島嶼生物地理學》指出,孤立的島嶼會產生較高的物種特有性,與外部相對隔絕(isolation)的狀態限制了新物種到達島嶼的可能性,……使島嶼構成獨立的生態系統。[20]20世紀60年代至今,有關無居民海島生態系統完整的研究不斷深入,無居民海島在動植物資源開發利用中具有的獨特價值得到普遍認識和關注。無居民海島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一體性具有兩層含義:一是每一個無居民海島實體都是一個相對完整的自然地理單元,不存在獨立于該島嶼生態系統之外而又從屬于其的地理單元。[21]二是無居民海島與周邊海域生態構成具有一體化。無居民海島是海洋資源和環境的復合區域,生境具有多樣性,島嶼陸地、海岸、島基和環島淺海四個生境都具有特殊的生物群落,被廣泛認為是研究生態學和進化生物學基本問題的模型系統,保護海島與保護海域內的珍稀動物、植物、自然景觀等密不可分。因而,生態系統完整性不僅涵攝無居民海島地理單元內部環境資源體系,也強調島嶼與周邊海域自然生態系統、珍稀野生物種天然集中分布區、海洋生物多樣性等的區域一體化特征。
20世紀80年代至今,人與自然耦合(nexus)的思想逐漸在生態系統綜合思維中得到重視,基于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綜合管理思想逐步成為環境資源治理的主流思想,并逐步作為指導環境資源立法的基礎理論。[22]為滿足無居民海島可持續利用,主要沿海國家有關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監督管理的職權趨向于集中化,但集中程度存在國別差異,例如,新西蘭將有居民海島與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監管職權集中于環保部;美國聯邦環境保護署在海島生態系統的維護方面擁有統一的執法權;[23]澳大利亞農業、水利與環境部對赫德島、麥克唐納群島等亞南極群島行使專職管轄管理,進入及在群島從事活動,均需要得到該部的特別許可;對于其他澳大利亞島嶼則依據相關立法,行使一般意義上的生態環境保護、生物資源養護、自然能源開采等監督管理職權;[24]加拿大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監管集中于環境部,并根據立法授權負責環境執法與野生生物執法。[25]從以上國家的無居民海島管理模式看,無居民海島利用及保護監督管理權在外部表征上是相對完整的,專職機構的管理職能覆蓋無居民海島利用及保護管理的不同方面。在立法層面,系統治理只有上升到制度層面、產生法律效力,才有可能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并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對此,一些國家開始反思依據森林、土地、草原、野生動物及植物等環境要素對海島環境資源進行拆分式管理、采取分而治之的立法模式,[1]88-90沿海國(島嶼國家)在海洋事務立法以及海洋區域管理方面已出現一種明顯的系統化的趨勢,表現為對無居民海島的利用與保護采取綜合性立法或專門立法,例如《韓國無居民海島保護及管理法》《克羅地亞島嶼法》《美國島嶼保護法》《印度尼西亞海岸帶及小島管理法》等。[26]可見,系統治理與綜合立法具有互為因果和目標統一的內在聯系,無居民海島治理的法治化過程就是按照無居民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系統性及其內在規律開展,對相關生態要素進行綜合治理的過程。
二、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對無居民海島治理的法治化指引
系統完整是無居民海島治理中生態要素與依法治理的契合點。海島的環境資源特性決定了無居民海島治理適宜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作為價值基礎,而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也需要通過立法予以固化,在具體的制度規則中體現其合理性與優越性。
(一)確認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的生態取向
無居民海島權屬是海島客體與社會制度相結合形成的,具體是指關于海島自然資源所有、使用以及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由誰承擔的一系列規定構成的法律規范系統。無居民海島權屬具有國際法與國內法兩層含義,國際法中的無居民海島權屬確定國家排他性權利的地理空間范圍,國內法中的無居民海島權屬按照市場經濟機制進行資源配置。無居民海島作為國家主權支配的客體,具有財產屬性和資源屬性,但該種屬性并不能直接產生經濟價值,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有償配置和轉讓,成為一種特殊的物質產品,具有一般商品的使用價值,能滿足人某種需要,由此發生的財產關系受私法性規范的調整。無居民海島由抽象的領土價值轉化為能夠產生市場經濟價值的財產,全賴國內法中的海島權屬制度設計。因此,確認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的生態取向,是從國內法出發確認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的公共屬性,要求權利人在實現無居民海島經濟價值的過程中,遵循生態環境義務,限制自身行為。
此項工作具體可分為以下兩個環節。
第一,識別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的生態屬性。無居民海島是不同類型自然資源的復合體,其權屬在國內法中從屬于自然資源權屬,受到當事國土地權屬制度的影響,兼具公法與私法性質,內容包括無居民海島所有權與使用權。在無居民海島國家所有權(領土主權)高度穩定的情況下,為實現環境資源的有效利用,國內法將無居民海島使用權從所有權中分離出來,使之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權利形態并且能夠交易,圍繞無居民海島所設計的自然資源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本質是財產權。基于此,一方面要識別生態環境保護義務的正當性,即傳統自然資源權屬制度關注的是發展經濟的自由,認為自然資源是可以任意使用的自由財產,[11]264權利是自然資源權屬制度的核心范疇,突出權利本位是自然資源權屬制度邏輯推衍中必然導向。課以權利人生態環境保護義務,要求包括無居民海島所有人與使用人在內的權利人承擔生態環境保護的義務,即面臨對其行使財產權的限制。因而,能否課以此類義務無疑是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生態化邏輯推衍中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要識別生態環境保護義務的內容取向,即自然資源權屬調整的對象是與人類社會發展有關的、能被用于產生使用價值,并影響勞動生產率的自然諸要素。海島是多種自然資源相互依存構成的資源綜合體,人類對海島資源開發利用的內容隨著生產力發展而不斷更新,開發利用的資源內容不同,相應的權屬內容也不同。把經濟活動、權利人的行為限制在無居民海島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的目的取向能否在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架構內悉數轉化為法律義務,以及如何設計生態環境保護義務的主要內容與功能,亦需要加以明確。
第二,確認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的生態屬性及內容取向。海島是陸地卻為海洋所環繞,是自然資源卻也是生態環境的組成部分,其作為資源與環境的綜合體,兼具海洋與陸地屬性。無居民海島作為一類重要的自然資源,對其利用不僅關系著使用權人的利益,更關乎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尤其是與有居民海島相比,無居民海島具有稀缺性、環境脆弱性,不同類型、區位無居民海島的生態環境和資源稟賦各有不同,這決定了對其經濟價值的過度開發會引起海島生態環境的破壞,進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7]借用經濟學中的產品理論認識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的生態屬性可以發現,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應屬于具有有限非排他性或非競爭性、介于私人產品和純公共產品之間的準公共產品(quasi public good)。進一步而言,在土地公有制下,無居民海島為國家所有,其他主體取得的只能是使用權,即便在土地私有制下,權利人對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的處分也是受到多重限制的,故而,無居民海島可以作為私人產品被加以消費,但消費行為或過程又受到諸如環境保護、國家利益等諸多限制。在當代社會本位的話語之下,公共利益作為一種獨立的利益形式也就日益突出。[28]從國別法角度看,盡管無居民海島在權屬制度上可以為私人所有,但其具有的海洋權利主張功能、資源使用功能、生態服務功能具有鮮明的公共利益色彩,一旦上述功能遭受破壞或價值出現減損,受影響的不僅僅是享有無居民海島使用權或所有權的私主體的權利,還包括社會公共利益,例如,無居民海島的不當使用導致珍稀物種的滅絕等。因此,準公共產品涵攝了無居民海島治理中的公共利益,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絕非僅針對某一類人權利數量或質量的保護,從公共利益著眼,無居民海島權屬應屬于國家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給予無居民海島法律庇護是對社會公共利益的整體保護。
(二)實現無居民海島治理生態要素的制度化集合
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指通過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使環境資源利用及保護管理體系日趨系統完備、不斷科學規范、愈加運行有效。依法治理是無居民海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礎要件,制度體系則是依法治理的前提保障,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推進無居民海島治理,必定是建立在具有科學性、合規律性、合理性的良法之上。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的價值在于統合環境立法與資源立法的價值取向,改變按照環境資源要素進行二元立法的傳統模式,基于無居民海島系統化治理要求,抽象出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共同遵循的一般性規范,用以指導和完善無居民海島治理制度體系。對此,可以從理念指導、規則構造、路徑選擇三方面理解。
第一,保護優先在無居民海島治理中具有優先序位。對于無居民海島開發利用而言,若想充分發揮其經濟價值,首先就要保障無居民海島自然資源的存量,同時維持海島生態環境的穩定,才能夠保持海島資源生產力的持續增長或穩定的可用狀態。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就是將生態保護的要求納入無居民海島治理各階段,使用權人在利用海島資源及環境創造經濟利益的同時,需承擔生態環境保護的義務,其對島嶼的利用方式、范圍與程度都要受到嚴格限制,不能造成不應有的生態和環境的破壞。但是,法律生態化要解決的問題是何種價值應該受到優先保護,以及在實現不同價值時應優先實現何種價值。[29]無居民海島作為具有多重價值的對象,其利用與保護在行為模式上呈現價值變量的關系,二者在立法中不存在恒定的價值序位。課以權利人生態環境保護義務,不等于極端化環境價值優先和生態環境保護義務在海島權屬制度中的泛化。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的生態取向不等于不計代價的生態環境保護優先,因為,極端化環境優先價值不僅會導致立法“先天不足”和規則僵化,也會不恰當地縮減
行政機構在
無居民海島管理中的裁量余地,遮蔽無居民海島治理的復雜性。故此,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對于無居民海島治理的既定法律價值與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修正,從而在觀念和制度局部引入和接納生態利益訴求,實現無居民海島利用與保護的良性互動。
第二,以系統治理發展無居民海島治理規則。習近平總書記從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視野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的論斷,強調“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無居民海島與有居民海島構成的海島生態群落,以及無居民海島的島體、灘涂、島基以及環島淺海四個子系統,是一個整體,不宜割裂。在確認保護優先理念的前提下,必須承認國內法中自然資源保護與生態環境保護在規制對象、價值取向上存在差異。自然資源保護屬于自然資源立法范疇,保護對象建立在物質實體基礎上,保護內容是維持及改善資源所具有的使用價值。[30]生態環境保護屬于環境立法范疇,保護對象以環境的生態功能為基礎,立法目的在于保護和改善人類生存環境和自然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協調人類、社會與環境的關系,包含解決與預防環境問題和生態破壞問題兩方面的法律規范。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章第六節規定的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是對破壞資源保護罪與破壞環境保護罪的總稱,兩類犯罪各有獨立的犯罪構成和罰則。然而,區分自然資源保護與生態環境保護,并不意味自然資源保護與生態環境保護存在一個程式化的價值排序,在無居民海島治理中二者亦具有均等性。因為,無居民海島與土地、水、礦產、森林等單一屬性自然資源不同,它是多種資源的復合體,因而無居民海島管理及立法天然具有綜合性、系統性特征。以環境或資源單一要素為標準的規則體系適用于無居民海島管理,只會人為割裂生態系統之間的內在聯系,降低環境資源治理效能。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思想實施無居民海島系統治理,不僅要求從生態整體主義價值觀出發,將無居民海島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加以保護,而且也需要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角度,將無居民海島治理與社會公共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故而,無居民海島治理法律規則體系必須建立在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一體化管理、整體化保護理念之上,以共同的法律理念和價值訴求連通具體法律規則,指導無居民海島治理制度體系構造。
第三,技術規則法律化是推動無居民海島治理的制度路徑。生態系統完整性概念的本源在于生態學,即便其后被生態系統管理學作為分析生態系統穩定性和自組織能力的評價工具,其評價標準依然需要與自然科學實證研究保持相洽性和同步性。同樣,立法對于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的吸納建立在自然科學意涵基礎之上,這也是構建科學的法律制度體系的基本歸宿。實現無居民海島治理法治化、科學化,要遵循生態系統管理科學規律,追溯自然科學對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理解。例如,無居民海島治理中的功能區劃、風險預防、管理計劃等具體規則,無一不是發端于生態學和管理學層面,然而,為避免技術規則的僵化,立法又賦予其一定的靈活性,作為對可能出現的不合理情況的修正措施,滿足功能實現與技術治理層面對法律規制的需求。進一步而言,滿足制度理性與技術理性相洽的運行邏輯,一方面需要無居民海島治理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制定、修改、廢止要同時滿足基于事實的“合規律性”和基于效用的“合目的性”,[31]即在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支配下,對無居民海島生態系統空間分布特征及生態敏感性空間分異現象背后客觀規律,有準確的、可驗證的和普遍適用的認知,并且在客觀事實和科學認知基礎上采取的立法技術和立法手段,能有效地實現立法目的;另一方面需要以發展的視角追蹤生態系統完整性實證研究的技術演進,增強法律的預見性、前瞻性。
(三)推動無居民海島治理生態效能的法治化運行
治理能力現代化則是運用制度管理環境資源事務,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現代性能力不斷強化。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指引無居民海島治理法治化是一個動態過程,法律體系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在完善法律體系的同時,還需要將靜態的法律規范付諸實施,使法治機器高效良性地運轉起來。[32]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擢升無居民海島治理效能,意在從條塊式分割式管理轉為系統性綜合治理,解決不同主體對同一海島環境資源主張權利時所發生的沖突或重疊,提高對無居民海島系統治理和綜合施策的能力。對此,需要從如下三方面考慮。
一是治理模式由分離型向綜合型轉變。生態管理公共性導致了權力的重疊與競合,以職能部門專業分工為基礎的分離型管理模式弊端日漸突出,不斷遭到來自學者和管理者的詬病,
[33]該模式在實際操作中導致無居民海島的開發利用及保護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和協調,[34]各監管機構權限狹窄且分工過細,在進行決策或制定長期發展規劃過程中,從部門利益出發作出的決策往往缺乏宏觀性把握和綜合考量,與無居民海島的生態系統完整性整體性管理需求無法契合。每個無居民海島都是相對獨立的生態環境地理單元,? 基于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提升無居民海島治理效能,需要在綜合管理框架內考慮島嶼資源及環境相關問題,形成一種全方位治理體系和管理模式。
二是治理方式注重陸海統籌。海島兼具海洋與陸地屬性,其管理既不同于土地等資源管理,也不同于森林、海域、水流等自然資源管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基于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綜合管理思想日益成為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治理的主流,2018年聯合國大會第73屆會議上《海洋和海洋法:秘書長的報告》再次強調:“海洋空間問題,包括在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及其資源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彼此密切相關,需要通過統一、跨學科、跨部門做法進行整體考慮。……有許多現成的管理工具可促進人類海洋活動跨部門綜合管理方法,例如沿海區綜合管理、海洋空間規劃,包括利用劃區管理工具和生態系統方法。”[35]以生態系統完整理念完善無居民海島治理既需要立足無居民海島的陸地、海洋環境資源特點,對島嶼資源開發、島嶼及其周邊海域生態保護等領域綜合調控,也需要協調發揮島嶼經濟功能、社會功能,實現綜合效益的最大化。
三是治理內容兼顧島嶼資源及環境。無居民海島生態系統類型豐富,自然環境發育獨特,與外部生態系統的物質流、能量流交換匱乏,具有環境與資源一體性特征。在立法調整內容上,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針對的客體具有同一性,二者相互結合、交叉,在立法中很難截然分開。[36]采取環境立法與資源立法二元化立法路徑的直接后果,是以條塊分割的方式規制面積狹小且空間獨立的海島區域,依照不同生態要素設定監管權,實則是從不同方面共同管理無居民海島的環境資源,由此產生了管理措施
的重復或沖突,海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被人為割裂。
三、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完善中國無居民海島治理的法治路徑
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為著眼點完善中國無居民海島治理,需要實現無居民海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法治化,按照制度理性與技術理性相統一的邏輯,對無居民海島進行法治化治理,在治理體系層面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規則體系,在治理能力層面推動系統治理、綜合施策,將法律規則體系轉化為治理效能。
(一)中國無居民海島治理與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的差距
中國無居民海島治理具有依法治理和綜合施策的特征。中國無居民海島的管理法律體系具有層次
性,《海島保護法》是中國海島管理領域唯一一部專門性“法律”,該法規定無居民海島屬于國家所有,無居民海島的利用及保護統一由海洋主管部門負責
。《全國海島保護規劃》按照海島的區位、自然資源、環境等自然屬性及保護、利用狀況,確定可利用的無居民海島;可利用的無居民海島的開發利用活動適用批準制度,應當遵守相關的保護和利用規劃,采取嚴格的生態保護措施,規劃并適用相應的污染防治措施,避免造成海島及其周邊海域生態系統破壞。未經批準利用的無居民海島適用嚴格保護制度,禁止進行生產、建設、旅游等活動。在《海島保護法》之外,無居民海島治理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主要為部門規章,內容涉及無居民海島測量、命名、有償使用、統計調查等事項。除前述中央立法之外,還有大量的地方性無居民海島立法,既承擔著實施《海島保護法》等中央立法的義務,也發揮著無居民海島治理的地方自主性。從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審視和評價中國無居民海島治理,存在如下差距。
第一,無居民海島治理立法模式亟需修正。無居民海島治理立法模式,是指在立法技術上如何處理無居民海島利用與保護之間的關系。當前中國環境資源立法存在兩種模式:一種是對資源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分別立法,例如海域利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簡稱《海域使用管理法》)調整,海域生態環境保護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簡稱《海洋環境保護法》)調整;前者以加強海域使用管理,維護國家海域所有權和海域使用權人的合法權益,促進海域的合理開發和可持續利用為立法目的,后者以保護和改善海洋環境,保護海洋資源,防治污染損害,維護生態平衡,保障人體健康為立法目的。另一種是對資源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實施綜合立法,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簡稱《漁業法》)作為“母法”系統規范 “漁業資源的保護、增殖、開發和合理利用”,在該法之下對漁業資源的使用、保護則分別由《漁業資源增殖保護費征收使用辦法》《水產資源繁殖保護條例》等“子法”調整,采取此類立法模式的還包括森林立法、淡水資源立法、草原立法等。中國無居民海島的利用與保護規定在《海島保護法》中,而該法與上述海域立法和漁業立法模式均不相同。雖然《海島保護法》名為“保護”,但從立法目的和立法內容看,該法既調整無居民海島及其周邊海域的生態系統保護,也規范無居民海島權屬、開發利用原則、主管機關、利用規劃、用島申請等內容;如果從綜合立法視角看,《海島保護法》又缺失無居民海島使用權的規定,相關規則以部門規范性文件或部門規章的形式加以規定,由此形成“上位法滯后、下位法先行”的模式特征。
第二,無居民海島集中統一管理模式存在局限性。依據《海島保護法》第5條第2款的規定,無居民海島的利用及保護統一由國家海洋主管部門(自然資源部門)負責;該法以“可利用”為標準區分對待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保護,對于可利用無居民海島要求確認污染防治措施,做好污染物無害處理,并輔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簡稱《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確立的環境保護稅制度;未經批準利用的無居民海島則維持現狀,適用立法一般性規定。這種無居民海島分類管理模式在運行過程中存在如下問題:一是可利用的無居民海島審批前集中管理與審批后分散管理并存。依據《無居民海島開發利用審批辦法》第5條的規定,經國務院、省級政府審批,無居民海島可以用于交通運輸、工業建設、旅游娛樂、倉儲物流等開發利用活動。申請主體經審批獲得使用權以后,對于無居民海島治理“回歸”至分散管理模式,即無居民海島的不同開發利用活動仍需要環保、文旅、交通、財稅等部門批準方可具體實施。在無居民海島使用權終止之前,對于其開發利用活動的監管與有居民海島監管幾近相同,并且權責協調機制的滯后加重了部門之間的矛盾。二是以利用為標準對海島實施區別保護割裂了生態系統整體性。海島有無居民與海島資源環境治理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37]例如,葫蘆島(財神島)屬于2011年中國公布的“第一批開發利用無居民海島名錄”的海島,也是廣鹿群島中唯一列入開發利用名錄的海島。[38]但實際上早在1997年該島就已經建設度假村,并非單純的漁業用島;而在葫蘆島周圍既分布著礬坨子等未列入開發利用名錄、生物多樣性豐富的無居民海島,也毗鄰廣鹿島等有居民海島。[39]《海島保護法》第30條規定從事可利用無居民海島的開發活動,應避免造成該島及其周邊海域生態系統破壞,實際上,可利用無居民海島、有居民海島的生產活動不僅影響了附近無居民海島的生態環境,[40]而且立法對于可利用無居民海島的開發利用活動對同一生態圈之內的其他無居民海島的影響也欠缺應有的考慮。
第三,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模式滯后。生態環境治理是指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主體針對環境公共問題,通過采用各種制度、技術和工具等途徑來共同合作以實現環境治理目標的過程。[41]中國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采用政府單一治理模式,這種模式的形成與無居民海島權屬制度、治理資金財政配給等治理要素密切相關,但是在運行過程中也逐漸顯現出一些弊端:一是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驅動單一化。既有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采取“命令—控制”模式,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門)是唯一的治理責任主體,而囿于治理成本、治理需求、技術支持等方面的困境,以及消費主體“搭便車”,導致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出現時滯性現象。二是治理資金機制結構局部失衡。無居民海島生態修復資金主要來源于兩部分,即中央財政通過一般公共預算安排的修復基金和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單位和個人(賠償義務人)繳納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金。從近年來相關環境公益訴訟司法實踐看,半數以上的加害人被要求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責任或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42]現實中,海島生態環境修復周期長、難度大、費用高,需要長期穩定的資金供應,賠償義務人繳納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與實際需求相比,無異于杯水車薪,[43]而高度依賴政
府財政撥款的治理項目面臨資金支付不可持續的風險。
(二)以綜合立法統攝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治理
在尊重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分異規律的前提下,從具體的社會事實和管理規則出發進行抽象歸納,將各種實際存在的無居民海島保護及利用規則涵攝進來,從中抽象出指導和規范無居民海島管理的基礎性法則,對各類權利主體予以統一規范,由綜合管理向系統治理、綜合施策邁進,這也是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治理綜合立法的應有之義。
綜合立法是無居民海島治理單項要素的制度化集合。“綜合立法”的表述在國內學者涉及立法模式的研究中比較常見,但是不同學者對于“綜合立法”含義的理解存在較大差異,有的學者將綜合立法表述為中央與地方立法、基本法與部門法、制定法與習慣法的綜合;[44]有的學者從立法任務、外部關系、方法層面、目的層面來界定綜合立法的含義;[45]也有學者從實體和程序兩部分來表述綜合立法。[46]從2009年至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工作文件中也多次提到推進綜合立法,但并沒有界定何謂“綜合立法”。綜合立法兼具立法技術和立法模式的含義,其要旨在于對相關實體規則的整合,注重規則設計的一體化。因而,基于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綜合立法統攝無居民海島治理,并不意味著必然以制定無居民海島單行法作為實踐路徑,而是借由綜合立法實現無居民海島治理法治需求的資源整合、供需匹配和共創驅動。從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兩個維度看,完善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治理可以從協調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關系,鼓勵地方立法“先試先行”入手。
無居民海島中央立法具有統攝性。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無居民海島中央立法是地方立法的上位法依據,對地方立法具有原則性控制的功能;二是中央立法面對的是不同行政區劃、不同環境資源稟賦、不同區位類型的無居民海島,需要采取相對概括的形式,將適用于海島利用與保護的原則和規則集中起來,對無居民海島治理的立法理念、立法目的、基本原則、制度規則、法律責任等內容作出綜合性、綱領性的規定,以統一的治理理念統籌制定無居民海島治理法律規則。在表現形式上,無居民海島治理綜合立法既可能是在現有立法框架內把同屬于環境資源的規范進行系統的、完整的、具有內在邏輯性的闡述,也可能是將無居民海島治理領域的相關規范匯集在一起,經過立法技術處理,以法典的形式呈現。但是,無論中央立法采取哪種編纂方式,無居民海島治理綜合立法都不是“包裹立法”。因為,無論是著眼于現實、從中國法制國情出發,還是立足于法理、從立法可行性論證,無居民海島治理綜合立法既不可能將所有涉及無居民海島利用和保護的實體性與程序性規范、公法與私法規范納入一部立法中,也不可能將森林立法、野生動植物立法、礦產立法、海域立法、土地立法等部門中涉及無居民海島保護及利用的規則抽出納入綜合立法。因此,無居民海島治理綜合立法需要整理的內容僅僅是無居民海島治理實體性規范,“綜合”表現尊重無居民海島生態系統完整性,注重海島保護與合理利用的一體化,規定集中統一管理、跨部門(區域)協調等治理機制。對于無居民海島治理綜合立法可能涉及的無居民海島使用權等私法內容,以及野生動植物、礦產資源等其他類型自然資源治理問題,一方面,可以通過指引性規定由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具體調整,而不是由綜合立法重復規定,避免破壞法的安定性和價值秩序。另一方面,在“特別法優于一般法”法律適用原則基礎上,可以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處理。如果野生動植物、礦產資源等類型自然資源的利用及保護與無居民海島治理耦合而具有特殊性,則需要綜合立法加以具體規定;反之,則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等其他立法的規定。
無居民海島地方立法不僅是中央立法的有益補充,也是中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地方立法在中國法律體系構建過程中發揮了“先行先試”的作用,許多中央立法的出臺都始于地方立法的經驗摸索。[47]中國海岸線漫長, 北至遼寧, 南抵海南,不同省份、不同地理緯度無居民海島的生態結構、社會經濟活動、周邊海域狀況、開發價值及用途,以及在實現國家海洋戰略中發揮的作用,各不相同。例如,天津、河北僅擁有個別近岸泥質沖擊島,無居民海島面積狹小且與周邊海域具有生態一體化特征;而浙江、福建沿海無居民海島不僅數量眾多、分布廣泛,而且這些島嶼大小不一、功能不盡相同,生態要素構成也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地方立法在制定之初,要根據本地無居民海島的實際情況,既需要與上位法相呼應、使立法適應本地海島管理的具體情況,又需要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及無居民海島管理需求,在法律框架內對中央立法予以細化、補充和完善。故而,與中央立法相比,地方立法是以本區域內無居民海島治理共性內容為基礎,采取具體的形式,規定適用本區域海島利用或(和)保護需求的制度規則。尤其是在面對中央立法原則性強、修改程序繁雜,甚至存在空白的情況時,地方立法往往需要充分發揮“地方智慧”和能動性,在解決法律適用空白的同時,為中央立法積累地方法制經驗。例如,2009年《海島保護法》出臺之前,《寧波市無居民海島管理條例》(2004年發布)、《廈門市無居民海島保護與利用管理辦法》(2004年發布)等地方性海島管理立法已經生效實施,為《海島保護法》中的無居民海島管理制度設計積累了寶貴的立法經驗。在協調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關系中,以地方立法推進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治理,需要滿足以下三項合法性條件:一是不得與上位法相抵觸。無居民海島地方立法的上位法不僅包括《海島保護法》等規范海島利用與保護的特別法,也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簡稱《立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簡稱《行政許可法》)等一般法。無居民海島地方立法需要滿足《立法法》第72條(地方立法不得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行政許可法》第15條第2款(地方性法規設定行政許可的排除性范圍)等強制性規定。二是遵循法定程序及規范化制定程序。即無居民海島地方立法應當滿足《立法法》第72條第4款、第98條等法律法規有關備案、批準的程序要件。三是在法律行政法規框架內發揮地方立法的能動性。在鼓勵地方立法對地區無居民海島治理中的新問題“先試先行”時,不得對法律、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專門性規定作出變通性規定
。
(三)以系統治理增加無居民海島集中管理的協同性
權屬制度是中國海島監督管理機制分野的基礎。國家海洋主管部門(自然資源部門)統一負責無居民海島的利用及保護,在無居民海島國家所有權制度基礎上,修正無居民海島監督管理模式既存問題,依法對無居民海島開發利用及生態保護施行系統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可以考慮以系統治理、協調執法補強目前無居民海島的監督管理模式。
無居民海島集中管理需要各方聯動配合才能形成整體治理效應。基于“利用名錄”對無居民海島進行分類管理,是造成無居民海島審批前集中管理與審批后分散管理并存的主要原因,也使得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整體性目標回歸至“碎片化”的實現方式。強化無居民海島的源頭治理、綜合施策效能,應當從內部構成與外部協調兩方面著手。在內部構成層面,對同一生態系統內相鄰、相連的各類無居民海島,可以考慮打破因行政區劃、資源要素分類造成的割裂局面,依照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進行歸并。一方面,將無居民海島審批后原先分散在自然資源各管理部門的執法權歸攏起來,統一由海洋執法部門來行使環境資源與生態保護領域的執法權。另一方面,2020年自然資源執法綜合監管平臺啟用后,實現了自然資源行政執法流程的數字化,借助大數據分析平臺對合并后的執法管理實效采用科學的量化評價指標,根據評價結果動態調整自然資源管理部門內部事權分配組合。在外部協調層面,按照行政效能原則的要求組建綜合執法機制。無論是執法權歸并,抑或優化無居民海島行政主管部門(自然資源部門)與其他行政主管部門執法機制,落腳點均在于能否提高無居民海島治理行政效能。按照行政效能原則的要求,綜合執法機構應獲得履職所需的手段。從無居民海島執法制度發展脈絡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執法分散格局的產生和持續,與行政管理需求緊密相連,不僅有充分的合憲性支撐,并且得到法律的確認。對此,無論是在制度層面,還是技術支持層面,協調執法機制比歸并執法職能更為現實。為此,可以考慮在行業執法的基礎上,對列入可利用名錄、已經實施開放利用的無居民海島,將審批后的末端執法納入源頭決策之中,協同推動海洋主管部門與其他行業執法部門組建常規聯合執法機制,建立常規的信息共享、共同協商與聯合決策機制,或者針對《無居民海島開發利用審批辦法》第5條規定的無居民海島的開發利用活動,在與交通、旅游等主管部門工作會商機制基礎上,組建臨時的專項聯合執法機制。
(四)適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推進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
面對無居民海島生態系統及綜合治理的復雜性,傳統由政府主導的線性管理模式已經不能對無居民海島治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給出有效的解釋和應對方案,[48]增加無居民海島綜合施策系統協調度和協同效應,就必須推行社會治理模式,實現多元主體的合作共治。建立健全基于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無居民海島治理機制,需要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力量參與無居民海島治理,統籌社會各種資源支持無居民海島治理。2020年《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提出“提高市場主體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形成導向清晰、決策科學、執行有力、激勵有效、多元參與、良性互動的環境治理體系”。在無居民海島治理領域,明晰政府主管部門、相關企業、社會公眾等各類主體權責,堅持多方共治,這是無居民海島治理的發展趨勢。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模式)最初作為將社會資本引入社會公共基礎設施等領域,彌補政府財政資金的不足,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一種項目運作模式。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下,PPP模式已經拓展至其他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五部分提出,建立健全社會組織參與社會事務、維護公共利益的機制和制度化渠道。以PPP模式完善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旨在構建多元主體參與協商共治的秩序結構,體現無居民海島治理方式的法治化和治理手段的多樣性。對此,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利用市場機制承接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職能。在無居民海島國家所有制和使用權流轉制度的框架內,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領域除了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之外,還有大量的具有一定排他性但非競爭性(例如無居民海島生態旅游)的準生態環境公共產品。將PPP模式引入無居民海島治理,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混合所有制等多種方式,目的在于引入社會化生態產品供給模式,引導社會資本投入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修復等,形成多元化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2020年自然資源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典型案例》《社會資本參與國土空間生態修復案例》中,將生態修復方案、土地出讓方案一并通過公開競爭方式確定同一修復主體和土地使用權人,并分別簽訂生態修復協議與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成為優化此類準生態環境公共產品供給的典型模式。該模式在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中同樣具有適用性。具體而言,在市場化出讓無居民海島使用權的過程中,通過成本補償機制和使用權出讓平臺機制,將社會資金引向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領域,平衡生態環境治理與關聯產業之間的成本收益,以實現準生態環境公共產品的可持續供給。
二是建立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磋商協調機制。PPP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平等合作、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社會組織既是政府與社會公眾溝通、互動的媒介,也是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結構的合作主體。PPP模式對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的主觀能動作用體現在:一方面,通過建立程序和實體磋商機制,確保有關利益相關者和行動者有效參與磋商進程、治理目標和行動決策,以及視情況參與治理方式的執行。另一方面,使得無居民海島開發利用功能理念從最初以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的,轉移至無居民海島的可持續利用,限制對無居民海島經濟價值的無限制追求和盲目的開發利用。
三是確立具體的治理績效標準。在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中適用PPP模式需要利用指標賦值的方法,實施量化績效考核,否則離開具體標準空洞地談論無居民海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PPP模式應當包括定性和定量評價指標,即定性評價指標包括全周期整合程度、風險識別與分配、績效導向與鼓勵創新、潛在競爭程度、政府機構能力、可融資性等六項基本評價指標,用以評價PPP模式在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中的適用性、可執行性。根據生態環境治理需求,定量指標應當包括生態環境要素、經濟要素、社會要素、技術要素等四類評價指標,每一類評價指標可以繼續被具體量化,例如,生態環境要素評價指標應包括植物覆蓋率、存活率、生物多樣性等子評價標準。
概言之,通過評價指標的逐級量化,建立反映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效能評價體系和外部價值形成機制,促使技術規則制度化。多元主體參與協商共治的治理秩序結構,通過金融杠桿和利益傳導機制將社會資金引入無居民海島治理領域,不僅可以滿足政府對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實現系統治理、源頭治理和綜合施策的需求,突破治理資金籌措、成本投入等問題,也有助于社會組織通過公平競爭參與無居民海島生態環境治理,在生態環境治理項目與關聯產業的融合發展過程中,獲得充分的經濟補償。
四、結語
綜上所述,無居民海島治理是在海洋綜合管理框架內集中考慮所有與海島環境資源治理相關的問題,形成一種全方位治理體系,體現系統治理與可持續利用理念。無居民海島生態系統空間結構及其組分不存在絕對的時間或空間邊界,系統結構組分隨人為或自然因素干擾而發生變化。以生態系統完整性理念指導無居民海島治理,按照技術規則與制度理性相統一的邏輯,借助生態系統管理工具對無居民海島進行法治化治理,既是尊重生態系統空間分布特征及生態敏感性空間分異規律的需要,也是法律與技術規則協同作用、相互補充的體現。
法治是推進無居民海島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
代化的頂層設計。將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治理擢升至公共利益層面,以生態理念為基礎推動無居民海島治理法治化,體現了生態系統完整理念對立法的指引。在制度層面保障無居民海島利用及保護行為的協同性、統一性和有序性,需要運用立法手段,發揮立法在社會治理中的價值指引和功能評價作用,增加無居民海島治理系統協調度和協同效應。以綜合立法作為無居民海島治理的制度牽引,規范治理職能配置,協調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關系,鼓勵地方立法“先試先行”,消除治理環節有法不依的遁詞和無法可依的盲點。在監督管理模式層面,應當從內部構成與外部協調兩方面著手,修正無居民海島集中管理制度,通過協調執法機制對無居海島環境資源施行系統治理,增加治理協調度和協同效應。在應對由政府主導的單向性治理模式所引發的問題時,應對推動無居民海島生態治理的動力內生化,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的主觀能動性,將生態治理與無居民海島治理的其他方面有機結合,借鑒PPP模式激發社會治理活力,實現多元主體的合作共治,綜合管理和有序安排無居民海島環境資源開發和空間利用的布局、比重和次序,以治理效能發揮制度優勢,構建一個穩定有序、合乎法治邏輯的無居民海島治理體系,以源頭治理、系統治理及綜合施策推動無居民海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1]王斌,楊振姣.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管理理論與實踐分析[J].太平洋學報,2018,26(6).
[2]WALCK C,STRONG K.Using Aldo Leopolds land ethic to read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Case of the Keweenaw Forest[J].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2001,14(3):261-289.
[3]WALKER B,HOLLING C S,CARPENTER S R,et al.Resilience,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Ecology and Society,2004,9(2):2.
[4]KAUFMANN M R,GRAHAM R T,BOYCE JR D A,et al.An ecological basis for ecosystem management[R].Fort Collins:USDA Forest Service,1994:14.
[5]WOODLEY S.Monitoring and measuring ecosystem integrity in Canadian national parks[M]//WOODLEY S,KAY J,FRANCIS G.Ecological Integrity and th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s.Florida:St. Lucie Press,1993:155-176.
[6]魏鈺,雷光春.從生物群落到生態系統綜合保護:國家公園生態系統完整性保護的理論演變[J].自然資源學報,2019,34(9).
[7]田其云.海洋生態系統法律保護研究[J].河北法學,2005,23(1):27-28.
[8]GARDNER T.Monitoring forest biodiversity:improving conservation through ecologically responsible management[M].New York:Routledge,2012:20.
[9]黃寶榮,歐陽志云,鄭華,等.生態系統完整性內涵及評價方法研究綜述[J].應用生態學報,2006,17(11):2196.
[10]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Engineering within ecological constraints[M].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96:97.
[11]呂忠梅.論環境物權[M]//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人大法律評論》編輯委員會.人大法律評論(2001年卷第一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12]陳泉生.論科學發展觀與法律的生態化[J].法學雜志,2005,26(5):81.
[13]李志文,馬金星.我國海域物權生態化新探——理念、實踐和進路[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66(2):71.
[14]張璐.環境法與生態化民法典的協同[J].現代法學,2021,43(2):174.
[15]MLLERA F,HOFFMANN-KROLL R,WIGGERING H.Indicating ecosystem integrity—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J].Ecological Modelling,2000,130(1):13-23.
[16]DE GRAAF K J,PLATJOUW F M,TOLSMA H D.The future Dutch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ct in light of the ecosystem approach[J].Ecosystem Services,2018,29:306-307.
[17]王繼恒.法律生態化及其矛盾辨思[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0(4):153.
[18]FLUKER S.Ecological integrity in Canadas national parks:the false promise of the law[J].Windsor Review of Legal and Social Issues,2010,29:89,112.
[19]Government of Canada.Oceans Act (S.C. 1996,c. 31)[EB/OL].(2019-07-30)[2021-03-15].https://laws-lois.justice.gc.ca/PDF/O-2.4.pdf.
[20]MACARTHUR R H,WILSON E O.The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3.
[21]劉超,崔旺來,朱正濤,等.海島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技術方法[J].生態學報,2018,38(23):8565.
[22]LAWFORD R,BOGARDI J,MARX S,et al.Basin perspectives on the water-energy-food security nexus[J].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2013,5(6):607-616.
[23]馬得懿.美國無居民海島集中管理機制及中國的選擇[J].財經問題研究,2013(9):118.
[24]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Water and the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 Order made on 5 December 2019 with effect from 1 February 2020[EB/OL].(2019-12-05)[2021-03-26].https://www.pmc.gov.au/resource-centre/government/aao-made-5-december-2019-effect-1-february-2020.
[25]Environment Canada.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acts and regulations[EB/OL].(2019-08-02)[2021-02-23].https://www.canada.ca/en/environment-climate-change/services/environmental-enforcement/acts-regulations.html.
[26]齊連明,李曉科.國內外海島保護與利用政策比較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19.
[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4.
[28]顏運秋.論法律中的公共利益[J].政法論叢,2004(5):74.
[29]徐祥民,李海清,李懋寧.生態保護優先:制定海島法應貫徹的基本原則[J].海洋開發與管理,2006,23(2):66.
[30]晏智杰.自然資源價值芻議[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1(6):70-77.
[31]裴洪輝.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科學立法原則的法理基礎[J].政治與法律,2018(10):57-70.
[32]李林.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21,43(1):1-9.
[33]蔡立輝,龔鳴.整體政府:分割模式的一場管理革命[J].學術研究,2010(5):34.
[34]ARDIANSYAH F, MARTHEN A A,AMALIA N.Forest and land-use governance in a decentralized Indonesia:a legal and policy review[M].Bogor:CIFOR,2015:13-18.
[35]海洋和海洋法:秘書長的報告[EB/OL].(2018-09-05)[2021-03-29].https://undocs.org/zh/A/73/368.
[36]馬驤聰.論我國環境資源法體系及健全環境資源立法[J].現代法學,2002,24(3):61.
[37]韓立新,陳羽喬.海洋生態環境損害國家索賠主體的對接與完善——以《海洋環境保護法》修改為契機[J].中國海商法研究,2019,30(3):3-5.
[38]楊璇,王君策.國家海洋局聯合沿海有關省、自治區海洋廳(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我國第一批開發利用無居民海島名錄[N].中國海洋報,2011-04-15(1).
[39]《中國海島志》編纂委員會.中國海島志(遼寧卷第一冊)[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338.
[40]中國將實施十項重點工程解決海島開發保護問題[EB/OL].(2012-04-19)[2021-03-09].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4-19/3832312.shtml.
[41]楊洪剛.我國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政策工具研究[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23.
[42]呂忠梅,竇海陽.修復生態環境責任的實證解析[J].法學研究,2017,39(3):130-135.
[43]蘇大鵬,汪莉.遼寧長海:精心呵護海洋牧場[N].經濟日報,2020-08-29(6).
[44]郭武,黨惠娟.從理念到立法:綜合生態系統管理與綜合立法模式[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3):43-44.
[45]王小鋼.論濕地保護綜合立法及其主要內容[J].林業調查規劃,2005,30(6):69.
[46]秦天寶,虞楚簫.基因隱私的法律保護限度[J].江西社會科學,2015,35(9):136-142.
[47]錢大軍.當代中國法律體系構建模式之探究[J].法商研究,2015,32(2):10.
[48]范如國.復雜網絡結構范型下的社會治理協同創新[J].中國社會科學,2014(4):98.
收稿日期:2021-05-04
基金項目:202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國際組織在國際海洋法律秩序演進中的功能研究”(20CFX087)
作者簡介:馬金星(1986-),男,天津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海洋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員,E-mail:majinxing@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