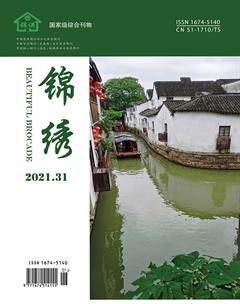一位老藝術家筆下的“行業戲”
牟家明老師已過世多年了,生前他曾生過一場大病,做過兩次手術,因為身體的原因,他依依不舍的暫時放下了手中的筆,但他對戲劇創作的深厚情感,卻仍然溢于言表。與他一起工作過的幾位同事經常談起牟老師,當年寫“行業戲”為什么會搶手這樣一個話題,我不會寫戲,但我知道,寫戲搶手,關鍵是產銷對路,這本來是個簡單的道理,然而卻被許多劇作家忽視了。
有一次搞創作的幾位老師和牟老師談論起這個問題,牟老師很有激情地扳著指頭說,如果從1958年“大躍進”中他寫第一個小戲算起,已有40多年的寫戲歷史了,寫了40多年的戲,不說字字都是血,卻也早早熬白了頭,單是那說不盡的酸甜苦辣,圈外人就根本無法體味,用他自己的話說,40多年的寫戲生涯中既有過“山重水復疑無路”,又有過“柳暗花明又一村”。
所謂“山重水復疑無路”,是指他在進入上世紀80年代之后,正值創作旺盛期的一段時間內,每年大戲小戲雖能寫上幾個,稿紙用上一大摞,自我感覺也很好,可真正成功的卻了了無幾。一年忙活到頭,發劇本的專業刊物能光顧一次就算不錯了。牟家明三個字能變成鉛字,讓戲劇界的老伙計們知道老牟還“賊心不死”,也算沒白忙活了一年。其余多數的本子都像受冷落的后宮佳麗一樣鎖進抽屜束之高閣了。眼看心血白白浪費,牟老師當然心疼當然于心不忍,就揣著劇本鼓足勇氣去找劇團,劇團的頭頭們漫不經心地翻翻本子,客氣地說聲上演的事等研究研究再說,就再無下文了,作為一個寫戲的,還有什么能比這樣的情況更苦惱呢?牟老師曾經多次說過,就是他愛人癱瘓在床、家無隔夜糧的時候,就是他一個月40塊錢50塊錢的工資苦苦支撐著一家大小五口人的生活的時候,似乎也沒有這樣苦惱過。往后的路該怎么走呢?寫戲這行當還要不要堅持下去呢?成天縈繞于心的就是這樣一個折磨人的問題,想金盆洗手,但又像害單相思走火入魔的情種,欲罷不能,再寫下去,前景卻又渺茫。
說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牟老師激動之情溢于言表,說這是原先根本沒有預料到的事情。上世紀80年代末,安丘劇團的團長竟主動登門請他去給團里寫個計劃生育題材的大戲,并說縣里的領導和計劃生育部門的同志如何重視云云。起先牟老師并不以為然,覺得自己這樣的老劇作家去配合中心工作寫宣傳戲,有點掉架,可他架不住人家誠心誠意再三相邀,覺得人家好不容易從縣里爭取到資金,縣里還在演出場次安排上予以支持,這樣的機會實是難得,于是最后就答應了。牟老師這人就這樣,應下人家了,就不能應付了事,寫就寫出個樣子來。于是,就走鄉串村深入生活,把自己對計劃生育問題的所思所想和全部的生活積累都投入了進去,沒想到,一出《盼兒記》居然一炮打響,用牟老師的話說是“三個沒想到”。
一是沒想到各級領導對這臺戲如此重視。安丘為抓好這臺戲的演出,當時的縣委、縣政府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由分管的副書記任組長,吸收宣傳、文化、計生、保險等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把《盼兒記》演出場次落實到每個鄉鎮,排演的資金由縣里安排解決。戲彩排時,縣五大班子的領導全部到場觀看演出,劇團下鄉演出時,各鄉鎮領導都是親自安排接待,省、市開計劃生育會都調演了這臺戲,濰坊市人民政府破例為牟老師記功頒獎。
二是沒想到這出戲的演出效果那樣好。《盼兒記》由安丘縣劇團首演后,濰坊市和濱州地區就有7個專業劇團相繼上演過千場,高密茂腔劇團帶《盼兒記》進京演出,受到文化部、國家計生委的領導和首都戲劇界專家們的好評,省文化廳為這臺戲頒發了“百場獎”,由這臺戲改編的電影《女人也是人》由廣西電影制片廠拍攝,并榮獲首屆山東電影節一等獎、上海第二屆農村題材影片優秀獎、廣西省人民政府文藝創作銅鼓獎。濰坊市的四個專業劇團在農村演出這臺戲時,無論是在影劇院還是搭“野臺子”,都是場場爆滿,盛況空前,當地領導出面安排只是一個外在因素,主要是農民群眾愛看這臺戲,有不少農民朋友一連跟著劇團看三四場還覺不過癮。
三是沒想到這臺戲會給上演的劇團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當時絕大多數地縣級劇團受種種客觀因素的制約,演出不景氣,在經濟上陷入尷尬的境地,而一臺《盼兒記》安丘劇團一連上演200余場,純收入十幾萬元,當時的十幾萬元是個什么概念?那可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一下子就使劇團起死回生。濰坊市的四個專業劇團爭相上演這出戲,也都是看準了《盼兒記》有“利”可圖,效益可觀。
“市場經濟”這個東西最是鐵面無情。
由“三個沒想到”,牟老師終于悟到了文章開頭說過的那個極為簡單的道理:寫戲要搶手,關鍵是產銷對路。自此,牟老師才徹底轉變了觀念,調整了視覺,由過去兩眼盯在發劇本的刊物上,轉為盯在劇團的需求上,從此他一發而不可收,繼《盼兒記》之后,十幾年中連續又寫了8個大戲,一個中型戲, 都由專業劇團搬上舞臺演出。當然,牟老師在寫“行業戲”之余,也從沒停止對戲劇藝術高品位的思考,他退休之后,通過深入生活有感而發,寫出了以反腐為題材的大戲《碧水長流》,先是晉京演出,之后又被評為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填補了我市在這個獎項上的空白,牟老師也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嘉獎。總之,用牟老師的話說,他沒想到寫“行業戲”會寫出這么好的效果,這確實是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過去他是為寫出劇本沒有劇團愿意演而苦惱,而后是為劇團爭相登門求寫戲,自己不能滿足人家的要求而苦惱。
牟老師寫“行業戲”搶手這一現象,至今可對地、縣的基層劇作者有兩個方面的啟示:
一是劇作者必須把著眼點單一的眼睛向上變為眼睛既向上也向下而且主要是向下,牢牢立足于為基層劇團寫戲。只有把著眼點轉過來,劇作者才能走出困惑,才能走出困境。縱觀當今劇壇,不難發現這樣一種怪現象,全國發表戲劇劇本的專業刊物少得可憐,可是劇作者們卻過分偏執地死死瞄準刊物,一窩蜂地往這條本已十分擁擠的小路上擠,美其名曰搞“藝術精品”。極少數作者好不容易發個本子,也就是僅僅變成鉛字而已,刊物發表的本子,劇團能夠看好搬上舞臺的了了無幾。就是那些在專家圈子里叫了好或是在什么評獎中中了彩的,劇團也照樣不買賬,因為基層劇團自有基層劇團的標準,劇團認定的標準加不得任何水分,還有的劇作者過分癡情地脫離實際搞什么“藝術精品”,最后也只是事與愿違。事實上,有好多劇本從變成鉛字那天起,有的甚至還沒有變成鉛字,藝術生命也就基本壽終正寢了,長此以往,劇作家的創作積極性必然大受挫傷,就只能重新考慮出路問題,“賊心已死”的索性與戲劇斷交,“賊心不死”的便從現實出發,轉向寫“商品報告文學”,寫廠家贊助的電視劇等等,不圖有名,只圖囊中不再羞澀。這就難怪寫戲的隊伍越來越小,至今能苦苦堅守陣地的不外乎那幫老面孔中的少數人,新作者新面孔簡直寥若晨星,青黃不接已是劇作家隊伍急待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劇作家認真從自身檢查一下,就不能不承認我們創作的出發點確實發生了錯位,劇本首先是為演出而寫,發表只是擴大其影響的中間環節,而不是終極目的,現在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是,一方面劇本園地期期有劇作,一方面,劇團大喊大叫無劇目演出。牟老師寫“行業戲”曾經產生的搶手現象說明,地、縣基層的劇作家們只有眼睛向下,放下架子,從追求見鉛字搞“精品”的迷途中走出來,老老實實為基層劇團寫戲,前景才會光明。
二是劇作家應該盡快從我想為劇團寫什么改變為根據劇團需求寫什么,從正確的供求關系上保證劇本的成活率和提高“兩個效益”。事實證明,地、縣基層的劇作家在實現了立足點的轉變之后,應該盡快解決的就是如何根據劇團需求寫劇本的問題,有些劇作家也不是不愿為劇團寫,但是總認為自己比劇團高明,“我寫的本子你應該演,否則就是對作者的勞動不尊重”,就是“曲高和寡”。而我們卻沒有看到,在劇本的選擇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是常年在基層頂風冒雨為群眾演出的劇團,他們最知道廣大觀眾需求什么樣的劇目,他們對劇本的需求實際上就是農村、廠企舞臺和基層觀眾的需求。現在,自上而下各級文化藝術主管部門都提倡文藝與企商聯姻,文藝與其它行業聯姻,我們的劇團為什么不能根據各個行業的需求,積極主動地與他們聯姻呢?這樣既活躍了舞臺演出,又宣傳了某個行業,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劇團演出收入,解決了經濟困境,又何樂而不為呢?我們的劇作家只要認識了這一點,就不會覺得為劇團寫“行業戲”而覺得“掉價”了。事實上,寫“行業戲”還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我們的劇作家不應該被動型地參與這個精神產品生產領域,而應該積極主動地參與進去,認真調查研究,盡快熟悉你所不熟悉的行業生活,只要從藝術規律出發,只要從人物出發,只要從鮮活的生活出發,就一定能寫出傳世的好戲來。像《白毛女》、《李二嫂改嫁》、《劉巧兒》、《朝陽溝》等,在當時不都是“宣傳戲”、“行業戲”嗎?誰又能否認它們是能夠載入戲劇史冊的上乘藝術品呢?問題不在于寫什么,而在于怎么寫。反之,當你一心想搞什么“藝術精品”的時候,反而出不了精品,而搞出的僅僅是“滯銷積壓品”。
這個問題應該引起劇作家們的注意和深思,也希望能引起爭鳴和討論。
作者簡介:孫玲(1966.03-),女,漢族,山東濰坊人,本科,齊魯文化(濰坊)生態保護區服務中心文藝培訓部主任、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群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