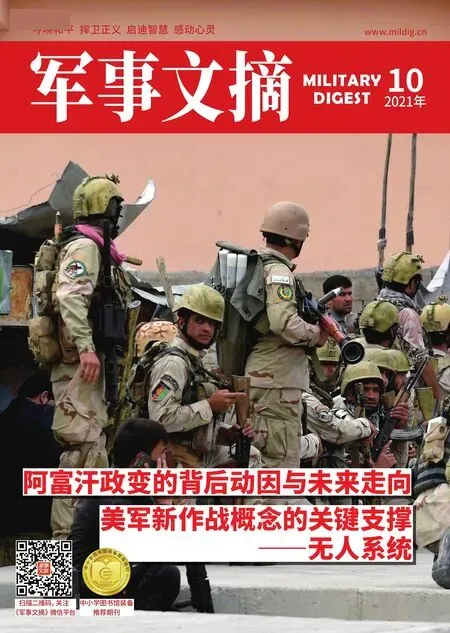巴以沖突又起,各方勝負如何
丁 工

2021年8月22日,以色列國防軍出動戰機空襲了加沙地帶哈馬斯的多處軍事目標,以方表示空襲是對日前加沙地帶武裝人員射傷以軍士兵事件的回應。近日,以軍先后多次對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的武器制造和儲存基地進行打擊,使巴以局勢在歷經短暫的總體緩和后有再度升級的風險。2021年5月10日起,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加沙地帶武裝曾爆發嚴重沖突,持續11天的沖突導致數千名平民傷亡,將巴以緊張局勢推向一個新的高點。5月21日,在埃及的斡旋下,沖突雙方達成停火,但隨后巴以之間的零星交火依然不斷并延續至今。
此輪沖突是自2014年7月以色列對加沙地區武裝實施“護刃行動”以來,巴以之間最大規模的武裝交火。巴以之間在齋月前后爆發激烈沖突已經“常態化”,雖然雙邊摩擦不斷,但基本上能夠保持適度理性和克制,盡可能地避免局勢失控。然而與以往相比,本次沖突雙方攻勢之凌厲、戰況之慘烈卻有些出乎外界預料,這其中所暗含的玄機和折射出的變化引發了國際社會嚴重關切。
巴以爭端因何再起波瀾
事實上,本輪巴以沖突的起因并無“新意”,但后續進程卻呈現了一些有別于慣例之處。這是由于巴以面臨的內外環境都已發生重大變化,再加上兩國分別處于臨近大選和正在組閣的關鍵節點,沖突兩派各懷心思、各有盤算,迫使雙方都需要在沖突中有所“斬獲”,從而為己方贏得更多的博弈砝碼,導致巴以緊張局勢再次處于歷史高位。

以色列鐵穹導彈攔截哈馬斯火箭彈
一方面,以哈馬斯為首的加沙地區武裝派別需要通過對以色列強硬發聲,來標示存在的合法性和對巴以局勢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防止出現在巴以事務上發言權被邊緣化的狀況。同時,哈馬斯還可以通過展示對以斗爭來轉移內部視線、博取各方同情,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即將舉行15年來的首次大選聚攏人氣選票和積攢政治資本。由于中東地區局勢變化,哈馬斯獲得的外部“輸血”有所減少,加上國際活動空間的顯著萎縮,使其對巴以局勢和巴內部政局的影響都趨于下降。哈馬斯此時展示一貫堅定的反以立場,為因美國偏袒政策而憋屈許久的巴勒斯坦百姓出口“惡氣”,擺出為民“請命”的姿態,將進一步強化其代表全體巴勒斯坦人民的形象,自然會給哈馬斯在未來巴勒斯坦大選中加分,也有利于其與以色列的交鋒以及與巴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的內部權力博弈中掌握主動,從而鞏固和強化哈馬斯在巴以問題上的發言權。另外,哈馬斯對以色列顯示強硬,還能夠贏得伊朗和土耳其兩個中東地區大國的積極支持。沖突發生后,伊土兩國紛紛第一時間表態強烈譴責以色列的暴行,伊朗不但暗中加大對哈馬斯的軍事裝備支援,并聯絡黎巴嫩、敘利亞的盟友趁亂襲擊以色列,使其陷入兩面作戰的處境以策應哈馬斯作戰。土耳其則積極為加沙人道主義救援物資和普通日用品的禁運“解圍”而努力,其外長甚至呼吁組建一支“國際保護部隊”,進駐加沙地帶保護巴勒斯坦平民。
另一方面,自敘利亞內戰后,以色列將戰略精力置于北部方向,以打擊伊朗在敘利亞不斷增強的軍事存在為主要目標,對南邊巴勒斯坦方向沒有投入過多關注。并且,以色列先后部署鐵穹、箭式-3、大衛彈弓和愛國者等多個反導攔截系統,建立起高、中、低搭配的多層警戒設施和綜合防御體系,具備在不同高度和范圍內攔截來襲攻擊目標的能力,進而認為哈馬斯武裝火箭彈襲擊的威脅已經大幅降低。再加上2014年7月“防務之刃”軍事行動又給予哈馬斯以重擊,短期內無法恢復元氣,導致以色列低估哈馬斯的既戰能力。從實戰情況看,本次沖突中加沙地帶武裝向以色列發射了1000多枚火箭彈,其中90%被以色列防御系統成功攔截,但仍有為數不少的火箭彈“漏網”,造成以方至少8人死亡、100多人受傷,這讓以色列意識到需要再對哈馬斯進行一次深度打擊。如今既然戰事已開,以軍索性甩開膀子大干一場。沖突一起,多名哈馬斯負責網絡、情報、安全和火箭工程的高級指揮官便被以色列“一鍋端”了。
此外,美國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時期,在巴以問題、中東地區政策上顯露出許多對以色列不利的征兆。拜登就任總統后,很快便與多個盟國領導人通過電話,提出美國要修復因特朗普在任時與盟國破損的關系。但拜登卻遲遲不同中東盟友聯系,直到上任近4周后才完成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首次通話,還曾批評以色列定居點政策,又揚言要重返伊朗核協議,美國新政府對巴以問題的反應冷淡,無疑令以色列既感到不滿、又產生不安。因此,以色列此番對哈馬斯大打出手,也有施壓美國重新審視對以政策的成分。同時,倘若臨選前夕任期將屆滿的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組閣失敗,將給其競爭對手“擁有未來”黨領導人拉皮德提供了問鼎總理寶座的機會。但巴以沖突的爆發,有可能使部分主張強硬路線的勢力放棄同拉皮德合作,為內塔尼亞胡執政之路帶來轉機。
不難看出,巴以局勢之所以再起波瀾,不僅是歷史與現實、偶然與必然等多種因素相互影響、疊加作用的產物,歸根結底更是美國政府長期偏袒以色列制造的不良后果。尤其是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在搬遷駐以使館至耶路撒冷,關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停止資助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機構以及猶太人擴建定居點等問題上,罔顧巴勒斯坦人民利益,完全站在以色列立場上,極大地激起巴方民眾的憤怒情緒。正是美國“欺壓”巴方的做法,讓巴方感到失落甚至絕望,誘使巴方民眾不滿情緒在敏感場所和時點的宣泄,成為“引爆”巴以爭端再起的導火索和助燃劑。
相關各方得失幾何
綜合來看,本輪沖突呈現出哈馬斯、土耳其和伊朗是得利一方,以色列、美國相對失利,埃及、俄羅斯平局的狀況。
哈馬斯、伊朗和土耳其是贏家。哈馬斯自誕生之日就明確反對巴以締結和平協議,主張同以色列進行頑強戰斗,直至從物理上將其消滅才肯收手。因此,主戰派哈馬斯不僅成為以色列的“眼中釘、肉中刺”,也與主和派法塔赫形成亦敵亦友的微妙關系。短期來看,哈馬斯在經歷近半個多月的戰斗后損失慘重,較長一段時間內都將處于以休養生息為主的戰略蟄伏期。但從長遠考量,作為巴勒斯坦內部兩大主流政治派別,哈馬斯在保衛民族權益和抗以侵略斗爭中花樣翻新、新招跌出,同法塔赫瞻前顧后、患得患失的表現形成鮮明反差。再說,戰火重啟對于歷來在巴以問題上秉持武裝斗爭路線的哈馬斯,本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勝利。因此,哈馬斯適時采取以退為進、見好就收的策略,再度提升自身在巴以議題和巴勒斯坦內部權力分配上的存在感和話語權,自然屬于本次沖突的獲利方。

哈馬斯自誕生之日就主張同以色列進行頑強戰斗
伊土兩國也是巴以問題的重要涉事方,此次沖突進一步強化伊土兩國在巴以爭端中扮演的不可或缺角色。其實,哈馬斯被排斥于巴以和平進程之外正是伊朗所希望看到的,也是什葉派伊朗支持遜尼派哈馬斯的深層緣由。伊朗將什葉派黎巴嫩真主黨和遜尼派巴勒斯坦哈馬斯打造成其在巴以問題上的“左膀右臂”,對以色列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配合敘利亞鉗制,使其難以抽身,不僅能夠插手巴以和談,甚至在一定意義上左右中東和平進程。伊朗通過對以色列強硬介入巴以沖突,是為阿以爭端打入楔子借以制阿,從而使美國、以色列和沙特在同伊朗的斗法對位中落處下風。阿以雙方陷入持久沖突而不能自拔,無力應對伊朗的勢力擴大是對伊朗戰略境遇最有利的時期。
以色列一直是土耳其打壓敘利亞的一枚重要棋子,“借以制敘”向來是土耳其的基本方針。冷戰時代,土耳其和以色列作為美國“哼哈二將”,建立起南北夾擊敘利亞的合縱陣線,與伊朗和敘利亞連橫集團形成對峙之勢,兩國關系一度達到“準盟友”的級別。在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關系開始“遇冷”,甚至近乎兵戎相見。事實上,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間既無遺留宿怨也無深仇大恨,土耳其對以色列顯示強硬,不惜以“犧牲”土以關系為代價替巴勒斯坦“出頭”的主要目的,既有通過“打臉”以色列來達到報復其“幕后老板”美國的戰略考量,也有顧及國內風向、爭取民意選票,樹立穆斯林民眾“衛道士”形象的現實考慮。一方面,土以關系雖然是一組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雙邊外交關系,但某種程度上土以關系是依附或者說是從屬于土、美、以三邊關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美國一直都在極力推動土以兩國建立友好合作關系,無論是當年土耳其與以色列結成互幫互助、有實無名的軍事盟友,還是2016年12月土以解決馬爾馬拉號救援船事件的羈絆后重新恢復外交關系,其間一系列的調度和運作無不飽含著美國的“辛勞”。但自2016年7月土耳其發生未遂“兵變”起,土美關系便進入到深度“冰凍”期,兩國因對待庫爾德武裝、F35戰機生產技術合作、引渡居倫受審和購買俄軍S400防御系統等事宜口角不斷、矛盾日深。另一方面,哈馬斯前身是“穆兄會”國際機構的地區分部,與土耳其執政的正發黨兩者可謂“同根同源”,意識形態的親近感使土耳其對于哈馬斯上臺執政較為寬容。土耳其認為應當面對哈馬斯執政這樣一個現實,孤立哈馬斯的政策只會導致巴勒斯坦問題更加激進。2006年,土耳其政府頂住西方壓力,邀請孤立中的哈馬斯領導人訪土。可見,土耳其對哈馬斯出手相助是處于多重考慮,也在此次沖突中獲利頗豐。
以色利贏得戰術、輸掉戰略。2020年9月11日,美國、以色列和巴林發表聯合聲明宣稱,以色列與巴林已經同意建立全面外交關系。這是即8月13日阿聯酋與以色列實現全面關系正常化之后,短時間內又一個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阿拉伯國家。這就意味著,21個阿拉伯國家聯盟中已經有4個成員國,與以色列全面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其后,2020年12月以色列和摩洛哥又同意實現關系正常化,雙方政府首腦還就建交準備工作進行了電話溝通。2021年稍早前,以色列駐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聯絡處和駐阿聯酋城市迪拜的總領館也正式開放,標志著阿以和解問題迎來重要“窗口期”。然而,在此之時以色列再次同加沙武裝爆發激烈沖突,無疑會對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產生不利影響。
再說自拜登政府上臺以來,中東地區出現美伊矛盾緩和、敘利亞政府坐穩位置、沙特與伊朗就也門戰爭談判等對以色列不利的形勢,以色列希望借助戰事讓美國重新進入并肩作戰的狀態。但現實卻是,拜登政府正努力把美國在中東事務的參與度降到最低,依然沒有因為巴以戰端重啟而有所改變的意思。因此,以色列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不錯戰績,限制了哈馬斯武裝力量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但其總體預期的目標意圖均未能實現,因而在本次沖突中所失大于所得。除此之外,俄羅斯、埃及等國也是重要相關方,但他們同沖突兩方都保持著緊密聯系,不存在“選邊站隊”的問題,故而在本次沖突有得有失、總體平局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