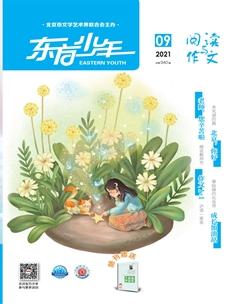滬語(yǔ)一家親
王嘉怡


名師點(diǎn)評(píng)團(tuán)
牛越,北京市第十五中學(xué)語(yǔ)文教師。古代文學(xué)碩士。多次承擔(dān)國(guó)家級(jí)、市級(jí)、區(qū)級(jí)示范課,疫情期間承擔(dān)區(qū)“空中課堂”的錄制工作。其研發(fā)的校本課程《古風(fēng)雅韻》等受到學(xué)生的廣泛喜愛(ài)。指導(dǎo)學(xué)生在“全國(guó)青少年誦讀大賽”中榮獲特等獎(jiǎng),個(gè)人獲得“優(yōu)秀輔導(dǎo)教師”稱(chēng)號(hào)。2020年榮獲第四屆“京城榜樣教師”稱(chēng)號(hào)。
“儂姓啥?吾姓黃。啥額黃?草頭黃……”每每這首滬語(yǔ)童謠響起,我的腦海里總會(huì)浮現(xiàn)出全家一起用滬語(yǔ)聊天時(shí)其樂(lè)融融的畫(huà)面……
外婆中學(xué)畢業(yè)響應(yīng)國(guó)家號(hào)召離開(kāi)上海,遠(yuǎn)赴新疆,支援邊疆建設(shè)。雖然離開(kāi)了家鄉(xiāng),但是外婆在新疆與同鄉(xiāng)人依然講著吳儂軟語(yǔ),以至于五十年后回到故鄉(xiāng)上海仍是“鄉(xiāng)音無(wú)改”。
但是,那時(shí)候講上海話(huà),全家永遠(yuǎn)只有外婆一個(gè)人唱“獨(dú)角戲”。
媽媽出生在新疆,中學(xué)時(shí)才回到上海;爸爸是北方人,大學(xué)畢業(yè)后來(lái)滬。所以,他倆都不會(huì)講上海話(huà)。而我雖然出生在上海,但是從小耳邊響起的都是北方話(huà),自然也與上海話(huà)無(wú)緣……
念四年級(jí)時(shí),學(xué)校開(kāi)設(shè)了“滬語(yǔ)童謠”課程。我這個(gè)不會(huì)說(shuō)滬語(yǔ)的上海小囡對(duì)此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剛開(kāi)始我還結(jié)結(jié)巴巴,舌頭不聽(tīng)使喚似的,總是念串音、講錯(cuò)話(huà)。在老師的指導(dǎo)下,我漸漸說(shuō)得順溜了,講起滬語(yǔ)來(lái)也有了那么一點(diǎn)兒地方味道。
富有童趣的滬語(yǔ)童謠念起來(lái)朗朗上口,韻味十足。外婆看著我煞有介事的模樣,聽(tīng)著我甜甜的家鄉(xiāng)口音,立刻眉眼彎彎的,笑得嘴都合不攏了。
外婆終于不用唱“獨(dú)角戲”了。媽媽見(jiàn)狀,也拉著爸爸加入了學(xué)滬語(yǔ)的行列。每當(dāng)晚餐后,一家子圍坐在餐桌前,我就把新學(xué)的滬語(yǔ)童謠念給大家聽(tīng),外婆總會(huì)在旁邊耐心指導(dǎo)。
“鴨子,要念阿——茲。”
“阿——茨。”
“錯(cuò)啦,‘阿的音調(diào)不能用拼音的第三聲。‘阿茨是‘鞋子的意思了!”
媽媽說(shuō)錯(cuò)時(shí),外婆總會(huì)善意地打趣她:“你啊!說(shuō)的還沒(méi)我們佳佳好,可得好好練練嘍!”媽媽撓著頭,尷尬地笑笑,一遍遍跟我請(qǐng)教。爸爸呢,總是在一旁笑而不語(yǔ)。等到媽媽終于講對(duì)時(shí),我們會(huì)噼里啪啦地給她鼓掌。那鄉(xiāng)音,那笑聲,那掌聲,聲聲入耳。
現(xiàn)在每天晚上,全家人仍會(huì)圍坐在桌前,談笑風(fēng)生,不過(guò)用的都是上海話(huà)。這不僅是外婆最幸福的時(shí)刻,還是全家最歡樂(lè)的時(shí)光!
也許滬語(yǔ)在有些人眼里老土、落伍,但這一句句吳儂軟語(yǔ)中包含的是我們上海人最淳樸、最真切的家鄉(xiāng)情感。我堅(jiān)信,這鄉(xiāng)音一定會(huì)傳承下去,一代又一代……
點(diǎn)評(píng)
鄉(xiāng)音對(duì)于每個(gè)人來(lái)講都是永遠(yuǎn)縈繞在心間的牽掛,小作者娓娓道來(lái),不蔓不枝,語(yǔ)言細(xì)膩生動(dòng),質(zhì)樸之中尤見(jiàn)真情。文章中很多細(xì)微之處都很有生活氣息,筆觸柔和、動(dòng)情,把對(duì)家鄉(xiāng)的情愫完整地表達(dá)了出來(lái)。
(牛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