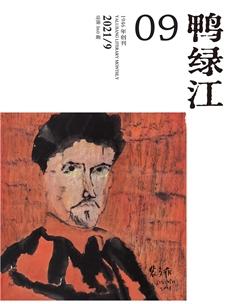焦慮與自我經典化(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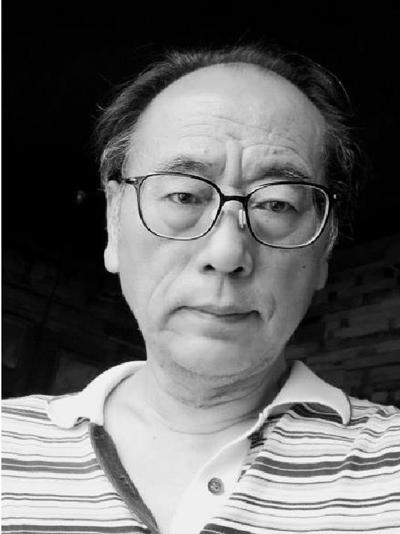
大約是1991年,有位女歌手需要原創歌曲,邀我寫了一首歌詞。第一段的開頭是:
太陽從東向西走,
河水從西向東流。
第二段的開頭:
男孩子有好多路要走,
女孩子有好多淚要流。
她請人譜了曲唱給我聽,我覺得曲子不行,收回了歌詞,后來不再想譜曲的事,再后來只記得幾句。
在很多年里,我沒把自己寫的東西保存下來。一個原因是,我以為我的語言會越來越純潔,思維的銳度會長久保持,可以寫作的歲月還有很多,后面寫出來的東西會更好。
這個原因看起來真實。有些寫作者就是這樣想、這樣做的。他們和我一樣懶散,沒有野心。但這些不是我的第一位原因。同樣是寫作者,我生性軟弱,膽量很小,首要的原因是心中的恐懼,不想保存自己寫的文字。
一部分恐懼來自家庭環境。大學畢業不到十年,我的父母,以及父系母系的長輩親屬,全都離開人世駕鶴西去。我的兩位兄長也病逝了,平均壽命四十五歲。那種家族式的短壽讓我驚訝和焦慮,那個陰影很大,很重,很噪,籠罩我的頭頂。幾十年后寫這段文字,我用的詞語是“那種”和“那個”,但在當時,卻是“這種”和“這個”,是距離感很近的詞語。與別人不同,我是個怕死的人,十九歲時一個人坐著,想到死亡淚水直流。從小時候開始,隔個一年兩年,我就會做我被兇殺、被謀殺、被追殺的夢,還有一次是被上個朝代判了死刑,我站在距行刑隊三棵樹遠的地方,看行刑者用內戰時的老步槍瞄準,我中彈后倒在淺水里,后來慢吞吞地爬出去了。在我當時的夢里,死罪是一槍之罪,一槍打不死的讓他逃走。逃走以后我就醒了。生命有涯,在世難久。世界上確實有敬畏生命因此發憤的作家,也有恐懼死亡而回避寫作的作家。由于自身原因,我在兩者之間游蕩如鐘擺,游蕩幅度太大,自己也覺得異常。在寫作上,我害怕用力拔高自己,揠苗助長,危及健康和壽命。有一位波蘭精神分析學家說,一個不成熟者的標志是,愿意為某個事物轟轟烈烈死去,而成熟的人,愿意為它謙卑地活著。
另一部分恐懼來自周遭環境。我不想在出版的限度里寫自己喜歡的事物,我不愿意聽命于人,那會留下自己的盲點、壓抑以及想象和思想的失敗。我在一個市級作家協會工作的七八年,是真正離開寫作的日子,只寫些領薪水的文字,后來我去一個電視臺工作,領多一些的薪水。
現在的問題是,人們有選擇地回憶20世紀80年代的寫作盛世,卻永遠忘了寫詩抑郁至死的海子,也根本不記得有作家罷筆的事情。那么,寫作者的焦慮是怎么回事呢?寫作的時候焦慮,罷筆的時候焦慮,然則何時而不焦慮耶?
怎樣都是焦慮?
怎樣都是焦慮。
怎樣都是焦慮,那就寫作吧。
要知道,文學最深層次的焦慮是文學性的。有的作家稍好一些。他們把文學寫作擺在宗教信仰的高度,未必能減少焦慮,可是焦慮的性質變了,它的代價是值得呈獻的,它變得理所當然,并不可怕,無須回避。林語堂說詩歌是中國人的宗教,馬悅然說詩歌是中國人的信仰。在這里,他們說的中國人包含了作家和讀者,情況復雜。塞林格有個說法是專門說給作家的,他說,寫作什么時候成了你的職業了?寫作一直是你的宗教。
文學寫作與宗教信仰相似,是我很少考慮的事情。我一直覺得,這對于我自然而然,現在也沒有想好怎樣表述。
在很久很久以前,文學寫作是首先出現的,有一部分神性文字被叫作宗教經典,其他的神性文字以及數量漸多的俗性文字,叫文學作品。從我站立的視角看過去,人們認可的宗教信仰,有的是政教合一不是宗教,有的是宗教卻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比我讀書更多,對各宗教的了解更多,可能會從中看到相同相異,看到精華所在,重新組合。你可能覺得你的文學寫作,可以關注同樣的事物,可以完成同樣的探索,可以有個更好的結果。這就像哲學系畢業的作家揚·馬特爾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寫了十六歲的派同時相信印度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幫助了他在海難時警覺、逃離、存活,可是,當他向蒼天怒吼時,個人生命與超自然力的對話,又成了另一種宗教信仰的力量,更加開放。
如果原有的各宗教不再發展,成了閉環,作家們需要一個開放的精神領域,需要一種四下彌漫又不可限制的精神,需要一些脫離固定的解釋和重新對話的自由。作家們在寫作中面對永生,妄圖得到生命的不朽。這不是奢望般的夢想,而是恐懼的派生物。因為對生命盡頭的恐懼,作家們要借助作品留下不朽的名聲,于是,這種恐懼在文學藝術中會轉化成對經典性的企求。作家們是一些知道天命的人。天命就是你一直期望去做的事,這些愿望來自宇宙的靈魂,那就是你在世間的使命。
現在,我們這樣想也這樣做了,我們需要的自我經典化的過程已經完成了一半。
假如我們有認知的敏銳——穿越一大堆偽經典抵達真正的經典,有語言的活力——是純凈和具有深度的活力,有創造的才情——能寫出自成一派的東西,并且再進一步說,我們還有必需的生存條件,有優越的心理承受力,有合適的身體狀態,那么,我們就會充滿跳躍的能量,把剩下的一半繼續完成。在這里,選擇是重要的,選擇什么是值得焦慮的,這個選擇決定了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到哪里去。當我們判斷自己下一部作品的構思,能夠達到卡爾維諾說的十多個文學經典標準中的半數,或者達到《西方正典》那部著作分析的莎士比亞所在的文學經典的核心位置,或者像某位學者說的,達到作品的權威性、普適性、示范意義、共識標準,給人類的生活、生命、生存帶來新的焦慮和啟發,那么基本上可以認為,我們的下一部作品就有成為文學經典的大概率。
看起來這值得一試。
【小檔案】
董學仁,1955年3月15日出生于鞍山,父親是修鞋匠人,當時開了一個修鞋鋪。幼年的一些經歷,對他的人生觀和文學寫作產生了比較深的影響。
1972年,他從中學畢業,兩年里沒有工作,跟電影院美工老師學水粉畫,此后當過火車裝卸工、采購員、廠辦干事、軋鐵板工人。
1977年底,中斷了十年左右的高考招生制度恢復,他考美術學院沒被錄取。到山野之間寫生增加了他對自然和美的感知力,那幾年他還意外地讀了好多書,因為一家廢品收購站允許他翻找站里隨時收購到的舊書,這讓他讀到了市面上見不到的外國文學、哲學等各種書籍。
1979年,考上遼寧師范學院(后改為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1981年開始詩歌、散文、小說寫作,擔任校園文學雜志《新葉》的編輯。
1982年底,他與劉興雨、林雪共同編印了《新葉》詩專號,并發表了徐敬亞長篇詩論《崛起的詩群》,以及北島、顧城、梁小斌、王家新等一批詩人的組詩與長詩,為這份刊物制造了在國內外的影響。
1983年畢業回到鞍山,在一家職業高中任教。1988年到當地作家協會工作,1995年去當地電視臺工作直到退休,此間曾在大學藝術系開設課程,之后移居北京并任《中國青年作家報》特邀編輯。
自2008年1月開始,《西湖》文學雜志連載董學仁的長篇系列散文《自傳與公傳》。至2017年10月停止,連載了九年十個月,五百篇左右,大約一百五十萬字,這在文學雜志的連載歷史上算是一個奇跡。
《西湖》主編吳玄在《光明日報》上推薦《自傳與公傳》時曾說:“在一個文本內,董學仁為一個人和整個世界同時立傳,自傳是細致的,公傳是廣博的,在此,個體變大了,世界則變小了,充滿了生命感。董學仁消解了個人敘事和宏大敘事之間的壁壘,很可能創造了散文寫作的一個新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