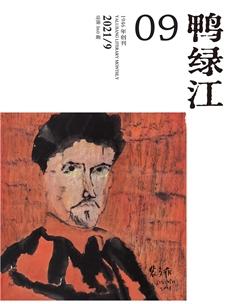用某種方式說(shuō)出這些事情(評(píng)論)
2020年歲末的一天,刁斗兄突然加我微信。通過(guò)之后,他就連發(fā)幾條語(yǔ)音,核心意思是他將為《鴨綠江》雜志主持一個(gè)欄目,每期推出一個(gè)他覺(jué)得有話可說(shuō)的遼寧作家,想約我寫(xiě)稿。他說(shuō):這個(gè)董學(xué)仁吧,搞的是“一本書(shū)主義”,早就寫(xiě)出了“長(zhǎng)河散文”,卻基本上無(wú)人知曉,但我特別喜歡。然后,他就給我描述了一番他喜歡的理由:你看過(guò)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嗎?看過(guò)卡內(nèi)蒂的“自傳三部曲”和夏多布里昂的《墓后回憶錄》嗎?董學(xué)仁的《自傳與公傳》,就類似于這種書(shū)。
此前,我對(duì)董學(xué)仁一無(wú)所知,沒(méi)讀過(guò)他的任何東西。但刁斗熱情洋溢的一番推薦(我聯(lián)想到了趙本山小品中的“忽悠”),讓我拒絕都不好意思。不過(guò),等他發(fā)來(lái)長(zhǎng)達(dá)百萬(wàn)字的電子版,我還是被嚇住了。寫(xiě)個(gè)幾千字的文章,卻要讀這么多東西?而且我的狀態(tài),一直就是從頭忙到腳,要寫(xiě)的文章排隊(duì)等候,夾塞兒往往比較困難,這可讓我如何是好?但我一跟他訴苦,他就微信道:“明白——但咱,有薩特的面子呀。當(dāng)然你酌情,我不逼你,你體諒我,方歡喜。”
薩特的面子?此話怎講?
這里面有故事。
那是2009年9月,《山西文學(xué)》主編魯順民折騰了一個(gè)筆會(huì)。那天我趕赴太原,與大部隊(duì)會(huì)合并與聶爾同行。到了晉北河曲,方才發(fā)現(xiàn)刁斗也已駕到。聶爾與刁斗早已相熟,我則久聞其大名,卻是第一次相見(jiàn)。三個(gè)月前,發(fā)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把我們?nèi)齻€(gè)拴在了一起。于是一見(jiàn)面,刁斗就鉆進(jìn)我與聶爾的房間,細(xì)細(xì)聊起了前因后果。此前聶爾與我通氣,讓我對(duì)刁斗有了種《紅燈記》里王連舉的印象:叛徒?但聽(tīng)他解釋,詳述原委,我才明白了他當(dāng)時(shí)的處境和具體的事態(tài)。
那天晚上,魯順民把聶爾、刁斗、王童和我拽出去喝茶。茶館是晉北風(fēng)味,我們好像是盤(pán)腿坐在一鋪炕上,服務(wù)員不斷倒茶續(xù)水,我們則在那里神吹海聊。聊到盡興處,不知怎么就說(shuō)起了薩特。我說(shuō)前幾年我對(duì)薩特用過(guò)功,薩特的書(shū),寫(xiě)薩特的書(shū),幾乎一網(wǎng)打盡,尤其是列維那本《薩特的世紀(jì)》,像《存在與虛無(wú)》一樣能當(dāng)秤砣使,但我卻讀得血脈賁張。
聽(tīng)著我講述,刁斗又坐不住了,他說(shuō):“《薩特的世紀(jì)》我讀過(guò),寫(xiě)得真他媽好!趙勇啊,咱們得為這本書(shū)握個(gè)手。”說(shuō)著說(shuō)著,他已從炕那邊蹦跶過(guò)來(lái)。
這廝居然讀過(guò)這本磚頭厚的書(shū)?萬(wàn)里他鄉(xiāng)遇故知!于是我也起身,兩只手握在一起,像是演電影。因?yàn)橐呀?jīng)進(jìn)入劇情,我腦子里立刻蹦出一句臺(tái)詞:“照這么說(shuō),你是許旅長(zhǎng)的人啦?”刁斗反應(yīng)快,立刻朗聲答道:“許旅長(zhǎng)的飼馬副官胡標(biāo)!”把三位觀眾看得哈哈大笑。
想起這個(gè)握手的梗,我說(shuō),啥也別說(shuō)了,等我寫(xiě)完手頭這篇就讀。
薩特真有面子!
打開(kāi)《自傳與公傳》第一部《迷失之地》,我一口氣讀將起來(lái),然后是第二部《傷痛之年》。《傷痛之年》讀得差不多時(shí)也快要“就地過(guò)年”了,這時(shí)候,我翻出半年前開(kāi)了個(gè)頭的東西,準(zhǔn)備寫(xiě)成大塊文章,而董學(xué)仁的書(shū),仿佛也為我的文章提供了一個(gè)鮮活的歷史語(yǔ)境。我要寫(xiě)的齊大衛(wèi)先生是1955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的,我必須從頭說(shuō)起;董學(xué)仁則是從他在娘肚子里的1954年開(kāi)始寫(xiě)自己的。這樣,我寫(xiě)的人與他說(shuō)的事就有了奇妙的交集。待這篇《檔案內(nèi)外的齊大衛(wèi)》塵埃落定,我又打開(kāi)了《狂亂之心》《深淵之火》《獻(xiàn)祭之羊》《大地之門(mén)》……我看到的《自傳與公傳》,寫(xiě)到董學(xué)仁大學(xué)畢業(yè)那年,即1983年,此后則是一片空白。后面的年代他寫(xiě)了嗎?他原來(lái)計(jì)劃寫(xiě)到哪年?
應(yīng)該先介紹一下他的寫(xiě)法。
實(shí)際上,讀完第一部,我便意識(shí)到了董學(xué)仁的勃勃野心,也對(duì)他的寫(xiě)法基本門(mén)兒清。五十歲那年,他“突然決定把自己經(jīng)歷過(guò)的、看到聽(tīng)到和想到的事情記錄下來(lái),用非虛構(gòu)文學(xué)的方式記錄下來(lái),給比我小的人、比我經(jīng)歷少的人、與我不是一個(gè)國(guó)度或者不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人來(lái)閱讀”。但他不想寫(xiě)成小說(shuō),因?yàn)椤爱?dāng)代中國(guó)小說(shuō)的想象力太弱了”“我想來(lái)想去,至多可以像諾曼·梅勒《劊子手之歌》那樣,寫(xiě)一些非虛構(gòu)的東西。不同的是,他采訪的是別人,我采訪的是自己和我經(jīng)過(guò)的時(shí)代。”然后他繼續(xù)寫(xiě)道:
再想來(lái)想去,我將要寫(xiě)下的東西,是將我、我的家庭、我的城市、我的國(guó)度、我的世界融會(huì)在一起的編年史,是自傳和公傳。
“公傳”一詞可能在世界上是第一次被使用,只能從與自傳相對(duì)的字面意義去理解。它們?cè)谖业挠洃浝飼r(shí)而融會(huì),時(shí)而分離,它們是自由的,沒(méi)有任何約束。
這是一種從沒(méi)有過(guò)的文體。記得我對(duì)一位比我小了十多歲的外國(guó)作家說(shuō)過(guò),這世界上本來(lái)就沒(méi)有什么文體,寫(xiě)的人多了,就成了文體。還有,人是寫(xiě)作的主導(dǎo),文體是為作家服務(wù)的,有什么樣的作家,就有什么樣的文體。讓文體束縛的作家,無(wú)論如何,都算不上聰明的人。
需要稍做解釋。董學(xué)仁出生于1955年,五十歲那年是2005年。也就是說(shuō)從2005年起,他有了這個(gè)念頭,然后開(kāi)始了這次寫(xiě)作長(zhǎng)旅。用什么文體呢?可以說(shuō)是無(wú)文體或跨文體,也可以叫作非虛構(gòu)。“非虛構(gòu)小說(shuō)”這個(gè)說(shuō)法出現(xiàn)在20世紀(jì)50年代的美國(guó),此后又逐漸演變成“非虛構(gòu)”。而國(guó)內(nèi)大張旗鼓倡導(dǎo)“非虛構(gòu)寫(xiě)作”是2010年,其標(biāo)志是《人民文學(xué)》在當(dāng)年開(kāi)設(shè)了“非虛構(gòu)”欄目。也就是說(shuō),在許多作家和刊物還沒(méi)意識(shí)到“非虛構(gòu)”的價(jià)值時(shí),董學(xué)仁便已得風(fēng)氣之先,“弄潮兒向濤頭立”了。然而,與一些因“非虛構(gòu)”而暴得大名的作家相比,董學(xué)仁至今依然默默無(wú)聞,或者只是在很小的圈子里被人知曉。
為什么會(huì)有如此不同的待遇?答案很簡(jiǎn)單,因?yàn)槎瓕W(xué)仁寫(xiě)得太真實(shí)了,真實(shí)到只能在《西湖》這種地方性刊物發(fā)表一些。
于是我只好說(shuō)其寫(xiě)法。
自傳都知道,是不需要解釋的。在這部非虛構(gòu)作品中,董學(xué)仁的自傳應(yīng)該是一條經(jīng)線。因?yàn)樽詡鞯木壒剩虐研枰尸F(xiàn)的年頭上限定為1954年,而不是1949年或1942年;也是因?yàn)樽詡鳎疟WC了這部作品“我”的存在——“我”的所見(jiàn)所聞所感,“我”的體驗(yàn)與“我”的思考。然而,自傳顯然并非董學(xué)仁寫(xiě)作的主要目的,他的野心在于要為50年代以來(lái)的歷史寫(xiě)出公傳。于是,每年發(fā)生的、經(jīng)過(guò)“我之思考”值得一寫(xiě)的大事小事,便進(jìn)入了他所謂的公傳序列。
公傳中寫(xiě)什么呢?比如1955年,他有十三個(gè)子題目,其實(shí)就是做了十三篇文章。這些文章圍繞著對(duì)社會(huì)生活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展開(kāi)。但是,他并不只寫(xiě)“國(guó)家大事”,而是記錄了許多現(xiàn)在已被人遺忘,或者已被宏大敘事刪除的趣事小事,例如,在1961年,他曾寫(xiě)有《戰(zhàn)爭(zhēng),讓女人與孩子走開(kāi)》。如此看來(lái),這部大書(shū)所謂的“公傳”,實(shí)際上是重在揭示隱藏在歷史皺褶中的細(xì)節(jié)。說(shuō)實(shí)在話,無(wú)論是他寫(xiě)周揚(yáng)還是胡風(fēng),都不可能寫(xiě)到李潔非《長(zhǎng)歌滄桑——周揚(yáng)論》《誤讀與被誤讀——透視胡風(fēng)事件》的份上,但是他寫(xiě)出了那個(gè)特殊年代的歷史細(xì)節(jié)。
我就是沖著書(shū)里的細(xì)節(jié),才讀得津津有味的。
董學(xué)仁是作家,大概就是因?yàn)檫@個(gè)身份,他才讓更多的中外作家進(jìn)入到他的公傳之中,比如薩特。
我原以為薩特會(huì)出現(xiàn)在1955年,因?yàn)槟且荒辏_特與其終身伴侶波伏瓦有過(guò)一次中國(guó)之行。但實(shí)際上,薩特卻姍姍來(lái)遲。直到1964年,董學(xué)仁才專門(mén)寫(xiě)了一節(jié)《存在主義的薩特》。當(dāng)然,即便是這一年寫(xiě)薩特,他也依然是從1955年寫(xiě)起的。他說(shuō),那一年薩特來(lái)訪,中國(guó)方面派出一男一女兩位作家接待他們。那兩人“年歲比他們大,長(zhǎng)相比他們老”。但因?yàn)殡p方都不熟悉對(duì)方的創(chuàng)作,他們只好談美食,“法國(guó)的油封鴨、芝士焗明蝦、紫菜醬煎法國(guó)鵝肝,中國(guó)的紅燒肉、蔥香鯽魚(yú)脯、美味麻辣小龍蝦。薩特的感覺(jué)是,不知道中國(guó)這一男一女寫(xiě)作水平高低,但談起美食很有水平,好像不是訪問(wèn)中國(guó)著名作家,而是訪問(wèn)著名廚師”。
因?yàn)榭粗丶?xì)節(jié),我立刻對(duì)這一處的敘述產(chǎn)生了興趣:這兩位作家是誰(shuí)呢?
我想到了趙樹(shù)理和丁玲,但他們是薩特的同齡人,而且,“方向作家”趙樹(shù)理后來(lái)雖然“失去了方向”,但他是1943年才真正開(kāi)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我似乎在哪本書(shū)里看到過(guò)丁玲見(jiàn)過(guò)來(lái)訪的薩特。為了把這個(gè)細(xì)節(jié)落到實(shí)處,我請(qǐng)教了年輕的薩特研究專家閻偉教授。他告訴我,從1955年9月起,薩特與波伏瓦來(lái)訪中國(guó)45天,曾訪問(wèn)過(guò)沈陽(yáng)四天,當(dāng)時(shí)由作家陳學(xué)昭陪同。羅大岡留學(xué)過(guò)法國(guó),期間亦曾陪同。但他明確指出,趙樹(shù)理沒(méi)見(jiàn)過(guò)薩特,我在《趙樹(shù)理年譜》中也沒(méi)查到相關(guān)記載。
于是,這兩個(gè)作家是誰(shuí)依然下落不明。
但在我看來(lái),這一節(jié)內(nèi)容依然重要,因?yàn)槎瓕W(xué)仁談到了20世紀(jì)80年代存在主義給他帶來(lái)的正面影響:“一是調(diào)整了社會(huì)觀念,知道社會(huì)是一張巨大的網(wǎng),我是其中的一個(gè)網(wǎng)結(jié),反抗只能是局部的反抗;二是樹(shù)立了個(gè)人英雄主義,因?yàn)榇嬖谙扔诒举|(zhì),你選擇了個(gè)人英雄主義,才能成為你個(gè)人的英雄。這種影響至今還在延續(xù),我現(xiàn)在的寫(xiě)作,仍然是想要成為個(gè)人英雄的一種努力。”
我在前面說(shuō)過(guò)我寫(xiě)出了《檔案內(nèi)外的齊大衛(wèi)》。在齊大衛(wèi)的檔案里,最觸動(dòng)我的一份材料是《對(duì)我的“個(gè)人英雄主義”的檢查與認(rèn)識(shí)》,“個(gè)人英雄主義”伴隨他走過(guò)二十多年的歲月。只是到了薩特和存在主義影響中國(guó)的年代,個(gè)體才終于從集體中成功剝離,個(gè)人英雄主義也才沖破集體英雄主義的重重迷霧,成為“80年代新一輩”的價(jià)值觀念。可不可以這樣說(shuō),董學(xué)仁寫(xiě)出的這部大書(shū),實(shí)際上就是20世紀(jì)80年代價(jià)值觀的重要遺產(chǎn)?
我傾向于這么認(rèn)為。而且,董學(xué)仁不僅得益于薩特帶來(lái)的價(jià)值觀,他的寫(xiě)法似乎也高度吻合了薩特倡導(dǎo)的文學(xué)觀和寫(xiě)作觀。眾所周知,薩特高舉的是“介入文學(xué)”的大旗,但他同時(shí)在《什么是文學(xué)?》中也說(shuō)過(guò):“人們不是因?yàn)檫x擇說(shuō)出某些事情,而是因?yàn)檫x擇用某種方式說(shuō)出這些事情才成為作家的。”這句話在我看來(lái)非常重要,它甚至可以成為檢測(cè)作家成色的試金石。而這里所謂的“某種方式”,既可以寬泛地理解為文學(xué)形式,也可以理解為某種文體。
很可能這就是董學(xué)仁寫(xiě)作的價(jià)值和意義:因?yàn)橐揽總€(gè)人英雄主義的支撐,他“介入”并且說(shuō)出了許多事情,但這只能證明其勇敢;而當(dāng)他以“非虛構(gòu)”的方式如此講究地說(shuō)出這些事情時(shí),事情的真相所袒露出來(lái)的本來(lái)面目,才具有了直指人心的效果。不妨設(shè)想一下,假如他選擇了小說(shuō)的寫(xiě)作樣式,其真實(shí)性,則完全可能大打折扣。我沒(méi)想否認(rèn)小說(shuō)的真實(shí)性,但小說(shuō)追求的是另一種真實(shí),而那種意義上的真實(shí),弄不好也容易變成偽飾。
但有趣的是,他在《讀書(shū)有沒(méi)有用處》一節(jié)的一開(kāi)篇就寫(xiě)道:
有人說(shuō),凡是自傳,都有小說(shuō)的成分。被他這樣一說(shuō),我一直當(dāng)成長(zhǎng)篇散文來(lái)寫(xiě)的這些文字,幾乎就變成了長(zhǎng)篇小說(shuō)。
再想一想,他是對(duì)的,我的文字,描述了很多奇特、怪誕的事實(shí),如果被另一個(gè)國(guó)家或者另一個(gè)時(shí)代的人閱讀,很容易被當(dāng)成想象力豐富的虛構(gòu)。
于是有必要談?wù)務(wù)鎸?shí)。
魯迅文學(xué)院與北師大合招的研究生班中有位叫王玲的作家學(xué)員,我正在指導(dǎo)她做碩士學(xué)位論文。她的論題是“非虛構(gòu)”寫(xiě)作中真實(shí)感的構(gòu)建問(wèn)題,目前已拿出初稿。在她看來(lái),真實(shí)感的構(gòu)建有三條途徑:一,口述實(shí)錄的傾訴;二,歷史資料的打撈;三,現(xiàn)場(chǎng)介入的凸現(xiàn)。由此來(lái)看《自傳與公傳》的構(gòu)建方式,我以為它主要是以第二種為主,卻也有一和三相輔佐。當(dāng)然,除此之外,它還有個(gè)人回憶開(kāi)道或?yàn)槠浔q{護(hù)航。于是,這部作品中的真實(shí)感就呈交叉重疊之貌:歷史資料是主角,口述實(shí)錄、現(xiàn)場(chǎng)介入和個(gè)人回憶則陪伴其左右,它們相互指涉,相互印證,層層疊疊,密密麻麻。這樣一來(lái),真實(shí)感也就具有了厚度和力度。
但真實(shí)感只是一種主觀感受,它能夠成立,其前提是有真實(shí)這碗酒墊底。
那么,什么又是真實(shí)呢?這個(gè)問(wèn)題說(shuō)起來(lái)恐怕比較麻煩。以前的文學(xué)理論教科書(shū)告訴我們,有兩種真實(shí),生活真實(shí)是其一,藝術(shù)真實(shí)為其二。按夏之放主編的《文學(xué)理論百題》的說(shuō)法:“所謂生活真實(shí),是指實(shí)際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人和事,即生活事實(shí)。而藝術(shù)真實(shí)則是指文學(xué)作品通過(guò)具體形象反映了社會(huì)生活的真實(shí)面貌,揭示出社會(huì)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本質(zhì)意義。藝術(shù)真實(shí)來(lái)源于生活真實(shí),然而生活不等于藝術(shù),生活真實(shí)也不就是藝術(shù)真實(shí)。”為了說(shuō)明藝術(shù)真實(shí)優(yōu)于生活真實(shí),教科書(shū)往往會(huì)舉例道:《白毛女》的“生活真實(shí)”原本不過(guò)是一個(gè)“白毛仙姑”的民間傳說(shuō),但經(jīng)過(guò)周揚(yáng)指導(dǎo),特別是經(jīng)過(guò)賀敬之等同志的再創(chuàng)作,立刻就揭示出了這個(gè)傳說(shuō)中所蘊(yùn)含的生活本質(zhì)——舊社會(huì)把人變成鬼,新社會(huì)把鬼變成人。
其實(shí),藝術(shù)真實(shí)在我看來(lái)并無(wú)多大問(wèn)題,而且確實(shí)也存在著一種名為藝術(shù)真實(shí)的真實(shí)。為什么恩格斯認(rèn)為《人間喜劇》提供了一部法國(guó)社會(huì)的“卓越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歷史”?為什么他說(shuō)他從巴爾扎克那里學(xué)到的東西“比從當(dāng)時(shí)所有職業(yè)的歷史學(xué)家、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和統(tǒng)計(jì)學(xué)家那里學(xué)到的全部東西都要多”?原因在于巴氏奉行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把藝術(shù)真實(shí)做到了極致。但問(wèn)題是,從蘇聯(lián)過(guò)來(lái)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根本無(wú)法與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同日而語(yǔ)。所以在我們的語(yǔ)境里,藝術(shù)真實(shí)成了“兩結(jié)合”“三突出”“高大全”和“紅光亮”。而此時(shí)回到生活真實(shí)、歷史真實(shí),就是對(duì)異化了的藝術(shù)真實(shí)的深度拒絕。我以為,這才是“非虛構(gòu)”的主要價(jià)值,也應(yīng)該是董學(xué)仁之所以如此打造他筆下真實(shí)的原初動(dòng)機(jī)。
我還看到董學(xué)仁說(shuō),如何挑選合適的敘述語(yǔ)言來(lái)寫(xiě)這部《自傳與公傳》,曾經(jīng)讓他頗費(fèi)琢磨,因?yàn)樵谠S多地方和許多情形下,語(yǔ)言里都“充滿了矯飾的空洞”,所以,我也確實(shí)看到了董學(xué)仁在語(yǔ)言層面的努力。汪曾祺說(shuō)過(guò):“寫(xiě)小說(shuō)就是寫(xiě)語(yǔ)言。”我前面提及的作家聶爾說(shuō)過(guò):“寫(xiě)散文就是寫(xiě)句子。”他們也都是漢語(yǔ)寫(xiě)作的高手。董學(xué)仁的敘述語(yǔ)言舒展中有隱忍與克制,冷峻中又不乏幽他一默或調(diào)他一侃的機(jī)鋒,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在我看來(lái),假如他的語(yǔ)言能再講究些更精致些,或許會(huì)有更好的閱讀主要是體悟效果。
作者簡(jiǎn)介:
趙勇,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文藝學(xué)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dǎo)師,兼任中國(guó)趙樹(shù)理研究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中國(guó)文藝?yán)碚搶W(xué)會(huì)常務(wù)理事、中國(guó)中外文藝?yán)碚搶W(xué)會(huì)常務(wù)理事等,主要從事法蘭克福學(xué)派、文學(xué)理論與批評(píng)、大眾文化理論與批評(píng)的教學(xué)與研究工作。獨(dú)著有《法蘭克福學(xué)派內(nèi)外:知識(shí)分子與大眾文化》《趙樹(shù)理的幽靈:在公共性、文學(xué)性與在地性之間》等十部,合著有《反思文藝學(xué)》等,主編有《大眾文化理論新編》等,合譯有《文學(xué)批評(píng):理論與實(shí)踐導(dǎo)論》。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文學(xué)評(píng)論》《文藝研究》《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文藝?yán)碚撗芯俊贰段乃嚑?zhēng)鳴》《南方文壇》等刊物發(fā)表文章二百余篇。在文學(xué)刊物、報(bào)紙發(fā)表散文、隨筆、時(shí)評(píng)等數(shù)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