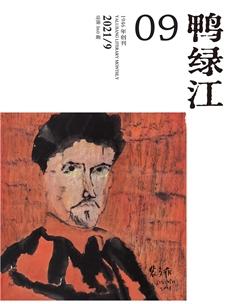非虛構(gòu)寫作與歷史的辯證和超越(評論)
讀罷董學仁百萬字的心血之作《自傳與公傳》,欽敬于作者堅韌的、日復(fù)一日的寫作姿態(tài)與書中流露出的歷史深度。他在開篇便提到:“我想來想去,至多可以像諾曼·梅勒《劊子手之歌》那樣,寫一些非虛構(gòu)的東西。不同的是,他采訪的是別人,我采訪的是自己和我經(jīng)過的時代。再想來想去,我將要寫下的東西,是將我、我的家庭、我的城市、我的國度、我的世界融會在一起的編年史,是自傳和公傳。”從以上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具備清晰的非虛構(gòu)寫作意識,這讓整本書具備了外在的辨認征兆,也讓讀者找到了深入文本的進徑。
相對于文學的“虛構(gòu)”寫作,“非虛構(gòu)”并非某種具體文體的寫作,它更多的是指一個大的寫作類型的集合。它在不同場域有不同的指認對象,文學界、新聞界、歷史界等對它的看法均有不同。而本書作者董學仁在青年時期從事多年文學工作,擔任過著名的校園文學雜志《新葉》的編輯,刊發(fā)北島等人的詩作;后期又有長期的媒體工作經(jīng)歷。此種復(fù)雜的人生體驗,使得他能夠超越“學院”的標準框架,讓《自傳與公傳》擁有文學寫作與新聞寫作的雙重特征,這一點,與白俄羅斯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好有一比。但此書的可貴之處,又在于親歷者的姿態(tài),在于作者深度書寫了中國一段特殊時期的特殊歷史面貌。所以筆者認為,“雜糅”之后的歷史才是《自傳與公傳》的本色,它將為構(gòu)建當代人的集體記憶發(fā)揮光熱。自傳是個人的歷史,公傳是集體、民族、國家的歷史,它們匯合成了時間的河流。在再現(xiàn)現(xiàn)實真相和還原歷史原貌方面,非虛構(gòu)寫作擁有極大的文體優(yōu)勢。它兼具微小和深度、情感和能量,讓文字得以獲得新的生長機會。正是借助“非虛構(gòu)寫作”,董學仁在種種“辯證”之中,完成了“歷史的超越”。
一.小與大:小人物與大人物
何兆武先生在《訪問歷史》一書中說:“老人有兩種,一種就是本人是很重要的歷史人物,應(yīng)該寫回憶錄……還有一種,就是普通的人,可以就普通人的觀點感受來記,那也是真實的歷史,因為歷史中并不僅僅有偉大的人物,也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要是寫下真實的回憶,我們就可以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的何兆武先生學識豐厚,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但他卻如此清晰地看到了歷史進程中小人物的作用。關(guān)注小人物,也是非虛構(gòu)寫作自誕生之日起的應(yīng)有之義,它既包括小人物拿起筆記錄生活的真實,也包括寫作者通過長期發(fā)掘以進入小人物的生活世界,而這,正是董學仁在寫作之中貫徹的理念。他同時寫小人物和大人物,運用親歷和文本兩種資源,讓歷史變得更加豐滿和新鮮。
在側(cè)重于表現(xiàn)集體主義的時期,文學作品中對個人精神著墨相對較少。但董學仁以人道主義精神重新發(fā)掘個人的生命痕跡,提供了一種新的認識世界和歷史的方式。他為不幸慘死的“無名者”立傳,有他不認識的人,有他的熟人,還有許多其他人;他寫被誤鎖在防空洞中去世的熱戀情侶,愛情居然“不幸”地走向了人間地獄;他寫他的外婆因為饑餓來到城里居住,卻因晚上眼神不好而將大便拉上了全家人的救命口糧,后因內(nèi)疚返鄉(xiāng),結(jié)果很快就去世了;他寫那些苦練游泳的逃港者,也寫那些在頻繁戰(zhàn)爭中去世的人;他寫一個人因自行車多次被偷而發(fā)瘋,也寫一個人因逃避工作而故意去偷自行車……所有這些人似乎都很小,但董學仁在歷史的世界里,用豐富的細節(jié)召喚情感,重新給予他們尊重與肯定。當他們會聚在一起時,新的歷史就產(chǎn)生了,非虛構(gòu)的深度也得以完成,而看似死去的集體記憶也重新活了過來。董學仁當然也寫“大人物”,但他寫“大”是為了映襯“小”,發(fā)現(xiàn)“小”的真實。正是這種極小,抓住了人性的深處與歷史的本質(zhì),也鍛就了他作品的深度,即在微小中成就真實。換句話說,董學仁筆下的“公傳”并不試圖把握宏大與完整,那只是他眼里的全世界與集體記憶,并不具備“暴力”屬性。它是小人物的,也是宏大時代的。
這種專注于“小”的寫作,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成為一個傳統(tǒng),后發(fā)的“非虛構(gòu)寫作”可以說是它的延續(xù)。在革命熱潮之后的改革熱潮中,部分寫作者厭棄了日復(fù)一日的宏大敘事,轉(zhuǎn)而感興趣于“小現(xiàn)實”和“小歷史”的展現(xiàn)。這些作家真誠地進入記憶,在細致反映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上予以超越和提升。董學仁也正是如此,許多的“小”不代表零碎,背后其實有著深厚的思考與歷史的緣由。這正是“小”的貼切性帶來的,它以更為直接的距離打開記憶的閥門,進而刺激思考。通過董學仁筆下種種小人物的命運,現(xiàn)實被翻了過來,這種從現(xiàn)實問題出發(fā)的眾多敘述超越了單純的事件,通過追根溯源的歷史敘事建構(gòu)了嶄新的集體記憶,讀者方能被引領(lǐng)去重新認識過往。董學仁為自我的人生立傳,為千千萬萬小人物立傳,就此,舊的歷史被超越了。
二.虛與實:有情與事功
王德威的《抒情傳統(tǒng)與中國現(xiàn)代性》記載,1952年沈從文赴四川參加土改,曾致信家人。他以《史記》為例,談到中國歷史的兩條線索——“事功”與“有情”:(兩者)“有時合二為一,居多卻相對存在,形成一種矛盾對峙。對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會中‘事功相背斥,以顧此失彼……因此有情也常是‘無能。現(xiàn)在說,且不免為‘無知……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年表諸書說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傳卻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別的東西……即必須由痛苦方能成熟積聚的情——這個情即深入體會,深至的愛,以及透過事功以上的理解與認識。”透過沈從文的文字,讀者可以發(fā)掘出許多東西。在“事功”占主導(dǎo)地位的年代,沈從文卻看到了“有情”的價值,這種人道主義的悲憫之心堪稱偉大。他在大變局之前透過“有情”與“事功”的辯證轉(zhuǎn)折,清晰地預(yù)見了后來的時代變革,為此才兩次自殺。但幸運的是,“有情”讓他重新回到了生活的正軌,接受了“無能”,并通過轉(zhuǎn)入文物工作,和環(huán)境保持距離以保全性命。
這種“無能”和“有情”,放在董學仁的書中也是一樣,在他書寫的二三十年里,他始終是一個“局外人”。他“年幼時營養(yǎng)不足,身體瘦弱,讀小學后因為有一些口吃,語言表達不如別人,養(yǎng)成了敏感、內(nèi)向、柔弱的性格,孤獨感一直很強”。這種孤獨的個性固然使他在當時備嘗失落,但同時,也讓他以更加清醒的姿態(tài)感受周遭的一切,不斷積聚痛苦與失望。董學仁在反思記錄那數(shù)十年的歷史時,支撐他對“小”持續(xù)關(guān)注的正是“有情”。于是,非虛構(gòu)也才成為“文學”。對于人物的命運,他不持冷眼旁觀的態(tài)度,而是始終將個體心力傾注其中,書寫事件中的情感流動。在《自傳與公傳》中,他記錄最多的感受恐怕是愛情、饑餓和“無常的夢”,小人物在這些“活動”中的活力極大地豐富和照耀了歷史,那眾多鮮活的材料更增添了文本的分量。
原本是可以養(yǎng)活自己的,可為什么突然就大饑荒了?他寫自己的饑餓,寫全家人的饑餓,以及所有其他人的饑餓和一小部分人的“不饑餓”。饑餓這東西看不見摸不著,無比虛無,但卻能將特定環(huán)境下的人物命運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連“動物性”的基礎(chǔ)需要都不再正常,所以,人也早已不再是“人”了。但當董學仁深度回溯這些事件時,可以看出的恰恰是作者巨大的“有情”,他是在為那些不幸的人哀悼,更是警示后人那樣的悲劇不要重演。
撇開饑餓,人最基本的情感“愛”,竟然也要“被迫消失”。它要么直接被消滅,要么得沾染上種種功利因素而不再純潔。在作者曾供職的長甸機械廠,一位漂亮的女工向一個男工表白愛意,那個男工卻因為物質(zhì)的原因拒絕了她,并把這件事情擴散了出去,不久,這個叫阿玲的女孩就“羞愧”自殺了。愛成為羞辱的理由,成為一種致命的罪過。于是,美好的情感成了“墳?zāi)埂保瑦矍閯t只能作為面目猙獰的禁忌而存在。但人總需要愛,壓抑也需要出口,于是又有了離奇怪誕的“夢”。一位年輕男工夢到和車間一名女工發(fā)生了關(guān)系,早上醒來到處吹噓,導(dǎo)致那位女工“羞憤難當”而上吊自殺。當然事情沒完,后來經(jīng)過法院激烈討論,院長最后拍板決定,判處年輕男工10年有期徒刑,罪名為“反革命夢奸罪”!因為現(xiàn)實中愛情與性都是禁忌,于是它只好逃逸和藏匿到夢境之中。但當“夢”清晰流出時,居然也具有殺人的力量,如此縹緲的東西效力竟這么大。
借助董學仁作品中“有情”的一面,讀者可以看到,那些有情的力量會被“事功”壓抑到什么程度,而“有情”還是辨識董學仁作品的核心要素。以上提到的對“饑餓”“愛情表白”“夢”等事件的敘述,與典型的歷史敘述有著極大區(qū)別,由于讓歷史接受了文學的修飾,董學仁的非虛構(gòu)寫作便不僅具有史料的價值,更是充滿了人的味道。也正如沈從文所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當年弱小的董學仁將自己的感受藏匿起來,說很少的話,卻默默將自己的情感注入無辜的大千萬物。這些對他物的感受一直沒有離開,許多年后,重新鮮活地注入了《自傳與公傳》。對普通人而言,那些宏大敘事都太遙遠,這些細微的感受卻深入人心,看似雜亂無章,卻能“潤物細無聲”。在虛和實的交會處,在有情與事功的爭斗與辯證中,機槍口號和帝王將相都成為空虛,董學仁筆下的文字卻可能因有情而悠遠久長。
三.精與繁:用途與濫用
前文提到,董學仁的作品以非虛構(gòu)的寫作姿態(tài)呈現(xiàn)為總體的“歷史寫作”,對塑造集體記憶和理解人性與現(xiàn)實有一定的作用,但在言辭、思想和摘選上尚擁有一些上升的空間。當然,超越?jīng)]有止境,成為“超人”需要持續(xù)努力,或許用董學仁比較喜歡并多處引用的尼采來理解這一過程會更好些。在《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一書中尼采曾說:“不管是對一個人、一個民族、還是一個文化體系而言,若是……其‘歷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會傷害并最終毀掉這個有生命的東西……所有這些,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對民族而言,都有賴于一條將清晰可見的東西與模糊陰暗的東西區(qū)分開來的界限而存在。我們必須知道什么時候該遺忘,什么時候該記憶,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時候該歷史的感覺,什么時候該非歷史的感覺。”
尼采的這段話不難理解,概括而言,便是提醒人們,需要限制對歷史的感受與接收:我們需要更多的裁剪和思考,而不是不斷去堆積;不要讓歷史來掌控生活,而是要讓生活去主導(dǎo)歷史。具體到非虛構(gòu)的歷史寫作,則需要作者更深入地思考寫作的核心,并得出一定的主線和規(guī)模。這也正如尼采所說:“一個人必須通過‘反思自己真正的需要,來整理好自己內(nèi)心的那堆混雜物,他需要用自己性格中所有的誠實、所有的堅定和真誠來幫助自己對付那些二手的思想、二手的知識、二手的行動。”以深度著稱的非虛構(gòu)寫作,似乎也到了需要接受一定規(guī)模限定的時候了,因為過于冗長的“深度”,容易演變成虛無和單純的智識游戲,堆積會變得極其危險。如《古拉格群島》那般可怕的蔓延,或許不是作者的經(jīng)歷所能支撐的,畢竟,對于所記錄的內(nèi)容,董學仁只是個不完全的親歷者,有大量的東西,尚需借助紙質(zhì)資料和他人回憶,這樣的非虛構(gòu),在效果上很難不大打折扣,至少編排選擇上的笨重無序,就會拖拉全書的后腿。因此,作者起筆之初即提出的寫作基準,看上去大半并未完成。比如對諾貝爾獎的諸多記錄,就未免空泛和略顯多余,這暴露出的,是思想準備的不夠完善;而記錄諸多哲人行跡時的蜻蜓點水,又常常因為或理解不夠或生硬牽強,有著一些拉大旗做虎皮的嫌疑。思想并不依靠數(shù)量,深度和質(zhì)量才是稀缺之物。
針對患有“歷史病”的人,尼采給出的是這樣的解藥:“歷史的解藥是那些‘非歷史和‘超歷史的東西……我用非歷史一詞指代那種能夠遺忘、能夠在自己周圍劃出有限視野的力量和藝術(shù)。我稱之為‘超歷史的力量,它能將目光從演變的進程上挪開,轉(zhuǎn)向賦予存在一種永恒與穩(wěn)定特性的事物,轉(zhuǎn)向藝術(shù)和宗教。”顯然,尼采是希望人們?nèi)プ非笞诮獭⑺囆g(shù)和智慧等相對形而上的,也更重要的東西,而不是一味地拘泥于一堆事實流連打轉(zhuǎn)。
但愿尼采的意見,對《自傳與公傳》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或許,只有完成“精與繁”的第四重辯證,超越歷史的能量才能被讀者接受并發(fā)揮出來。
作者簡介:
鐘書,本名鐘大祿,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20級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