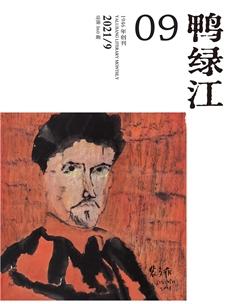董學仁印象(印象)
他比我們早醒好幾年
大學的同學雖然是同窗,但相互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計,有時甚至不像一個學門出來的。對我而言,董學仁就是這樣的同學。他比當時的我們至少先進幾年。
何以如此說?用古人的寫作方式,叫有詩為證。
那時我們離開故鄉到大連海濱求學,不免思念家鄉,不免寫下“故鄉的河在我心中流過”的所謂詩句,而他卻這樣寫起故鄉:
我不相信故鄉有什么特殊意義
也許在哪里都一樣
打敗命運 ?或被命運打敗
我們是工作了幾年后,于1979年,到當時的遼師院、現在的遼師大讀中文的。
我們那一屆學生,有兩件大事在省內外造成轟動。用我們一位寫作課老師的話說:“遼師是靠學生出名的。”
兩件大事的主要參與者總共不過六人,而董學仁都名列其中。
由一個小妹的輕生想到“友誼信箱”
為寫此文,我翻看了董學仁的博客,在他的《自傳與公傳》系列里,有這樣一篇文章,《一個小妹的非正常死亡》。他們有一天接到一封女學生來信,說自己想自殺,他們急忙趕到那所學校,見到了18歲的寫信的姑娘,原來是與她一同練武術的師兄弟常到學校門口接她,同學們便風言風語,她承受不了,自殺前給他們寫了一封信。
為什么給他們寫信呢?原來,董學仁和另外兩個同學搞了個“友誼信箱”,就是用通信的方式為校內外學生解答人生疑難。他們不但寫信,有時還親自出面解決來信者的問題。對此,《遼寧日報》在頭版頭條做過報道。
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那么大一所院校也很難在省報露面,更不要說頭版頭條了,可他們三個人的“友誼信箱”硬是上去了。
他們知道那個姑娘輕生是基于社會的疾病,是她厭惡周圍的人際環境。他們找了她家,也找了她學校,讓他們多給姑娘溫暖。
他們還帶她來我們學校玩,周末去公園散心,讓她感受大學生的生活。那個姑娘果然沒再尋死,一點點地,從他們的關愛中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氣——當然,還有后話,后話是幾年以后,那個姑娘的姐姐來信告訴早已大學畢業的他們,妹妹終于還是選擇了自殺,但妹妹認為,與他們接觸的那段時間,她活得最開心快樂,有被人尊重的感覺。
這期間,就是辦“友誼信箱”期間,董學仁還第一次得到了稿費。他到郵局左手接過錢,右手就將它全買了郵票,以便為他們的通信事業節省支出。我怕他耽誤學習,勸他少參加點社會活動,他卻樂呵呵地說“沒事”。還真沒事,不少整天摳書本的,成績真不如他。我不禁想,這小子沒準兒長兩個腦子。
友誼的深化
我倆當時是一個年級,但不在一個班。我們相識于系里的一次演講會。當時一家全國性的大報,對作家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發動攻勢,氣勢洶洶,讓剛從那場浩劫中逃脫的人們頗為義憤。我以《珍珠不能丟掉》為題,指責了那種棍棒式的批評方式。事先并未被安排演講的他,卻接著我登臺,還說劇本內容也無可非議,惹得輔導員老師和他辯論起來。會開完后,我將自己的一首《自度曲》給他看,內有這樣的句子:“一園芬芳盡荒蕪,誰肯眷顧?賞花人嘆,踐花人笑,種花人哭。遍地落英,何時再綴青青樹?”沒過幾分鐘,他寫了和詞,至今我還記得這樣幾句:“癡情誰為綠歡呼,無奈翻復。嘆甚枝折,憂甚葉枯,根堅在土。寄語芳華,重睹時留教春駐。”比我昂揚多了。
不久,校內搞攝影展,他來了興致,跑到公園照了兩張,一張題為《有希望才有痛苦》,另一張題為《人與人之間都有個縫隙》。后一幅的畫面,是公園長椅上等距離坐著一排人。一位老院長看后對他說,這題名不利于安定團結。他后來對我說,我應該再照一張學生們在買飯窗口擁擠的照片,取名為《人與人之間都沒有縫隙》,但終于沒照。也許照了沒有展出。
《崛起的詩群》讓我們同舟共濟
寫到這里,就要說到遼師學生出名的另一件大事了,那就是在《新葉》上全文推出了徐敬亞的四萬四千字長文《崛起的詩群》。
七八級畢業后,我接手主編學生文學刊物《新葉》。因為董學仁與林雪在第一屆學生文學大賽中獲一等獎,我拉他們參加了編輯工作,他任副主編,林雪任詩歌編輯。他修改稿件、設計封面、校對、發行,樣樣興致勃勃,充滿了創造力。
1982年,《朦朧詩選》編者之一高巖拿來了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全面評價了北島、舒婷、顧城等新詩群的創作。我讀完之后激動不已,決定在第八期《新葉》上全文刊出。董學仁提議那就干脆出個詩專號,我同意了。但顧慮到徐敬亞這篇文章可能會惹事,我們正面臨畢業,怕影響其他編委分配,就決定只有我與董學仁、林雪署名。他們二人慨然答應,頗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味道。
《崛起的詩群》推出不久,新葉文學社開新年晚會,我們共擬了一副這樣的對聯:“事業造就我們我們也造就事業,春天需要新葉新葉更需要春天。”記得我出的上聯,董學仁對的下聯。
那期載有徐敬亞長文的詩專號輾轉到了瑞典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手里,他專門給我們寫了一封信表達興奮之情。董學仁代表編輯部給馬悅然先生寫了回信。此后他們的通信維持了將近一年。
后來,《遼寧日報》用整版的篇幅介紹遼寧當年大學新詩潮的情況,其中大半是介紹我們,并配發了照片。還有四川大學的詩歌紀念館,在醒目的位置擺放著那本第八期的《新葉》,董學仁設計的封面依然大氣別致,現在看也毫不落伍。
2019年,我們在沈陽與他當年“友誼信箱”的兩個伙伴相聚,提起當年辦《新葉》的往事,我由衷地說:“那時全虧了老董。”他有些靦腆地說:“如果不是你當頭,換另一個人,結果也許就完全不同。”
2020年第一期的《詩探索》,還發表了姜紅偉約兩萬字的長文——《遼寧師院〈新葉〉:一本轟動國內外的大學生詩歌專號》。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畢業幾個月后他給我寄來的賀年卡,卡上這樣寫著:“我們還是我們,世界還是世界。我們和世界敵視著,感到各自的快樂。”他說他理解的敵視是一種不戰不和的狀態,也有尊重對手的因素,比如梅勒在《一場美國夢》里寫到的,一個敵軍司令給另外一個敵軍司令頒發獎章。
他眼里的好作家
董學仁閱讀量極大,眼界亦高。
在我們同學中,知名度最高的是詩人林雪,她的作品入選過《朦朧詩選》,她本人參加過《詩刊》的“青春詩會”,后來獲得過魯迅文學獎。有一年,《詩刊》介紹林雪,讓董學仁寫一篇評論文章。林雪有這么大成就,要擱別人,還不得掄圓了吹,可他只在文章中說林雪的創作找到了優越的方向。在一般人看來,這太沒高度,也缺少熱情,可在他那里,認為一個人找到了寫作的方向,那是件了不得的事情。有多少名作家寫了一輩子也沒找到寫作的方向啊!
當然,對林雪的才華橫溢,他也不是沒有評論,在《見證一段時光》中說:“她比同一代人多了一份對自然的淳樸感受,對生活的細膩感覺,對詩意的完好追求。”并說:“她個性上的寧靜與親和,輕松與單純,細微與精確,敏感與內省,也更接近一種優越的詩歌寫作狀態。”
寫到這,你可能以為他早已著作等身,其實,他正式出版的書就一本報告文學《藍色的路標》,雖然獲得過省里的一等獎,但遠代表不了他的水平。
真正能代表他實力的是在《西湖》上連載十年的《自傳與公傳》。
在這個系列剛連載一年多時,小說家吳玄就在《光明日報》上隆重推薦:
在一個文本內,董學仁為一個人和整個世界同時立傳,自傳是細致的,公傳是廣博的,在此,個體變大了,世界則變小了,充滿了生命感。董學仁消解了個人敘事和宏大敘事之間的壁壘,很可能創造了散文寫作的一個新范例。
我的一個叫李磊的朋友,非常喜歡這部作品,把它從頭到尾復印下來,摞起來足有一米高。
時代有時會意外成就一些作家,有時也會貽誤一些作家。有些作家適逢其時地燃放,像小鞭兒或二踢腳,有了動靜。而有的人卻像火山,沒噴薄而出時,平靜得不動聲色。董學仁就是一座火山,我相信,他的《自傳與公傳》不論是否有機會出版,都可能成為一部傳世之作。
大約十年前,他到本溪,在一個酒店里與孫承、馮金彥幾位朋友說起好作家是什么樣子。
他說好作家是有見識、有胸襟、有良知的人。
他說,一般來說,見識來自對事物的了解、熟悉和感悟。了解和熟悉是見的部分,感悟是識的部分,合起來叫見識。對于作家以外的人,這些已經夠了。但是對于作家,還必須有對世界上一大批優秀作品的見識。你讀過沒有?你讀懂了沒有?你知道它們的優秀在哪里?如果沒有讀過,如果沒有讀懂,如果不知道它們為什么優秀,你的文學見識可能就是零,就是負數。
他還說,30歲的時候,人們可以靠自己的靈性寫作。這種靈性包含了必要的寫作膽量和寫作技巧,可以組織起有情趣的文字,比如優美啊、漂亮啊、有膽量啊,讓大眾贊不絕口,在中國作家里混個不錯的、靠前的位置。但那不是好作家,甚至不是好作家的基礎。到了40歲,有沒有見識,有沒有胸襟,有沒有良知,這些才更重要。沒有這些,即使是中國第一的作家或作品,對于文學,也是沒意義的。
我們聽得清楚,董學仁這里說的好作家,按照世間通行的說法,可能是著名作家、優秀作家,或者是偉大作家、文學大師。
但他說那是人們的誤解。好作家不分那么多層次,在不好的作家里,才可以分出許多層次來。套用托爾斯泰的話,世界上好的作家都是一致的,而不好的作家,卻各有各的不好。
上面這些,可以看作他的文學觀,縱橫捭闔,睥睨天下。你可能以為他一定慷慨激昂,其實,這些他都是娓娓道來的,很怕聲音高了驚嚇到別人。
談起文學作品,他似乎很吝嗇使用贊美之詞。但也有偶爾破戒的時候。有一次我把朋友徐濤的詩發給他,他回信說:“讀徐濤這些詩,還是挺敬佩的。讀到了良心,詩人的悲憫之心。他寫詩的方式,就是把那些良知化為詩的表達方式,是難得的成熟。”
他讓我想起了木心
董學仁在鞍山辦過文學雜志《金銀花》,還在當地有線電視臺工作過,后來到了北京,參與一家報紙的編輯工作,還在那張報紙上開了名為《阿甘先生的文學課》的專欄。
在開專欄之前,他似乎工作很多,想讓我和馮金彥給他寫些介紹外國作品的東西,但馮金彥當時做報社總編沒有時間,我眼睛視力急劇下降,難以勝任。他在找楊雪松救場的同時,自己親自上陣。虧了他親自上陣,讓我們看到了全新的談名家文學的隨筆。
這個系列,目前寫了30多篇,是從世界上最早的偉大文學家開始的。當然是他心目中的偉大,與別人的不同。
原來想寫100篇或150篇,也就是說,在報上連載,每周一篇,連載兩年或三年。開始的時候只需要為報紙的青少年讀者介紹文學名家,這并不難,但他的個人愿意是從頭寫起,像是從巡視偉大作家的角度,描述這個星球上文學的歷史。
他不是從網上搜點資料就連綴成文,而是融進自己對文學的全部理解。
董學仁寫了很多人們熟悉的偉大文學家,比如莊子、荷馬、屈原、蘇東坡、但丁、莎士比亞、雨果;也寫了人們不熟悉但偉大的文學家,比如維吉爾、張若虛、克雷蒂安、夏多布里昂、歐文、庫柏、霍桑。他認為,偉大作家往往藏在偉大的作品背后,像海蟹藏在石頭后面。
有些他讀過和曾經喜愛的作品,其作者聞名世界,但因為不喜歡其立場,也沒有選,比如盧梭。
有的作家有很大意義,但更多是對于本民族和那個時代,他也沒選,比如俄國的普希金。他認為他的作品弱一些,現在的寫作者從他的作品里學不到什么。
在這些高大身軀面前,很多人是仰著頭的,只有一個角度看,而他卻取了一種特殊的角度,用了一組一組平視的鏡頭。
他就是這樣一個既淵博又有些挑剔的人。但越是這樣,讀者所得就越多。
每讀完他的這些作品,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個叫木心的作家。木心是這些年才廣為人知的大家,他對各種藝術門類的非凡見地,很是讓人嘆為觀止。在這方面,董學仁與他有相似之處——當然,在個人生活上,董學仁比木心安寧了許多。
作者簡介:
劉興雨,1955年生于遼寧本溪。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高級編輯。1983年畢業于遼寧師大中文系,在校期間曾任學生文學刊物《新葉》主編,與董學仁、林雪一起推出徐敬亞轟動國內的長篇詩論《崛起的詩群》。其《追問歷史》一書由著名出版家賀雄飛推出,多次再版,并榮登各地暢銷圖書排行榜。《中國雜文百部》推出《劉興雨集》,作為全國重點中學優秀教師推薦的雜文經典書目,已經第四次印刷。編輯過《中國雜文百部》中的《魯迅集》和《胡適集》。連續20年進入全國的多種隨筆、雜文年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