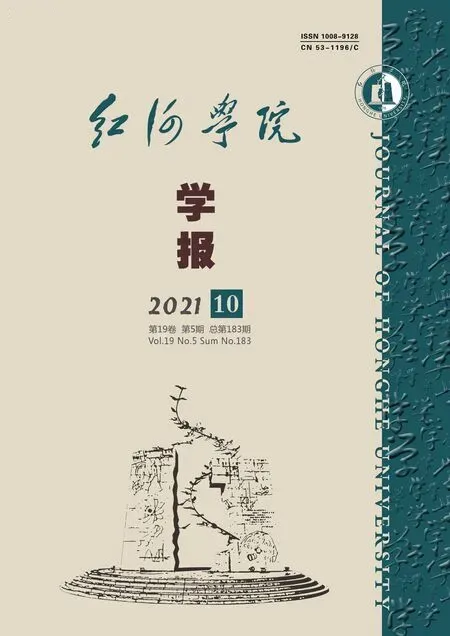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漢字偏誤現象及分析
郝同玉
(北京唐風漢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22)
漢字,作為集形、音、義一體的語素符號系統,是以語素或詞為單位。在這一點上不同于音素字母系統,如羅馬字、希臘字母,也不同于音節字母系統,如日語的假名等。正是漢字的這種獨特性,成為了第二語言學習者為之頭疼的根源。漢字問題伴隨漢語教學的始終,一直存在于漢語教學的各個階段,既影響了漢語學習者學習積極性,也影響了學習者漢語水平的快速提高,成為漢語學習的瓶頸。
漢字形體復雜,數量龐大,有些漢字筆畫繁多,辨認和書寫都很不容易。表現在漢字教學中就是“三難”,即難認、難寫、難記。因而漢語學習者和研究者都普遍認為,“(漢字)是漢語學習最大的難點”[1]。
一 初級階段漢字偏誤
初級階段是漢語學習者接觸漢字的開始,也是一個打基礎的重要階段。學習者對待漢字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其漢語學習的態度,如果不能解決漢字的書寫、辨認和記憶問題,在今后的語言學習中所遇到的困難和阻力就更大。
(一)漢字偏誤語料
本文漢字偏誤語料來自初級階段課堂作業、聽寫和考試。學生在開始本階段的漢語課程時,已經掌握約600~800個漢字。
以本次語料統計,實有漢字本字為115個;偏誤字,即錯字或別字為150個,偏誤率約為1.3%,即每個漢字本字平均產生約1.3個偏誤字。事實上,產生1個偏誤字的本字有83個,約占全部本字的72.2%。產生2個或2個以上偏誤字的本字有32個,約占全部本字的27.8%。從中可以看出,漢字偏誤呈現出個體因素特征,規律性較差。
(二)漢字偏誤類型
漢字偏誤劃分有的分為五類:字形相混,結構混淆,筆畫增減,結構不勻、位置改變,字詞不分、結構錯位。有的則分為七類:筆畫增損,筆形失準,筆順顛倒,部件易位,偏旁竄亂,間架不勻,及由于形近、義近、音近而產生的別字。根據以上分類,結合所得偏誤字具體特點,我們擬將漢字偏誤分為以下幾類:筆畫問題(包括:筆畫增益、筆畫缺失、筆畫錯誤)、同音代替、結構錯位、部件問題(包括:部件更換、部件增加、部件缺失),共計四大類,八小類。
二 漢字偏誤分析
由表1可見,因漢字部件問題而產生的偏誤在初級階段漢字偏誤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其次就是筆畫錯誤。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在初級階段學生已具有了一定的詞匯儲備,但是對于部件又不甚明了,由此而引起了部件問題。至于筆畫錯誤則仍是初學者的常見錯誤,主要是由筆畫不明所致,也就是說缺少基本的筆畫知識。

表1 漢字偏誤分類
從漢字本身來看,漢字數量眾多,有數萬之眾。據統計,現代通用漢字有6000~7000之多,目前公認的常用漢字也有2500個。漢字字形龐雜,筆畫繁多,而且富于變化,布局不統一,有很多的筆畫、部件,同音字、形近字也較多,因此對于第二語言學習者來說,偏誤率高也是自然的。
“外語教學分為親屬外語和文化及非親屬外語和文化兩個不同的教學領域”[2]。對歐美學生而言,漢語及漢文化屬于非親屬外語和文化在語言學習和語言系統的建構上自然相對困難。尤其表現在漢字的學習方面,漢字與拼音文字,如英語等,分屬完全不同的文字體系。
在課程設置及教學方面,目前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課程設置上大多都未單獨開設漢字課程。即使開設,也還未取得與必修課程,如綜合課、口語課、閱讀課等的同等地位,一般是作為技能選修課而設。
漢字教學還受到教材、教師因素的制約。對于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習者來說,漢字就是一些枝枝杈杈的圖形,一些曲里拐彎的符號。在此情況下,教材中對漢字的處理、編排、選用直接影響到漢字的教學效果,從而也就直接影響了學習者的漢字能力。
教師自身漢字知識不足,在具體的教學路徑和方法上也會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也是制約因素之一。不排除部分教師僅是作為漢語漢字的使用者而不是使用和研究者的現象。因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糾錯及對待漢字偏誤上缺乏科學有效的方法。故而雖然從理論及研究上對于漢字教學較為重視,但在具體的教學層面,需改進之處尚有許多。
三 目的語負遷移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告訴我們,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存在遷移現象,遷移又分為正遷移和負遷移。在所收集的漢字偏誤材料中,有一些是由于目的語負遷移引起的。
(一)筆畫問題
學生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具有了一定的詞匯儲備,因為對漢字筆畫認識不清,因此容易“張冠李戴”。波士納實驗證明,同形關系要比同音關系反應快[3]。如:漢字有“真、少”等,所以產生了筆畫的增益和缺失,如“宜”,留學生把下面的結構寫為“”,“步”的下半部寫為“少”等。
(二)部件問題
部件問題表現在淺層是筆畫的增減,其深層原因則是由于已掌握目的語的負遷移,就漢字而言,就是漢字部件的負遷移。學習者們常常用已知的漢字或漢字部件來替換自己所不熟悉的漢字,這種部件的替換以替換左邊或上邊部件為多,這類字占部件更換字的59.2%,因右邊部件、下邊部件更換引起的錯誤占40.8%。認知心理學中的“左邊特征比右邊特征重要,上邊特征比下邊特征重要”的說法在此得到了基本驗證。至于部件的增加和缺省,也是一種目的語負遷移的結果
(三)同音替代問題
現代漢語中的音節,不算聲調,只有400多個,如果考慮聲調因素,大約有1300個左右。其中“一音一素的約占全部音節的25%”[4],這意味著只有四分之一的音節能夠“聞聲知義”,其余四分之三的音節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同音語素。也就是同音現象在漢語里是非常普遍的。
漢語作為我們的母語,我們可以通過詞或詞組或句子來判斷同音詞,但是學習者則很難達到我們母語使用者的高度,尤其是尚處在初級、中級階段的學習者,更是無法通過語義來判斷。認知心理學告訴我們,(短時)記憶“對信息的加工,最主要的是以聽覺形式來編碼并保持或存儲的。”[3]因此也就出現了漢字書寫時的同音替代現象,如“情看、對不氣、起怪、隊手、租織”等。
(四)結構錯誤
這方面的錯誤主要是漢字的結構特點引起的。視覺上拼音文字是線性排列,呈單向性。而漢字則是立體的,多向行進的,呈三維性。在結構上,漢字主要有上下結構、左右結構、內外結構。因此在漢字的記憶過程中,呈現的視覺影像要比拼音文字復雜得多。在不了解漢字或漢字部件語義的情況下,信息的存儲及編碼顯然是困難的。由此導致信息存儲過程是低效的,甚至是錯誤的。因而在回憶時,即使信息的搜索和提取過程是正確的,但最后的輸出結果還是錯誤的。如“味”,留學生把左右結構換過來,成了“未口”,或者“想”,留學生把上面的“相”左右結構寫反。
四 漢字偏誤現象及啟示
漢字教學屬于語言要素教學,與語音、詞匯、語法一起構成漢語教學的基礎,是語言交際能力的組成部分。掌握不好漢字,漢語學習就會受到影響,尤其是到了中高級階段,漢字的學習和掌握更是關鍵。
但是漢字形、音、義三位一體的特點,完全不同于拼音文字,因而學生在漢字學習上普遍表現出畏難心理。漢字的特點要求我們幫助學生辨音、識形、知義。基于此,我們的漢字教學應采取什么策略呢?
初級階段(包括入門)學生的語言能力很弱,也是漢字教學的發生階段。在這一階段,筆畫、筆順的教學是必不可少的。在入門階段,應著重筆畫、偏旁的識別和記憶。在學生對筆畫和偏旁有了一定的認識后,需要把重點放在部件的教學上。合理地拆分部件,講解字義,分析字源,逐步提高學生對漢字的造字理據及文化背景的認知。如“氵”“灬”“青”“ 戔”等部字,或者如“忍”“解”“封”等,這些字的造字理據或是字源意義都可以很好地激發學生興趣。
根據認知心理學的詞優效應理論,部件教學應受到重視。心理學認為,記憶與記憶的材料的復雜程度有關。人的短時記憶大約是七個記憶單位,因此在拆分漢字時,我們得到的部件越少越容易記憶。根據《現代漢語通用字表》對7000個現行漢字的統計,平均每個字的筆畫為10.75畫。在部件方面,根據崔永華的統計,兩個到三個部件構成的漢字最多。《詞匯等級大綱》(1997)8822個詞的2866個漢字的部件,平均長度為2.91。另據統計,“《漢字信息字典》所收的7785個漢字中,由2~4個部件構成的漢字就占總數的90%”[5]。因此部件作為漢字教學單位,符合記憶規律,有利于漢字教學,應為漢字教學的重點。
在部件的拆分上,以有意義為原則。如“情”,我們可以拆分為“忄”“青”兩個部件,或者也可再拆分,把“青”分成上下兩個結構部件“”“冃”。因為長時記憶與“識記材料在學習者身上喚起的情感深度和在頭腦中產生聯想的認知廣度有聯系[6]。”這就啟發我們能夠盡可能地提供有意義的識記材料,另一方面也要盡可能地提供學生所熟悉的,能夠引起學生心理共鳴的材料,以便于學生的聯想和記憶。
很多人認為“漢語被公認是難學的語言,倒不是因為漢語語法難學,漢字難學是主要的原因。”[7]同時“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學習漢語,但是真正堅持下來的人不多,究其原因,漢字難學難記是一個重要原因。”[8]毋庸置疑,漢字已經成為了漢語教學的瓶頸,漢語教育者要努力嘗試改變人們對漢語、漢字難學的認識,力爭把學習瓶頸轉變為學習平臺。這要求我們更多地進行研究和分析,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兩個方面入手,積極改進和探索適合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漢字教學法,這無論是對實際教學還是對教材中的漢字部分的編寫都將具有實際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