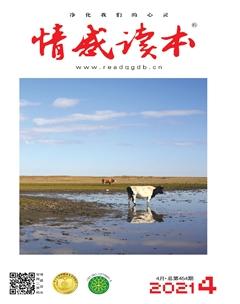等我回家
齊昕筠
這世上仍有人在等我,等我回家。這凄風冷雨,仍有一座城市、一個家、一盞燈,在等我。
我出發離家的那天,福州正下著擲地有聲、寒氣逼人的冬雨,云重得凄風也吹不開,室內水汽爬滿了玻璃窗。奶奶用她特地提早熬好的雞湯煮了一碗熱騰騰的太平面給我,又送我到樓下。爸爸媽媽開車送我去車站,看著我檢票進站、過安檢。到我拖著行李踏上通往候車廳的扶梯的時候,他們仍雙雙并肩站在安檢口外,一直到我們再不能看見彼此。
每一次,每一次都是如此。總是要一路目送,直到再不能目送。我總是避免去想起,卻又總是在思歸時分想起,呼吸里都帶著酸楚味。我有時想,于他們,又何必對自己這樣殘忍呢?
這是一場為人父母、為人子者都必須經歷的陣痛,斷裂之后則是彼此共歷的一次成長。倘若這世上沒有這樣多情感的羈絆,也許就可以避開那些牽念與愧疚,“活著”這件事就仿佛褪去負重,會輕松許多,可我又舍不得這世上有那么多千里迢迢的牽掛,哪怕我從未同他們表達過我的舍不得。
出發的前一天,外婆給我打了無數個微信電話,直到最后一個我才接到。她在電話里反復念叨,要喝什么樣的水,要吃什么樣的食物,要如何穿衣,要如何照顧自己——與她上學期末時發給我的語音留言如出一轍。外婆學會用微信不過一年半載,多的是打微信電話,每每想與我講話,又怕我在上課不便接聽,后來媽媽干脆教她發語音。外婆不會說“發語音”,她管這叫“按住講話”。學會“按住講話”的第一天,外婆就發一條語音給我,交代這交代那,又問我什么時候回家。這次亦然。她該交代的都交代完畢后,又有些埋怨地說:“你怎么也不到我這兒來。”哪怕實際上我們不過兩天前才剛剛見過面。我便答應她下次小長假就回家,她忙不迭跟上一句:“說好了啊,那我請你去喝茶。”——外婆最喜歡的事情之一,就是帶我們這些小輩去吃茶點。
寒假回家時,媽媽叫我拉個一家三口的微信群,還偷偷同我笑,“你爸特別嫉妒你經常給我發消息,又不好意思問你為什么不給他發,到頭來還要借我的手機看我們聊天記錄。”我舉雙手鳴冤,“冤枉啊,他不是自己說不怎么用微信嗎?”最后建了群,我似乎都能聽見爸爸的偷笑聲。
而奶奶,哪怕她平時從不說什么,放假時我說陪她去超市,她便開心;陪她看電視劇,她也開心。歸家前或是離家前,她總會準備我最喜歡的菜。
我知道,我都知道。
短暫又漫長的別離彌合了少年時互不退讓而撕裂出的鴻溝,我們彼此和解——與家人,與我曾經腳下的土地。
動車駛離我熟悉的站臺,開往我不抱任何期待的目的地。它去往異鄉的冬季和新的一輪未卜的困難。我總是在車駛離站臺之時就開始想家。我終于強烈地感受到,多么奇怪啊,自踏上異鄉求學的道路,家成了一年里只能短暫盤桓的驛站,而我成了故鄉的異鄉人。
我曾多么想要逃離,像許多同齡人一樣,想要把家園拋在身后,用大好青春的四年時光去看我向往的山川和世界。高三一年,大多數的時間被困在小小的一方書桌前,又總因為揮之不去的壓力和屢屢的挫敗導致的情緒與家人沖突,我自覺像籠子里被縛住翅膀的鳥。那時還有瑰麗的夢想,似乎看得到一片自由又燦爛的未來,無論如何肯定都要好過被囚在方寸之地,一心只想熬過這一年,掙脫出去。
最后我終于掙脫出去,卻遠沒能到達夢想的城市。高考失意,讓我徹底錯失我所夢想的一切,而背井離鄉之后的生活也全然不是曾經期待的模樣。孤身在異地,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大腦里永遠緊繃著一根不敢松開的弦。吃不到奶奶做的荔枝肉,也聽不懂包圍著我的當地絮絮的方言,它們筑起無形的圍墻將我隔絕在外。冬天到了,街上的人群裹緊了衣服步履匆匆,高中生們把脖子縮在校服里,坐在媽媽的車后座。他們都在回家的路上。可我在人群之中茫然無措,偌大個城市,卻不知道自己應該去到什么地方。我沒有接納它,而它似乎也沒有打算接納我。我終于真正理解那些古詩里的游子,“每逢佳節倍思親”“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才熬了半年,我卻已經熬怕了。
盡管我在家時也從未嫌惡過我的故鄉,卻還是在離開它之后,才真正覺出它給我的前所未有的強烈歸屬感。那里有我閉著眼睛都會走的街巷,有永遠叫我牽腸掛肚的福州菜,有我最熟悉的鄉音,嘰哩哇啦填滿我的耳朵,卻讓我會心地笑出來。熱土難離。
有時不免惶惑,我洶涌的懷鄉執念,到底是對“熟悉”帶來的安全感的依賴不休,還是不過是對自己的挫敗和孤憤的轉移呢?
可我又真的想家。
前幾天舍友病了,特別結實一姑娘忽然就病得軟綿綿的,但病得再難受也不過是咬著牙不說話。晚上她到陽臺給媽媽打電話,一開口忽然就帶了哭腔。她哭得止不住,卻在描述病情的時候依然說得很克制。我們其他人聽到,心里也怪不是滋味。
她后來說:“本來不想打電話的,白白讓她隔那么遠還擔心,可還是忍不住打了……”
獨在異鄉,我們都習慣了報喜不報憂,學會獨立處理好一切,可有時候情緒很大,大到撐破天地都不足以消解;情緒也很小,只要一個家,就被輕輕地接住了。
想起放假時,爸爸曾問我:“我同事他們都說小孩也就第一年想想家,之后就根本不想了。你明年應該也就不會這么想回來了吧?”他說話的樣子帶著一點小心翼翼的試探和訕笑。我嘴上笑他擔心多余,可心里卻難過得縮成一團。
可他不知道,心里的弦只有在家才會松下來,終于得以再做回任性的小孩。友人琰琰說:“回家就是水果總會以削好的方式出現在自己面前。”
于是我明白,我的懷鄉,也是戀家。
故鄉是無可替代的。
那里有我的家。我們彼此需要。
動車飛馳駛過閩江,家鄉的風物在我的車窗外不斷后退。在閃現中,我們交錯,然后背向而馳——我在離它越來越遠,我正離家越來越遠。可離開家之后,我所經歷的每一天,所邁出的每一步,都走在回家的路上,都在一步一步地靠近它。
我拍了一張動圖發給媽媽,江心島緩緩向后滑過我的畫面,青灰的天色下閩江水波濤依舊,亙古不變。每次回家,是它最先滑進我的視線,給我回家的擁抱;每次離鄉,也是它堅守陣地,向我作故鄉最后的致意。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媽媽一如既往地秒回:“這拍的啥啊?”
我哭笑不得,卻在那一刻異常篤定——
這世上仍有人在等我,等我回家。這凄風冷雨,仍有一座城市、一個家、一盞燈,在等我。
萬山紅摘自《少年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