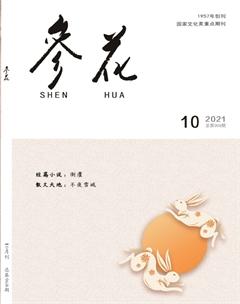文莫強求,鈍學累功
自古至今,文人騷客多好為文作詩,以抒發情致寄托遠懷。而在作家們的創作歷程中,或靈感突至,作品天成偶得而獨具風韻;或精心雕琢卻能不漏斧鑿之跡。但也有些時候,會如劉勰所言:“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若此時勉強為文,則往往難出佳作。
一、學問異于文。“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學問和文章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學問做得好,文章未必精彩,這一點從《詩經》的創作上便可以看出。在學問被官府貴族壟斷的時期,百姓是無法具備深厚學識的,但由于生活及勞動經驗豐富,他們卻也創作了諸多優秀的歌謠,這些歌謠后來匯成的《詩經》也就成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光輝起點,引領了后代文學的發展。時至宋代,人們極為重視學問,突出表現在創作中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面對這一問題,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出了“別材”“別趣”說。“材”與“才”通,即指才能學問,詩歌創作要有特別的才能,并非只靠書本學問就能造就好詩。孟浩然學識遠不及韓愈,但其詩卻在韓愈之上。曹植在文章上卓有建樹,謝靈運稱贊他“才高八斗”,但在學問方面曹丕的《典論·論文》則是曹植所不可比的。可見,學問與文章是兩個相互聯系而又相互區別的概念,切忌將學問與文章等同起來。
二、為文勿強求。古往今來,有人指物作詩立就,有人執筆揮墨成文,此中所言之天賦可謂可遇而不可求也。在文學創作中,天賦異稟之人的確有著先天的優勢,十七歲便因才華入“初唐四杰”之列,并為四杰之首的王勃可謂是神童般的人物。據《舊唐書》記載,他六歲即能寫文章,文筆流暢,被贊為“神童”。九歲時,讀顏師古注《漢書》,作《指瑕》十卷以糾正其錯。十六歲時,應幽素科試及第,授職朝散郎。這樣的天才為文作詩自是得心應手。在他前往交趾看望父親的途中,正趕上都督閻公在滕王閣上舉行盛會,王勃揮筆寫就《滕王閣序》。這不僅驚艷了當世人,更成了經久流傳的千古佳作。于天才般的王勃而言,又何必強行求文?
三、薄發須厚積。天賦雖然是創作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并非是決定性因素。前文所言不要勉強為文并非提倡不作文,而是要在適當的時機去作文。而這個時機恰恰就是靈感來臨之際,長期積累后靈感便會突至,此時為文才最為適宜。鈍學則累功,厚積而薄發,這都強調了勤學的重要性。天賦不可習得,而學問卻可通過學習獲得提高。天賦異稟之人若不通過學習充實自己,也會泯然眾人矣——這個詞語本就是指物作詩立就,文理皆可觀的方仲永,憑借卓越的天賦名噪一時,卻因其父“不使學”,且自己“不知學”,終究天賦也不復存在。那些本就具有天賦的人也是通過鍥而不舍地追求學問,提升自己才能取得如此成就的。以杜甫為例,他轉益多師,學魏晉之五言,杜審言之五律兼收盛唐詩人的創造興象。“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這不正是他認真鉆研學問的真實寫照嗎?因此,厚積是薄發的前提,天才尚且須努力,更何況是資質平凡之人呢?
韓愈在《師說》中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同樣的道理來說作文之事,人非生而善作文,因此,勤學而多寫則是提升學問、促進寫作的好方法。在學問有所欠缺時,多學勤學來提升自己;在行文的過程中,善于把握作文的時機,不勉強為文,不刻意求文。此則是“文莫強求,鈍學累功”。
作者簡介:房政旭,就讀于臨沂第一中學北校,系臨沂市作家協會會員。
(責任編輯 于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