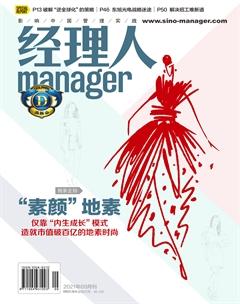管控互聯網商業超級巨頭的權力
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對于不完全競爭中有關壟斷競爭(monopolistic?competition)的概念,沒有更多的新說,仍然保留了前代經濟學家張伯倫(E.H.Chamberlin)的原意:行業中有許多生產者,但是其中的某些生產者生產出了具有差異化的產品,由此使得自己成為壟斷競爭企業。
其后,著有影響全球的《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等經典教材的哈佛大學終身教授曼昆(N.?Gregory?Mankiw)告訴學生,關于壟斷,是因為某個企業以低于大量生產者的成本生產產品,以及獲取生產所需的關鍵資源。
從“經濟人假設”角度,如果做到以低于大量生產者的成本生產產品,以及獲取生產所需的關鍵資源,就意味著可以追求自身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
這種具有“實利”的“經濟人假設”在互聯網壟斷競爭企業中得到了事實詮釋。
由倫敦國王學院的媒體、傳播與權力研究中心主任馬丁·摩爾(Martin?Moore)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副教授達米安·坦比尼(Damian?Tambini)在他們共同撰寫的《巨頭:失控的互聯網企業》中提出:“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已經在數字世界積累了我們難以想象的權力,而現有的監管機構對此無能為力,甚至還未察覺。這種新的數字壟斷的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對經濟、社會、政治和個人生活都已產生重要影響,未來可能會愈演愈烈。”
這些互聯網商業超級巨頭所擁有“難以想象的權力”包括:數字霸權、數據濫用、對反壟斷法的挑戰、對獨立新聞業的威脅、操縱思想和傳播、假消息中心、擁有注意力經濟權力等等。
細思極恐,互聯網商業超級巨頭擁有的“權力”完全超出了一個商業企業正常的經營范圍,變成了一種準國家力量。
如何管控這些超級巨頭無邊界的權力生長,不僅是全球的問題,也是我們同樣面對的新問題。
從成長演變角度,互聯網商業超級巨頭首先是從科技創新或商業模式肇始,然后在做大做強過程中,將其戰略完全轉向“獲取生產所需的關鍵資源”——其一、通過入股及并購手法獲取直接關鍵社會及商業資源要素;其二、通過大量吸收關鍵科技資源、人才資源獲取間接的社會、商業關鍵資源。
在管理學上,獲取生產關鍵資源被叫做“護城河行為”。但是,實施護城河行為,本質上是為了和對手產生不均衡競爭,即不公平競爭。
由于長期熟稔于不公平競爭,且越來越獲得效用的最大化后,互聯網超級商業巨頭就形成了平臺力量,進而形成平臺權力。遺憾的是,擁有這種權力的互聯網超級商業巨頭一方面不再將注意力放在創新,另一方面以壟斷手段擠壓后進新企業的生存空間。
當一家互聯網商業超級巨頭不僅具有長期且不可挑戰的平臺權力,同時還在公司中充斥了無數的精英員工為其提供權力智慧,這樣的互聯網商業超級巨頭,必然會對社會產生廣度影響,而如果有利于商業秩序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然也樂見其成,但是這樣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他們本質上很難脫離“經濟人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