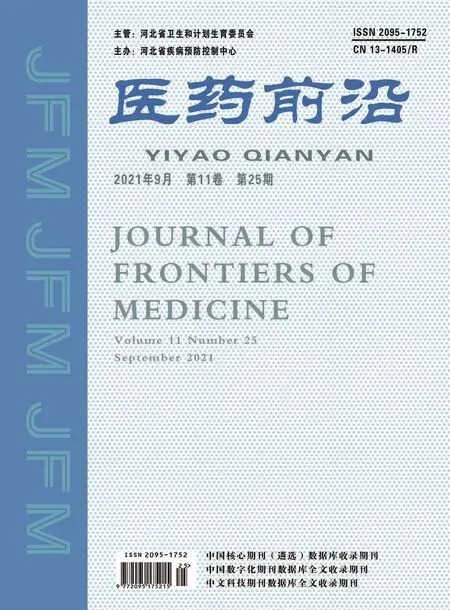D-二聚體與C反應蛋白及白細胞介素-6聯合檢測在診斷下肢深靜脈血栓中的價值分析
黃家良,陳銘碧,張其永,趙宇棟
(欽州市第一人民醫院骨科 廣西 欽州 535000)
國內已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人體內的骨質會隨著年齡增長而不斷流失,使得股骨頸骨折和股骨頭壞死的患病數量出現明顯的增長,進而危害了老年人群的生活和健康。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對于骨科疾患行人工置換股骨頭與髖關節置換術等術式的應用越來越多。但與此同時,術后出現的并發癥也愈發受到社會上的關注,尤其是下肢深靜脈血栓。由于下肢深靜脈血栓一旦脫落,容易造成肺動脈栓塞,使得患者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嚴重時會危及患者的生命,是骨科手術所必須重視的問題[1]。故對下肢靜脈血栓患者,早期診斷或盡早發現非常重要。為此,本研究將以髖關節置換患者,探討D-二聚體(D-D)、C反應蛋白(CRP)以及白細胞介素-6(IL-6)聯合檢測對下肢靜脈血栓形成的診斷價值,為臨床診斷提供理論依據,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關節外科2019年9月—2021年3月206例髖關節置換手術患者,將發生下肢深靜脈血栓的105例作為觀察組,年齡為60~82歲;將未發生下肢深靜脈血栓的101例作為對照組,年齡為60~82歲。納入標準:(1)皆與髖關節骨折的臨床指征相符;(2)皆配合該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3)皆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4)皆自愿接受手術治療。排除標準:(1)中途退出研究的;(2)肝、脾、腎功能異常的;(3)存在手術禁忌的;(4)合并惡性腫瘤的;(5)感染高危的。兩組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1.2 方法
該研究皆挑選我院經驗豐富、專業水平高的檢測人員進行操作,讓患者維持空腹的狀態,持續到采血結束,采集到3 mL的空腹靜脈血后實施離心處理,將轉速設置為3 500 r/min,離心處理5 min后,借助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分別以膠乳免疫比濁法檢測D-D,膠乳增強免疫比濁法檢測CRP,記錄術后1、3、5 d的數據并整理。
1.3 觀察指標
將兩組術后1、3、5 d檢測的D-D、CRP以及IL-6水平做比較。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7.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頻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 兩組D-D水平比較
觀察組術后1、3、5 d檢測的D-D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D-D水平比較(±s, mg/L)

表2 兩組D-D水平比較(±s, mg/L)
組別 例數 術后1 d 術后3 d 術后5 d觀察組 105 3.66±0.77 4.30±0.71 5.21±0.68對照組 101 2.40±0.54 2.47±0.52 2.53±0.44 t 13.640 21.038 33.441 P 0.000 0.000 0.000
2.2 兩組CRP水平比較
觀察組術后1、3、5 d檢測的CRP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CRP水平比較(±s, mg/L)

表3 兩組CRP水平比較(±s, mg/L)
組別 例數 術后1 d 術后3 d 術后5 d觀察組 105 10.63±4.05 16.72±3.48 19.77±3.37對照組 101 8.36±2.21 7.95±1.40 5.14±1.32 t 4.996 43.657 40.724 P 0.000 0.000 0.000
2.3 兩組IL-6水平比較
觀察組術后1、3、5 d檢測的IL-6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IL-6水平比較(±s, ng/L)

表4 兩組IL-6水平比較(±s, ng/L)
組別 例數 術后1 d 術后3 d 術后5 d觀察組 105 33.63±5.32 48.89±6.15 61.02±8.37對照組 101 25.59±4.28 28.81±4.49 19.27±3.72 t 11.923 26.678 45.951 P 0.000 0.000 0.000
3.討論
下肢深靜脈血栓是指內源性或者外源性因素使下肢深靜脈中血液動力學改變,導致血液凝固成塊狀所引起的疾病。下肢深靜脈血栓在血管外科特別多發,起因多與靜脈血流滯緩、靜脈壁損傷有關,侵害到較多患者的下肢健康,從而引發腫脹、疼痛以及沉重等表現。
D-D作為反映體內的高凝狀態以及纖溶活化的分子標志物之一,它由纖維蛋白單體與活化因子相互交聯,再經纖溶酶水解,產生的一種降解產物,與血栓之間存在密切的關系[2]。有研究認為,臨床上測定D-D簡便、迅速,對于下肢深靜脈血栓的診斷和預后評估具有重要意義,并且D-D對老年患者骨科大手術后的下肢深靜脈血栓具有很高的陰性診斷價值。也有研究發現,D-D是血栓形成后繼發纖溶的結果,反映的是血液高凝和纖溶亢進[3]。術后D-D水平對深靜脈血栓篩查診斷有一定價值,但準確性較低,其AUC值為0.688。分析其原因可能與D-D的檢測方法、試劑不同以及研究中確診靜脈血栓方法不同等因素有關。
根據相關研究表明,血管炎癥和血栓有著相關性,尤其是血管壁的內皮損傷性炎癥,而其中CRP作為炎癥的主要標記物之一,臨床上常以血清高敏CRP(hs-CRP)檢測血管炎癥反應,一旦血管穩定性受到影響,會造成血栓脫落[4]。已有文獻報道CRP可以作為肺栓塞的一個預測因子。據相關研究表明,急性下肢深靜脈血栓栓塞癥患者血漿CRP水平明顯升高,并證實炎癥因子在下肢靜脈血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hs-CRP化學結構與CRP完全一致,但敏感度極高,可以及時反映機體的炎性反應。hs-CRP是一種非特異性的急性時相蛋白,可誘導單核細胞組織因子表達,激活補體系統,使血管內膜損傷,破壞凝血纖溶系統的平衡,從而促進血栓形成。近年來的研究表明,CRP作為系統性炎癥和血液高凝的生化指標之一,對關節置換術后患者住院期間下肢DVT事件發生不靈敏[6]。但同時也有研究表明,hs-CRP水平升高可促進血栓形成,在下肢靜脈血栓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7]。hs-CRP水平升高越明顯,血管內壁損傷越嚴重,發生血栓可能性越大,監測hs-CRP水平變化對早期診斷下肢靜脈血栓有一定的臨床價值。
IL-6由內皮細胞、單核細胞和成纖維細胞等產生,屬于多向性作用的細胞因子。IL-6作為炎癥反應的重要炎癥介質,能獨立調節心血管功能,其與受體結合后可表現出多種生物學效應,包括分泌抗體、促血細胞生成、血小板生成,刺激肝臟合成急性時相蛋白,參與炎癥反應等[8]。IL-6可誘導纖維蛋白原、凝血因子等激活凝血過程,導致高凝狀態,進而促進血栓形成。相關研究發現,靜脈血栓形成的急性期血清CRP及IL-6水平明顯升高,CRP及IL-6在靜脈血栓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通過本文結果得出,觀察組術后1、3、5 d檢測的D-D、CRP以及IL-6水平較對照組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D-D對血栓形成性疾病具有早期診斷價值;CRP是一種非特異性的急性時相蛋白,敏感度極高,可以及時反映機體的炎性反應;并且IL-6與炎癥反應有密切的關系。
綜上所述,D-D、CRP以及IL-6聯合檢測對圍手術期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的預測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可為髖關節置換患者下肢深靜脈血栓的預測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