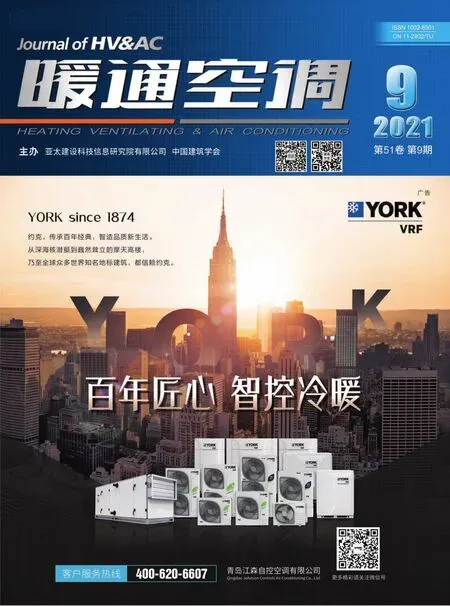過站運行條件下地鐵車站出入口卷簾門壓力分析
中鐵第一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 馬江燕 鄧保順 廖 凱 牛永勝
0 引言
隨著地鐵列車周期性地運行,地鐵車站出入口通道內也周期性地進出風。在正常運行工況下,列車進站制動減速,行車速度降低,且出入口通道敞開,故出入口通道內壓力較小,約為十幾至幾十Pa[1],一般不會對出入口通道內的附件產生危害。然而,在實際工程中,北方某地鐵線路停運后,列車調度行車時(所謂調度行車指線路停運后或開始運行前,需要將列車調運到車輛段或停車場,由此形成單向密集行車,列車過站運行),經常出現地鐵出入口卷簾門變形和脫軌的狀況,影響卷簾門的正常開啟。因此,有必要對過站運行等特殊運行條件下地鐵車站出入口卷簾門承受的壓力進行分析,從而提出減小卷簾門承壓的措施。
研究活塞風對地鐵車站影響的有效方法之一為實測。國內許多專家學者通過實測的方法研究了作用在屏蔽門上的風壓的大小、作用規律及車站型式、有無排風等因素對屏蔽門所承受的壓力的影響[2-3]。數值模擬也是研究活塞風對地鐵車站影響行之有效的方法,常見的有一維和三維模擬。由于地鐵空間結構的復雜性,三維模擬一般都是在大量簡化基礎上研究一輛列車、短時間內運行情況下活塞風對車站的影響[4-5],很難考慮到行車周期、多輛列車運行等影響因素。而一維網絡模型由于其便捷、準確等特點,在研究地鐵活塞風中得到了廣泛應用[6-8]。然而,在眾多活塞風壓對車站影響的研究中,對地鐵車站出入口的風壓研究較少[9]。
本文采用一維數值模擬的方法研究地鐵調度行車工況下活塞風壓對卷簾門的影響。
1 模型建立及邊界設置
1.1 模型建立
以實際運行線路為物理模型,采用IDA tunnel[10]建立一條總長度為12.824 km的線路模型(IDA軟件對活塞風預測的準確性已得到筆者的驗證[11-12],限于篇幅不再贅述),并以1個典型雙層島式A型地鐵車站(如圖1所示)為例進行詳細分析。


圖1 線路信息及模型示意圖
典型車站尺寸:站廳為98 m×20 m×5 m(長×寬×高);站臺為136 m×12 m×4.5 m(長×寬×高);4個出入口均為45 m×4 m×3 m(長×寬×高)。隧道面積為22.7 m2。列車為A型車,尺寸為140 m×3.0 m×3.5 m(長×寬×高),列車最大加速度為1.0 m/s2,最大減速度為1.1 m/s2,不考慮熱壓帶來的影響。迂回風道A和B面積均為22 m2,迂回風道上設迂回風閥控制迂回風道的開與關,活塞風井面積20 m2。列車不在站內停靠,過站時不減速。
1.2 主要邊界設置
常見的卷簾門型式大致可分為3類,如圖2所示。鏤空型卷簾門空隙率很大,大于90%,其局部阻力系數可忽略不計[13]。半密實型卷簾門上開有小孔,其局部阻力系數可等價于孔板出風口阻力系數[13],由于開孔率不同,局部阻力系數可在幾十到幾百之間,本文設定為100、300。密實型卷簾門上無空洞,卷簾門關閉時,形成的局部阻力系數理論上無限大,設定為9 999。北方地區由于冬季寒冷而且室外多風沙,為了阻冷風、風沙及防鼠的要求,地鐵出入口常采用密實型卷簾門。

圖2 常見卷簾門的類型
全高封閉站臺門(屏蔽門)和全高非封閉站臺門(安全門)是常見的2種站臺門型式。屏蔽門使軌行區和站臺完全分開,屏蔽門的結構型式決定了其存在大量縫隙,縫隙寬度一般為毫米級[14],本文模型把屏蔽門的縫隙折合為站臺門上的開口面積(0.2 m2)。安全門系統通常在站臺門上方存在一條百葉風口連接站臺和軌行區,每側站臺門百葉風口等效面積為50 m2。
另外,IDA模型中各個支路處總阻力系數根據文獻[13]進行計算得出,其中,出入口通道為8.4,活塞風井為10.5,樓梯口為2.0。
2 模擬工況
根據上述分析,設定表1所示工況進行模擬分析。其中,工況1為實際運行出入口卷簾門脫軌時的工況。該運行工況下,出入口通道采用密實型卷簾門,且為關閉狀態;活塞風閥執行冬季閉式運行模式,即活塞風閥關閉,列車不停站。

表1 模擬工況
設置其他工況與工況1進行對比:工況2~5與工況1對比,主要研究行車速度對出入口壓力的影響;工況6~8與工況1對比,研究行車間隔對出入口壓力的影響;工況9~11與工況1對比,研究卷簾門型式對出入口壓力的影響;工況12與工況1對比,研究設置迂回風道對出入口壓力的影響;工況13、14與工況1對比,研究活塞風井數量對出入口壓力的影響;工況15與工況1對比,研究站臺門型式對出入口壓力的影響。
3 模擬結果及分析
圖3顯示了不同行車速度下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出入口處的壓力隨著時間呈現周期性變化,行車速度越大,出入口處瞬時壓力最大值也越大;行車速度為40 km/h時,瞬時壓力最大值不超過47 Pa;行車速度為50 km/h時,瞬時壓力最大值不超過77 Pa;而當行車速度為80 km/h時,瞬時壓力最大值能達到252 Pa,約為40 km/h時的5倍。這是因為行車速度越大,形成的活塞風量也越大,從隧道進入車站的風量也越大,由于出入口卷簾門的阻擋作用,車站內空氣受到擠壓,使得出入口處的壓力隨著行車速度的增大瞬時顯著增大。

圖3 不同行車速度下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
圖4顯示了行車速度為72 km/h、不同行車間隔下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行車間隔越小,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越劇烈;行車間隔為120 s時,瞬時壓力最大值為170 Pa;行車間隔為180、240、360 s時,瞬時壓力最大值分別為244、239、225 Pa。可見,瞬時壓力最大值并不隨著行車間隔的減小而增大,這是因為速度一定時,單輛列車形成的活塞風量一定,進入車站的風量也一定,所以行車密度的增大,會增加出入口的平均承壓,但并不能使瞬時最大值增大。



圖4 不同行車間隔下出入口的壓力變化
圖5顯示了不同卷簾門型式下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卷簾門阻力系數越小,即卷簾門鏤空率越大,卷簾門所承受的瞬時壓力越小;當出入口采用密實型卷簾門時,瞬時壓力最大值可達170 Pa;當出入口設置的卷簾門阻力系數為300時,出入口的瞬時壓力最大值可達到92 Pa;當出入口不設卷簾門時,出入口的瞬時壓力最大值為21.4 Pa,僅為密實型卷簾門的13%。


圖5 不同卷簾門型式下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
圖6顯示了迂回風閥開、關條件下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2種工況下壓力變化曲線基本重合,迂回風道起不到良好的泄壓作用,迂回風道的設置與否,并不能改善出入口處卷簾門的承壓。


圖6 迂回風閥開、關條件下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
圖7顯示了不同活塞風井數量下出入口處壓力的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閉式運行時(即活塞風閥關閉),出入口處瞬時壓力最大值可達170 Pa;單活塞和雙活塞運行時,出入口處瞬時壓力最大值分別為45、35 Pa,分別為閉式運行工況的26%和21%。可見,活塞風井能起到很好的泄壓、分流作用。


圖7 不同活塞風井數量下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
圖8顯示了不同站臺門型式下出入口處壓力的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既使是閉式運行,出入口設置密實型卷簾門,屏蔽門系統下出入口處的瞬時壓力最大值(40 Pa)遠小于安全門系統下出入口瞬時壓力最大值(170 Pa),僅為安全門系統的24%。這是因為屏蔽門對車站起到了很好的“屏蔽”作用,使得進入車站的活塞風量大大減小,出入口處的壓力顯著降低。


圖8 不同站臺門型式下出入口處的壓力變化
4 結論及建議
結合實際工程中列車過站條件下列車運行特點及車站實際情況,將卷簾門的型式等效為局部阻力系數,對不同行車速度、不同行車間隔、不同站臺門型式、不同卷簾門型式、不同活塞風井開啟數量及迂回風閥開啟與否工況下,出入口處卷簾門的承壓進行了系統分析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對于典型雙層島式A型車站:
1) 安全門系統閉式運行模式下,出入口處的瞬時壓力最大值與行車速度密切相關,行車速度越大,瞬時壓力值越大,行車速度達到80 km/h時,瞬時壓力值可達252 Pa。
2) 行車速度一定時,加大行車間隔與設置迂回風道對降低出入口處卷簾門的承壓作用不大。
3) 安全門系統閉式運行模式下,加大卷簾門的鏤空率(降低卷簾門的局部阻力系數)能顯著降低卷簾門處的壓力,鏤空型卷簾門所受到的壓力僅為密實型的13%。
4) 出入口設置密實型卷簾門安全門系統,單活塞系統時,卷簾門處的承壓為閉式運行的26%,雙活塞系統為閉式運行的21%,因此,活塞風井開啟能大大降低出入口處卷簾門的瞬時最大壓力。
5) 屏蔽門較安全門能對活塞風起到很好的“屏蔽”作用,減少活塞風對車站的影響,過站運行條件下,出入口處瞬時壓力最大值屏蔽門僅為安全門的24%。
北方地區,尤其是較寒冷地區的冬季,地鐵停運后調度車輛時,建議根據站臺門的型式,調整列車過站時的速度,或采用開式運行模式,減小活塞風壓對地鐵卷簾門等附件的影響,保證地鐵運行時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