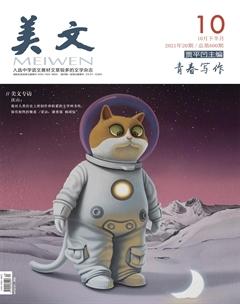泰山崩前色不改 歸悟生命在修心

靳超
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每提及蘇洵,最先映入人們腦海的是他有兩個出色的兒子——蘇軾和蘇轍。殊不知,蘇洵是一位極富雄辯特質的古文大家,并在中國古代散文史上占據獨特的位置。同樣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曾鞏曾評蘇洵文風為“煩能不亂,肆能不流”。文如其人,這也恰好能反映出他心如鼎鎮、志如磐石、寵辱不驚、豁達寬廣的人格特質。蘇洵對于人格修養的觀點莫不體現于《心術》——看似通篇在談兵法謀略,實則暗含著修心、治心之心法真諦。
一、修心之道——歸悟真實的自己
撥開生活的冗蕪,我們需要回歸本真的狀態;遇見真實的自己,我們需要細品心靈的聲音。生活,不僅是一個平凡的詞語,更代表著美好的際遇和程式化的節奏。如果我們在這種固定的節奏中迷失,那么我們將失去遇見自己的機會。因此,我們要跳脫出生活的冗雜,創造體悟心靈的特定環境,在安靜的氛圍、深夜的空寂,抑或于無聲的書籍中歸悟生命的真諦。
修心,一定是每個人體悟生命的必修課。幾千年前,至圣先師孔子曾這樣評價老子:“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連老子這樣道德與天地相匹敵的圣人,尚且借助極高明之言進行修心,更何況是吾輩之凡軀?在蘇洵看來,一位好的將領的行軍用兵之道,莫過于先修煉自己的內心。泰山訇然崩塌,但面容卻不失其色;麋鹿突然奔襲,但目光卻不閃爍。這樣的內心需要修煉,達到“心定”的境界才可至,如此,將領便可權衡利害,滿懷信心地定而待敵,從而無往而不利。
修心之源便是“人性本善”。孟子曾云:“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按照孟子的話來理解,每個人生來便具有良知。只不過內心在人生漫漫旅途中沾染上了蒙塵之蔽,因此,修心便是將心內的蒙塵去除,回歸到清凈、光明的本真狀態。如此便能回歸自身本真的狀態,歸悟真實的自己。
二、治心之術——動與變中的博弈
如果說“道”是上乘的規律與境界,那么“術”便是下乘的技藝與方式。按道理來講,盡管應該以“道”御“術”,但如何做到以“道”御“術”呢?譬如曾國藩在《治心經》中說道“治心之道,先去其毒”,然而如何具體做到“去心中之毒”?蘇洵在《心術》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解決方式,即善用動于變的妙處。
于動態博弈中治心。毋庸置疑,治心之術是指向自己的,但仍然需要與外界的他人產生聯系,需要根據對方的行動、反應做出預判、推斷,而這個過程便是重要的治心之術,即“動”。在文中,蘇洵用一例以蔽之:三國時期魏國名將鄧艾深諳兵法,在伐蜀的過程中,由于了解劉禪疲軟無能的特點,兵行險招,從陰平小道行無人之地七百余里,并且用繩子拴著士兵從山上墜下深谷。如果對方是善于思考,精于謀略的孫權,那么鄧艾絕不會行此險策。換個角度來看,如果劉禪并不昏庸無能,那么行此險棋的魏軍也有可能被捆綁擒獲。總而言之,“治心”是一個博弈的動態過程,需要根據對方的強弱、虛實、反應來衡量自己,從中獲得心之定數。
于逆向通變中治心。以己之長制他人之短,此乃人之常情,亦是常有的邏輯。然而蘇洵反其道而行,提出了在逆向通變中“治心”。他認為,如果僅僅順應正常的行事邏輯,拿出自己的長處去對抗敵人,把自己的短處隱蔽起來,那么如果對方明悉了這樣的心術,不對抗我之長處,竭力對抗我之短處,那么這一制敵之術便失去效能。因此,蘇洵提出了逆向的通變:我方的短處,我故意顯露出來,使敵人心生疑慮而退卻;我方的長處,我暗中隱蔽起來,使敵人輕慢而陷入圈套。雖是御兵之術,但在通變博弈中“治心”卻是一個重要的法門。
三、歸心之境——光明坦途中求放心
修心、治心終將指向“歸心”,意即回歸本原的初心。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在給陸原靜的書信中寫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秉承孟子的人性本善,陽明先生認為回歸本原的心便是達到了“良知”之境。原初的本心不同于徹悟后的良知,在這里需要加以區分。人生轉瞬,白駒過隙,白云蒼狗,生時無來一毫,逝時無帶一絲。本心正如來時的真醇,良知便為去時的返璞。修心、治心便是貫穿在生、逝之間的修煉,而這也即是修心、治心的意義所在。
歸心之境,人生修煉的真實奧義。人們常常反問自己:為何人生不能坦途一片,而會產生如此多的問題、痛苦與糾結;人們也常常叩問自己: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其實,人生正如一輛列車,無非是從一個起點到一個終點的過程,只不過,這個終點最終會和起點重疊恰逢,而沿途曼妙的風景、灰暗的天空都是為了體驗之后的回歸。只有到達了回歸的境界,人生的修煉才能得以圓滿完成!
放心之境,生命體驗的光明時刻。在我們的人生中,生命的體驗感尤為重要,如果這種體驗感是幸福的,那么此刻人生便是幸福的;如果這種體驗感是痛苦的,那么此刻的人生便是痛苦的。然而,人的一生總是交錯著喜怒哀樂,歡喜憂懼。當我們在修心、治心中達到了歸心之境,那么便會迎來一次內心光明的生命體驗。正如王陽明在臨終時留給世人的遺言:“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當生命體驗達到了光明、放心之境,那便意味著所有的喜怒哀樂,歡喜憂懼終將化為拭去之塵土、散去之陰云。這是一種灑然的快感,光明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