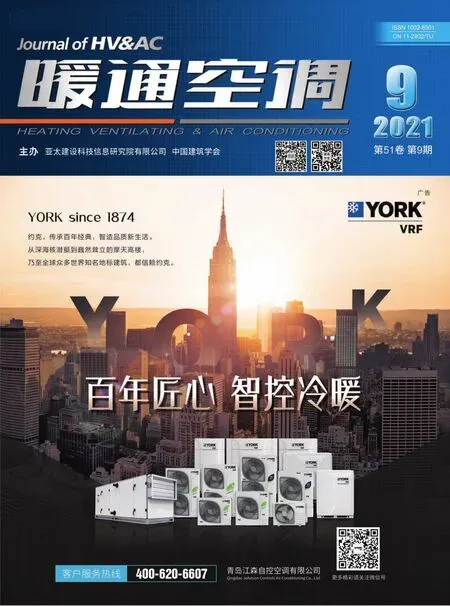地鐵防排煙系統(tǒng)設計理念及方法反思*
中鐵二院工程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劉伊江
0 引言
GB 50016—2006《建筑設計防火規(guī)范》[1]之前,我國的建筑防排煙采用指令性設計體系,按防煙分區(qū)面積乘以相應的排煙量指標計算排煙風量。GB 51251—2017《建筑防煙排煙系統(tǒng)技術標準》[2]部分納入了性能化設計體系的方法,根據(jù)設計火災的規(guī)模及類型,采用相應的煙羽流模型計算產煙量。
2018年頒布的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3]對防排煙系統(tǒng)的設計要求雖然也引入了性能化設計的一些理念,但基本仍采用指令性設計的體系,即仍以指標法計算排煙量。本文試圖從性能化設計的角度對國內地鐵工程防排煙設計進行反思,以期引起業(yè)界對現(xiàn)行一些做法的討論。
1 性能化防火設計理念
在性能化防火設計體系下,需首先確定建筑的幾何參數(shù)及使用情況,確定設計火災場景(包括可燃物種類、數(shù)量,火源功率、位置,煙羽流特征等),設定設計目標,保證人員在火災發(fā)展到威脅人身安全之前到達安全區(qū)域,即人員疏散時間Tev小于危險來臨的時間Tcrit,在可用的逃生時間內維持人員疏散路徑上的逃生條件[4]。逃生條件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與防排煙系統(tǒng)設計目標相關的,則是在設定的設計時長內,通過防排煙系統(tǒng)的運行使逃生路徑上的煙層維持在一定的高度之上,以及控制煙層平均溫度[5-6]。
美國消防協(xié)會(NFPA)發(fā)行的相關規(guī)范及標準基本采用性能化防火設計體系。其中NFPA 92[5]為煙氣控制系統(tǒng)標準,NFPA 204[6]為排煙排熱標準,NFPA 130[7]為軌道客運系統(tǒng)防火標準。
NFPA 92側重于防煙(含自然排煙),規(guī)定了防煙系統(tǒng)在設計時長內須達到的具體設計目標,包括:1) 把煙氣控制在火源所在的分區(qū);2) 在人員撤離建筑所必需的時間內維持樓梯井內的逃生條件;3) 在人員到達安全出口或煙氣避難區(qū)所必需的時間內,維持所有通向安全出口和煙氣避難區(qū)通路上的逃生條件;4) 大空間內煙氣邊界層維持在某一預設的高度[5]。
NFPA 204為排煙排熱系統(tǒng)的標準,規(guī)定了在設計火災工況下,設計時長內排煙系統(tǒng)設計需達到的設計目標,包括:1) 維持煙氣邊界層不低于允許最小清晰高度;2) 維持煙層溫度不高于最高允許溫度[6]。
NFPA 130對軌道交通的事故通風系統(tǒng)提出的具體要求為:1) 為封閉車站或封閉區(qū)間沿火災疏散路徑上提供逃生條件;2) 為封閉區(qū)間提供足以形成臨界風速的空氣流量;3) 能在180 s內達到滿載運行狀態(tài);4) 系統(tǒng)能力按事故狀態(tài)下相鄰風井之間可能出現(xiàn)的最多列車數(shù)考慮;5) 保持要求的風量時長不小于1 h,且不短于要求的逃生時間。逃生條件包括溫度、CO濃度、視距及風速等定量指標,其中溫度及CO濃度2個指標是時間的函數(shù),即具體指標不是定值,而是隨著人員暴露時間變化的,分別見表1及表2[7]。

表1 文獻[7]高溫暴露限值

表2 文獻[7]CO體積分數(shù)暴露限值 10-6
性能化設計體系充分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防排煙系統(tǒng)的設計目標十分清晰,始終聚焦于在一定的設計時長內維持人員逃生路徑上的生存條件[4-7],絕非“為了排煙而排煙”。
2 理論體系
GB 51251—2017《建筑防煙排煙系統(tǒng)技術標準》引用了NFPA 92給出的軸對稱型、陽臺溢出型和窗口溢出型煙羽流模型,此3種煙羽流模型均是基于煙氣在一定功率火源的熱壓作用下向上浮升,至頂棚后沿頂棚水平流動(頂棚射流),煙層的厚度在頂棚下逐漸積聚,因此存在一個煙層界面,該界面下緣至室內地面之間視作可保證人員逃生所必須的無煙氣的清晰高度。隨著煙氣的積聚,煙層厚度加大,煙層界面下沉到人員活動高度的時間即視作一個危險來臨時間Tcrit。防排煙系統(tǒng)設計的目標即是保證在人員撤離所必需的時間Tev之內煙層界面不會下沉至人員活動高度,亦即保證Tcrit>Tev[2,4-6]。
然而,上述3種煙羽流模型均有其適用的幾何、物理條件[5-6],煙氣的基本流動特點均是上升流——水平頂棚射流,因此,這3種模型均不適用地鐵工程中的列車火災場景。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指出,“……基于列車火災規(guī)模……我國目前尚無適合這種情況的排煙量計算公式”,因而介紹了日本提出的計算方法供參考[3]。
日本所采用理論體系與前述NFPA體系的一個明顯不同是,對火災規(guī)模區(qū)分了一般火災和大火源火災,并明確指出,“在一般火災和大火源火災情況下,其火災特性和煙流動特性是不一樣的”。一般火災情況下,站臺層根據(jù)“煙濃度(減光系數(shù))Cs必須低于0.1 m-1”來評估疏散安全性,站廳層則是根據(jù)煙氣擴散容積V必須大于按疏散時間計算出的相應值評估;只有在大火源火災情況下才采用“二層煙模型”“大火源火災時由于煙的溫度很高,在天花板會形成層并按層進行流動,而且煙會隨著它的蓄積而落下”,此種情況下才是根據(jù)煙層下降到有礙疏散的某個高度(2 m)所需時間評估疏散的安全性[8]。換言之,此種理論認為,在一般火災場景下,由于火源熱功率不大,熱壓不足以支撐煙氣與潔凈空氣形成分層,煙氣是充斥著整個空間高度的,正因如此,才采用煙氣的減光系數(shù)Cs或擴散容積V作為評估指標。
需特別指出的是,由于理論基礎完全不同,兩種模型不能兼容。在一般火災情況下,基于稀釋原理,按面積指標法計算防煙分區(qū)的排煙量。由于煙氣不出現(xiàn)分層,排煙目的在于保證整個控制體空間內的煙氣減光系數(shù)[8]。而“二層煙模型”的基本原理則是通過“排煙量≥產煙量”來控制或減緩煙氣分層界面下沉的速度,在必須疏散時間(required safety egress time,RSET)內保證最小清晰高度,并將煙層界面下沉至人員逃生高度的危險來臨時間點之前設定為可用疏散時間(available safety egress time,ASET)[4]。
我國在列車火災基礎理論的研究方面尚有所欠缺。不論是GB 51251—2017《建筑防煙排煙系統(tǒng)技術標準》[2],抑或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3],均采用儲煙倉概念,要求排煙風口設于儲煙倉內且排煙風口底邊距擋煙垂壁下沿的垂直距離不小于0.5 m,則事實上是采用了“二層煙模型”,認為煙氣會因火源的熱壓作用出現(xiàn)分層,煙氣與其下方的潔凈空氣之間會存在一個界面。
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第8.2.4條第2款規(guī)定,當防煙分區(qū)包含軌道區(qū)時,應按列車設計火災規(guī)模計算排煙量,但條文說明中所參考引用的日本列車火災產煙量計算方法卻是采用減光系數(shù)法,即并非基于“二層煙模型”,并且該公式中完全沒有火源功率一項,故而存在內在的邏輯上的矛盾。針對列車火災,我國沒有相應的公式可用于產煙量計算。
3 評價體系
國內各城市軌道交通線路在開通運營之前均需由相關機構進行試運營安全評價,評價依據(jù)為AQ 8007—2013《城市軌道交通試運營前安全評價規(guī)范》[9](以下簡稱《評價規(guī)范》),熱煙測試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評價規(guī)范》表1.2給出了熱煙測試評價的具體指標,其中第一項即為測試站臺、站廳、車站隧道、區(qū)間隧道的溫度場,并要求疏散路徑區(qū)域1.5 m高度以上煙氣層溫度不超過180 ℃;第二項為測試站臺、站廳危險高度平面的溫度,要求疏散路徑區(qū)域1.5 m高度的溫度不超過60 ℃;第三項為站臺、站廳、區(qū)間隧道的煙氣層高度測試,要求不小于1.5 m[9]。此三項測試要求是性能化防火設計理念,并且是基于“二層煙模型”提出的要求。
然而,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3]中防排煙系統(tǒng)相關部分仍基本采用指令性設計體系,設計過程中并未考慮煙層溫度及分層高度等項的控制措施。對這套依據(jù)指令性體系設計出來的系統(tǒng),卻采用性能化的理念進行評價,不盡合理。
4 區(qū)間排煙及中間風井
本著“以人為本”的原則,火災工況下應關注人員疏散路徑上的逃生條件,“排煙”只是達成“人員安全”這一設計目標的措施之一,而不是“目標”本身。換言之,不應該“為了排煙而排煙”。關于地下區(qū)間排煙,現(xiàn)行規(guī)定中有諸多問題值得商榷。
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規(guī)定,“連續(xù)長度大于一列列車長度的地下區(qū)間和全封閉車道”應設排煙設施,另規(guī)定,地下區(qū)間的排煙宜采用縱向通風,正線區(qū)間的通風方向應與乘客疏散方向相反,無載客軌道區(qū)間的通風方向應能使煙氣盡快排至室外。采用縱向通風時,隧道斷面風速不應小于2 m/s。采用縱向通風方式有困難的區(qū)段,例如線路設置配線的大斷面區(qū)域,難以形成2 m/s的斷面風速,第8.3.1條則在條文說明中建議在該區(qū)段采用橫向排煙方式,即設置排煙管道[3]。
首先,這里需深究2種情況:所謂“區(qū)間排煙”,究竟是考慮無列車的隧道結構本身火災,抑或是列車火災停靠在隧道內?隧道結構內,除電纜包覆層外基本沒有可燃物,即便是電纜包覆層發(fā)生火災,其火源功率及產煙量均很小;更重要的是,此種情形下列車不可能主動停車,即此時不可能有人員經(jīng)由隧道行車區(qū)域疏散撤離。關于2 m/s隧道斷面風速,GB 50157—2013《地鐵設計規(guī)范》[10]中給出了明確的解釋,是為了“造成一種氣流使乘客感受到新鮮空氣流動,指示其撤離的方向”。因此,如果不是列車火災,而僅是隧道(電纜)火災,人員不經(jīng)由隧道疏散,要求2 m/s隧道斷面風速意義不大。即便是列車火災情形下,有人員疏散的需求,配線區(qū)段通常已經(jīng)進入了車站范圍,就更不需要“2 m/s風速”來指示疏散方向了。
車站的疏散條件遠優(yōu)于隧道內。若是行駛中的列車發(fā)生火災,原則上均應行駛至前方車站疏散,而絕不應允許列車停靠在區(qū)間隧道。地鐵列車均為動車組,動拖比通常為2∶1或1∶1,且站間距通常不超過5 km,故即使因火災失去了一半的動力,列車仍有足夠的能力運行至前方車站。我國TB 10020—2017《鐵路隧道防災疏散救援工程設計規(guī)范》[11]即采用“定點救援”原則,而不考慮火災列車隨機停靠于區(qū)間隧道的排煙,且僅對長度大于20 km的隧道或隧道群才要求設置緊急救援站,長度小于20 km的隧道則僅要求設置緊急出口或避難所。地鐵系統(tǒng)一直以火災列車隨機停靠于隧道內的任意位置為前提組織縱向通風是不合理的。
其次,即便是啟動機械排煙,也不應選擇排煙方向[12],而應統(tǒng)一順行車方向排煙。這是因為,在活塞效應的作用下,隧道內始終有一定的順行車方向的風速,即使事故列車制動,在相當長的時間(通常約15~20 min)內此縱向風速仍然存在。按列車的制動減速度簡單計算即可知,列車制動時間通常大于60 s,此段時間內煙氣已經(jīng)向前移動了數(shù)百米,若反向排煙,必然造成部分區(qū)段二次過煙。
最后,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要求,若區(qū)間內存在2列或以上列車追蹤運行,排煙時應能使非火災列車處于無煙區(qū)[3]。因前述“區(qū)分車頭、車尾火災,保證多數(shù)人迎風疏散”的原則[12],若某長區(qū)間有多車追蹤運行,前車車尾火災,則需逆行車方向排煙。目前國內的習慣做法是簡單地按高峰小時列車行車間隔計算追蹤列車的距離,區(qū)間隧道長度大于列車追蹤距離時,通過設置中間風井劃分通風區(qū)段,試圖保證每個通風區(qū)段內只有一列車。然而,按行車時間間隔計算列車間距事實上只適用于采用固定閉塞信號系統(tǒng)的線路,而國內新建的城市軌道交通幾乎全部都是采用基于通信的移動閉塞系統(tǒng)(CBTC),列車的追蹤間隔完全是動態(tài)的,可以只有200 m甚至更近。若按上述思路,區(qū)間隧道每200 m就需設置中間風井,這不現(xiàn)實。NFPA 130-2020對事故通風系統(tǒng)的規(guī)定是“系統(tǒng)能力按事故狀態(tài)下相鄰風井之間可能出現(xiàn)的最多列車數(shù)考慮”[7],而不是規(guī)定一個通風區(qū)段內只允許出現(xiàn)一列車,或是規(guī)定后車必須處于無煙區(qū)。
5 列車火災熱釋放率
關于列車火災熱釋放率(heat release rate,HRR),國內地鐵設計界普遍存在一些誤區(qū)。首先,列車火災功率的取值普遍為5.0~7.5 MW,此值最初的起源難以考證。對客運機車車輛的防火性能,有大量的相關標準,如NFPA 130[7]、EN 45545[13]、DIN 5510[14]等,對客運機車車輛的防火、阻燃性能及選用材料的燃燒熱值、產煙量等均提出了嚴苛的要求。城市軌道交通以服務通勤客流為主,車輛內飾選用的可燃材料原本就極少,因此,符合上述任何標準要求的地鐵車輛,即便發(fā)生火災,其熱釋放率基本不可能達到5.0 MW水平。以中車集團為某項目提供的列車為例,基于達根法(Duggan method)計算得出的列車火災900 s內平均熱釋放速率僅為2.8 MW。達根法本身所提供的并不是真實列車火災場景的模擬值,而是基于車內所有可燃物同時被引燃的假設,將各可燃物試樣在錐形量熱儀中的燃燒熱值的實驗數(shù)據(jù)進行平滑處理而得出的。而可燃物事實上是均勻分布在車廂內的,即便發(fā)生火災,初始火源的發(fā)展延燒需要一定的過程,不可能第一時間即引燃全部的可燃物,故達根法所得出的遠非列車實際發(fā)生火災時的熱釋放率,而只是一個不可能達到的“天花板”[15-16]。
另一個認識誤區(qū)是把熱釋放率的峰值取為一個長時間的恒定值。日本對列車大火源火災僅是在3 min內取為5.0 MW,超出3 min時則取為0 MW[8],見表3及圖1。事實上,列車上可燃物的量并不是無限多,根據(jù)質量守恒及能量守恒原理[17],若HRR值高,其可支持燃燒的時間必然較短;反之,若在較長的時間持續(xù)燃燒并產煙,則其HRR值必然較低。將HRR的峰值取為一個長時間內的平臺值(plateau)是不合理的。

表3 文獻[8]中列車火災特性模型


圖1 文獻[8]中列車火災特性模型
最后,還有觀點認為,火災功率與列車車型及編組有關,這也是沒有依據(jù)的。火災熱釋放率僅與可燃物的物理參數(shù)、數(shù)量、空間分布、空氣供應量(燃燒效率)及初始火源的強度等因素有關[17]。A8編組的列車火災功率并不是必然大于B6編組。
6 排煙量計算
如前所述,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第8.2.4條第2款規(guī)定,若防煙分區(qū)包含軌道區(qū)時,應按列車火災規(guī)模計算排煙量[3],但我國尚沒有適用于列車火災場景的產煙量計算模型,因而事實上無法執(zhí)行該條款。
該條第3款規(guī)定,地下站臺的排煙量還應保證站廳到站臺的樓扶梯口部具有不小于1.5 m/s的向下氣流[3]。此條文的本意是防止大量煙氣浮升侵入站廳層。但是,若火源功率較小,難以支撐煙氣分層(即按煙氣減光系數(shù)法或擴散容積法計算時),煙氣本身的浮升動力不大,此1.5 m/s向下風速的要求顯得并不必要;如果火源功率大到足以使煙氣出現(xiàn)明顯分層,樓扶梯口部的向下風速的確很有必要,但由于地下車站的空間特點,站臺層排煙時,樓扶梯口部天然地成為“補風口”,而此補風口又天然地與儲煙倉處于大致相當?shù)母叨龋蛳嘛L速稍大即可能對煙層形成明顯擾動因而破壞分層。因此,若能利用局部誘導射流或其他手段形成有效的向下壓制氣流,則不一定靠無限加大站臺層“排”煙風量來實現(xiàn)站廳層的“防”煙效果。
7 通道排煙
GB 50157—2013《地鐵設計規(guī)范》[10]及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3]均規(guī)定,連續(xù)長度大于60 m的地下出入口通道應設機械排煙設施,且同時又均規(guī)定:站廳公共區(qū)任一點距疏散通道口的距離不得大于50 m。
出入口通道作為安全疏散通道,其與站廳公共區(qū)相交的點既然被作為疏散距離計算的基準點(目標點),則該點即應視為安全點[3],出入口通道內應該確保不會出現(xiàn)大量煙氣,否則該通道不得作為疏散路徑使用。因此,出入口通道應該做“防煙”而不是“排煙”。
若是該通道本身發(fā)生火災,按“一處火災”的設計原則,站內乘客也不可能選擇該條通道向外疏散。而前述標準[3]的安全疏散章節(jié)中對于長通道內安全出口的設置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可保證長通道內的疏散距離不大于50 m,故長通道本身火災的情形下事實上也沒有設置機械排煙的必要。
8 關于煙氣蔓延
GB 51298—2018《地鐵設計防火標準》第8.1.3條規(guī)定[3],對站廳公共區(qū)排煙時,應能防止煙氣進入出入口通道、換乘通道、站臺;對站臺公共區(qū)排煙時,應能防止煙氣進入站廳、地下區(qū)間、換乘通道;對地下區(qū)間縱向控煙時,應能防止煙氣進入相鄰車站、相鄰區(qū)間。
對某一區(qū)域排煙,防止煙氣大量蔓延至鄰近區(qū)域的要求本身是合理的,但對此不應過于絕對、僵化地理解和執(zhí)行,而是應該給出定量的標準。火災情況下,任何設計方案都無法絕對保證相鄰的非事故區(qū)域沒有“一丁點”煙氣。按“一處火災”的基本設計原則,不論相鄰區(qū)域是否位于事故區(qū)的疏散路徑上,即使有少量煙氣蔓延,只要不影響相鄰區(qū)域的逃生條件(視距、溫度、CO濃度)[7],應該是可以接受的。若相鄰區(qū)域不在服務于事故區(qū)的疏散路徑上且本身又是無人區(qū),可接受的蔓延程度則更可以放寬。
9 結語
傳統(tǒng)的指令性設計方法簡單明了,易于執(zhí)行,但對具體的火災場景針對性不強。由指令性設計向性能化設計轉變,是一大進步。但是,建筑防火的性能化設計應建立在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之上,且必須有性能規(guī)范、技術指南及評估模型3個要素支撐,因此不應割裂開來僅使用其中的部分理念或方法。
我國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地鐵火災疏散救援的理論體系,只能借鑒國外相關經(jīng)驗。不論是美國NFPA體系,還是日本體系,也許都未必盡善盡美,但至少能各自形成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然而,這2套體系相互間未必“兼容”,同時借鑒2種體系中的部分做法,必然造成諸多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