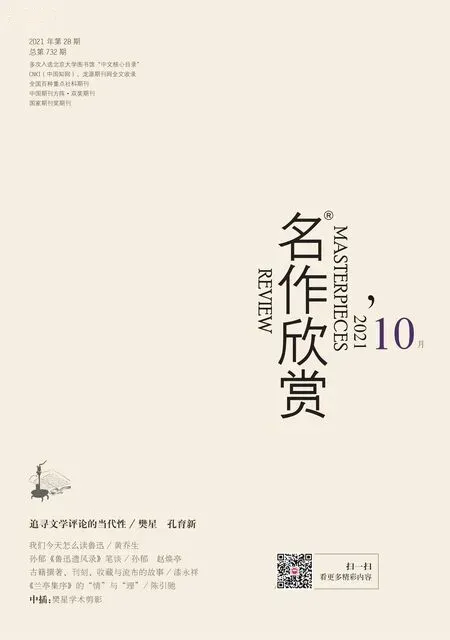余秀華詩歌論
上海 葛紅兵 艾曉丹 河南 郭玉紅
余秀華以殘疾農民的身份出場而成為一個現象級的詩人,其詩作為她“搖搖擺擺的人生中的拐杖”反而倒成了配角:她的詩歌因這身體的某種出場及出場姿態,而被稱為“蕩婦體”,在一系列關于余秀華的評論和論爭中,似乎她的殘疾“身體”的本尊出場才是“文壇”主角。在余秀華的世界里,女人、農民、詩人,是她自認的三個身份,而且,這個身份的自認,是有順序的——首先是女人,她說,她首先是個“女人”,這構成了她的自我指認,一種帶“性別”的身體性指認。大眾評論者指責她的詩:(1)“骯臟惡心”;(2)沒文化,營養不良,“包括了標點、分行、空格”。“女人”的帶著性別的詩,它是“骯臟”的嗎?這是一個問題。“農民”的帶著底層身份的詩,它就必然是“營養不良”的嗎?這也是一個問題。
相比較于影視類視頻藝術,文學,包括網絡文學和紙面文學(純文學),已經不是當代藝術的“紅款”主流樣式,純文學創作更是如此。近年“爆紅”的網絡作家少之又少,而純文學作家幾乎沒有,更不要說,余秀華是個詩人,詩歌是文學創作的小眾領域,是一個在相對小且比較封閉的文化圈層內發生影響的創作樣式。在這個小的文化圈層內,“讓大家都知道”是比較容易的,“爆紅”很難,社會化“爆紅”更難,余秀華的爆紅不是詩歌創作本身的爆紅,而是余秀華詩歌創作作為一個“事件”的爆紅。筆者認為這個“事件”背后包含了兩個可討論的方向:第一,“農民詩人”的作者身份問題,第二,“蕩婦體”詩歌與中國傳統詩教傳統的反思問題,而其背后的根本問題是:中國文論缺乏解釋能力,中國寫作學沒有完成現代創意寫作學轉型的理論貧困問題。
上篇:誰擁有寫作的權能?誰可以成為作家?
20 世紀以來,中國文壇經歷了數次左翼運動,從“五四”時期開始,文學家們逐步形成了反思自己的“知識分子”文化身份,向大眾文化身份看齊、向底層普羅大眾階級立場看齊的傾向。在魯迅的筆下,知識分子作家的道德情操并不比人力車夫高,知識分子作家在“人力車夫”面前,常常能見到自己靈魂深處的“小”來;而在胡適、周作人等眼里,這種道德身份的傾斜,進一步地被發展成了“語言”身份的傾斜,引經據典的文言文“語言身份”應該向底層的“白話”身份傾斜。文學在語言上原先的高下邏輯被顛倒了過來,底層的語言是高的,而原先文化高層的語言則是低的。
余秀華顯然知道自己的社會文化身份,她甚至能把這種社會文化身份發揮到極致,把底層并弱勢者的文化階層身份(包括農民的社會底層身份和殘疾人的弱勢群體身份)和她鐘情的“女人”性別文化身份的邏輯結合起來加以突出,她的“色解唐詩”語言脫口秀就是這一背景下的行為藝術——余秀華對文化經典的“色情化”解讀,顯示了她對自己的“文化”底層身份的認同與故意放大。這種放大獲得了專業知識分子界某種意義上的認可,有學者在論述余秀華詩歌時這樣寫道:“只有當底層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時候,才會有真正的底層。”還有有些學者甚至從民粹主義出發,認為在“一切底層之外和從底層出身但已經擺脫了底層的人都喪失了表述底層的能力,因為被表述意味著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層來證明不屬于底層的東西,或將底層引入誤區”的意義上強調底層寫作的意義,這就把余秀華當成了極少數“已經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代表了。
但是,這種身份指認進而從其社會身份來論證其詩歌價值的做法,在普通網民那里是不被認可的,網文《余秀華一個極具爭議的女人,究竟是詩人,還是文化流氓》中,作者借一般網民的口說:“看她這個長相,就倒胃口”,“難道,社會的發展進步,是靠這樣的人、庸俗語言、齷齪思想推動的嗎?”“歪解經典作品,其實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認可,何況還是帶有色情色彩的解構,就更加褻瀆了文化。”該網民認為評論圈、詩歌圈為余秀華開道和鳴鑼,完全是一場無底線的炒作,認定余秀華的創作“爆紅”完全是文壇丑聞。此種言論所針對的問題,具體到余秀華個人及其創作上,顯示的是一種彼此抵牾的邏輯:專業知識分子界認為余秀華代表了甚至是在非常純粹的意義上代表了底層和弱勢的“發聲”及“發聲能力”,而大眾網民觀點卻恰恰相反,他們要求詩人必須擁有并且恪守文化的“高端”“精英”身份。在大眾網民看來,余秀華的底層、弱勢者身份及其姿態反而構成了她的欠缺——她褻瀆了詩歌和詩人的文化屬性,是一個文壇笑話。
文化界的平民主義/民粹主義指向是20 世紀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壇的一個“道統”,本來,這個道統代表了文壇與底層的謀合,應該得到大眾網民的認同才是;但是,事實正好相反:詩歌界的專業人士,包括作者和評論家,更多地對余秀華表示了贊賞,而大眾網民卻認真地扛起了價值“批判”的大旗。
其實,歷史上,在文學史及文學理論領域,多數時候精英主義是占上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領域,文學史家們對“一門三蘇”(宋代蘇洵晚成而為文壇“大器”,其子蘇軾、蘇轍則似乎更上層樓)現象的濃墨重彩、對“咸陽三班”(班彪為東漢首屈一指的文、史大家,他的兩子女班固、班昭似乎直接繼承了他的如椽巨筆)等現象的津津樂道,都隱含著“龍生龍、鳳生鳳”的精英主義氣息。中國古代詩人和文論家中從不缺乏對創作天賦和天啟的論述,南宋詩人陸游的《文章》一詩就寫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對于陸游來說,文章首先必須來自“天成”,其次是“妙手”得之,何謂“妙手”?“有天賦的人”之謂爾。中國古代文論的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龍》把文才看作是天賦的結果,“文才具有稟賦性,其屬于性靈層面的才情個性、內在直覺體驗和感悟能力等都是來源天賦”。
中國古代文論中的作家才華問題討論以“才性論”為核心,以“才德論”為輔助。“才性”是先天的,從孟子的“性善說”到王充的“氣壽天命說”,無論在孟子那里還是在王充那里,“才性”都是先天的,后天只能“養”(氣),而不能“生”(氣)。才性如果天生,那么后天的人又如何作為呢?“德”是可以后天通過實踐來生成的,后天的才德可以部分彌補先天的才性,理想的狀態是“性”“德”俱美,但,如果達不到理想狀態,才德“粗”而才性“精”也是可以接受的(東晉葛洪)。
在多數專業評論家的眼里,余秀華是擁有天賦才情的天生詩人,他們熱衷于“以詩人的文本為據,解析她對農村自然意象的詩意審美、女性欲望的表露以及身體殘疾且掙扎在底層的痛苦感受;梳理其創作心理”。一位論者這樣寫道:“在自然美學的視域下解讀詩人之詩”,她的詩具有“深蘊的悲劇美感”。另一位論者評論道:“她的詩歌在對立的狀態中相互抗衡、沖擊、比較、映襯,同時在意義上又形成平衡的整體,產了立體的審美感受。”在這些專業評論家的眼里,余秀華的詩無疑是極有才情的,她的“‘個人化’‘日常主義’‘及物’的詩學主張”,使她得以“脫離了‘意識形態’話語的束縛,追尋更加獨立自由的創作方式”。在專業評論者的眼里,她的寫作的動能只來源于自然和生命本身,她在生命與自然之間保持了和諧而又沖突的張力關系,因而她的詩作充滿了文化詩學意義上的批判性和生命本體意義上的啟示性,這種詩歌是可以進行文化詩學意義上的解讀的。一句話,余秀華無疑擁有從事詩歌創作的特權和創作出優秀詩歌的權能。
而在網民討論者的眼里,余秀華則并不擁有成為詩人和寫出優秀詩歌的天賦,余秀華之所以成為“詩人”而且“著名”,僅僅是因為她是文壇炒作的“丑聞”,“蕩婦體”的問題,不是“是不是好詩”的問題,而是“是不是詩”的問題。在網民論者看來,余秀華的詩,是“‘蕩婦’體到底有多‘水’,又到底有多‘臟’呢?”的問題,余秀華根本就夠不上一個詩人的稱號,其所謂詩作也構不成是什么詩歌。
其實,在這里,專業評論者和網民評論者他們分享的是一個邏輯,他們都認為“寫詩需要天賦才情”,專業評論者認為余秀華擁有天賦才情(進而認為這種才情和她的底層和弱勢者的文化身份是同一的),而網民評論者則認為余秀華沒有天賦才情,她只是利用了她的底層身份,放大了她的弱勢者處境。雙方的根本分歧在于余秀華是否具有天賦才情,進而在于她是否擁有創作優秀詩歌的權柄問題上,他們之間無法互相說服。
這顯示的是文論的貧困,中國文論的歷史并沒有真正發展出一種科學的理性的對于詩歌才情能力的解釋、闡釋理論,因而不要說是圈外讀者,即使是最專業的詩歌評論家,對詩人、詩歌的評論與闡釋都是蒼白而沒有說服力的。對于當代詩評家來說,用余秀華的底層、弱勢身份說話,把她的詩人才情牽強附會于她的社會底層身份(這是當代左翼文論經常犯的錯誤之一)甚至殘疾的生理身份上,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而這種不得已的選擇顯示的是理論的貧困。
前文說到文論上的“精英主義”和“平民主義”分野,盡管精英主義文論占據著古典文論的主流,但平民主義也不是沒有進展。20 世紀以來,平民主義文論一直在向著主流上升,但是,在現代創意寫作學出現之前,“平民主義”文論往往無法克服其內在欠缺,其論述過于依賴作者的社會性“身份”,其觀點往往無法克服地最終導致民粹主義。20 世紀初期,在西方,隨著古典文獻學和語言學的衰落,伴隨著文學創作、閱讀的平民化,西方文學教育由古典文獻學、語言修辭學向現代創意寫作轉型,逐漸地西方文論發展出了“人人能寫作”的平民主義創意寫作學理論。但是,筆者在這里更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現代創意寫作學意義上的平民主義創作理論,不是依靠“天賦才情論”“階層生活論”(在這一點上,平民和精英主義的傳統文論其實是沒有區別的),現代創意寫作學解決“誰有寫作權”的問題,解放寫作權給全體大眾,讓文學寫作適應現代社會市場化、平民化的趨勢,將“創造”由上帝的權柄而轉手于人,進而是普通的人——但是,它不是將寫作的權柄奠基于人的天賦才情,它的“人人能寫作”的立論基石是“寫作能力可以被培養”,這是現代創意寫作學思想的偉大成就。遺憾的是,創意寫作學在中國遲來了一百年,無論從其引進的力度來看,還是從其中國化發展的進程來看,中國創意寫作學在這一點上,還任重道遠。
在創意寫作學看來,“創意寫作人人可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有表達的愿望”。“文學創作有規律可探,有路徑可循。作家可以培養,靈感可以激發。”靈感不是來自天啟和神性,而是來自“激發”,創作不是來自天賦才情,而是可以來自后天能力“培養”,“激發普通人的創作自信,在工作生活歷練之后重新拾起文學的夢想。”在創意寫作學看來,“作家是否有天賦才情?”的問題是一個偽問題,創意寫作學堅持“創作人人可為而不必依賴天賦才情”,在創意寫作學看來,天賦才情對于寫作來說,不是必要條件,創意寫作學反對用天賦才情把人分成“能寫作者”“不能寫作者”的做法,相反認為這種做法違反了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關于“平等”的基本信條。創意寫作學把上述前現代問題轉向為“創意寫作能力的后天培養和靈感的后天激發如何進行”的問題,它以自己的學科理論也以自己的學科教學實踐來回答“普通人如何擁有創作自信”“拾起文學的夢想”的問題。如果對余秀華詩人身份的討論在這一方向上進行,我們也是可以得到共識的,其文論史意義也是可以看到的,但專業評論界的理論慵懶和網民討論的情緒極端化妨礙了這一討論的深入。
下篇:什么內容能進入創作?審丑何以需要承擔偏見?
文學是“審美”的事體,但是,對美的看法,卻無往而不在“爭論”之中。

但是,不符合古典詩學關于美的律法,卻不一定不符合現代詩學關于美的定義。
在現代美學看來,古典美學對于永恒美的頌揚,隱含著的不僅僅不是人類的偉岸,相反是人類的荏弱。在古典美學時代,人類恰恰是沒有勇氣直視和逼問自己的欠缺者、短暫者、罪孽者身份和必死者命運的,人類恰恰是在這個過程中沉醉于虛幻的神性,而失去了不依賴神性的慰安獨對殘缺人性的能力。由此出發,丑進入現代美學視野,成為現代審美的合法“內容”,也因此,人類發展出了審丑的能力,“藝術丑”登堂入室。“不僅最杰出的詩歌都在公開表現丑,而且這還成了現代詩歌的指導原則”,何以如此?在這一向度上,阿多諾的理論闡釋最有說服力,他意識到:“傳統上把丑視為美的否定的定義根本無法解釋現代藝術中丑強有力的呈現,因為一個形式的定義雖能最大限度地認可諸如此類的現象,但卻無法評估它們的起源和合法性。而他關注的中心恰恰是丑的合法性。”“在他看來,美和丑都是歷史的產物,都源于人類最初的恐懼,古風時期的丑‘是對恐怖的實體性模仿’,當主體聲明恐懼的對象不再令人恐懼之時,美就產生了,而當自由的主體開始模仿恐怖的對象,并在模仿中否定了丑時,便形成了美的藝術。美和丑既非實存的,亦非相對的,‘它們雙方的真正關系是以階段的形式展示自身,這期間一方經常是另一方的否定’。”由此,阿多諾認定:“現代主義藝術熱衷于表現丑是歷史的必然,有其否定的使命。用阿多諾的話說,這是一個悲苦的社會,而理性‘沒有對付苦難的能力’,但丑卻有巨大的否定的力量,‘藝術務必利用丑的東西,借以痛斥這個世界’。”
對審丑進行美學理論上的論證,并不能給余秀華具體的詩作提供好或者壞的證詞。如果說,本文上篇包含著余秀華“作為底層和弱勢者而擁有成為詩人的合法性”論證,那么下篇,本文則試圖論證,余秀華有權利將她認定的意象——即使是丑的意象——寫入詩歌,這是一個現代詩人的詩性權柄(有些論者把它歸結為女權主義寫作的詩歌政治倫理問題,而筆者則將之歸結為“審丑是否可能”的現代寫作美學問題)。對審丑進行藝術理論上的論證,并不能直接處理“什么具體內容能合法進入詩歌”“什么具體內容不能合法進入詩歌”的具體判斷,美學上的理論說明無須像政治審查一樣,產生刀削斧砍的效果,然而,我們依然要對此做一個延伸,我們要延伸到一個寫作學的問題:什么是可以寫的,什么是不可以寫的?
長期以來,我們傳統的寫作學和美學的發展并不同步,現代美學已經以其無與倫比的理論說服力闡明了審丑的合法性,但是,傳統寫作學卻似乎依然存活在虛幻的“前現代”空間里。多數時候,在大多數學者和教師的意識里,它依然堅守著古典美學的傳統觀點,它把美和丑對立,把丑當作美的對立面,反對丑進入審美,而不是把丑當作美的否定面,當作“美—丑—美”否定之否定過程的必然階段來認識。
網友們對余秀華詩歌的厭惡實際上來源于這種傳統寫作學誤導。這種誤導的中介應該是傳統寫作學觀念統攝下的中小學寫作教學,這種誤導不僅僅表現在“拒斥丑進入寫作內容”的觀念影響上(許多孩子不敢寫丑,甚至不敢寫所謂的稍稍的“負面”“陰暗”的東西,怕拿不到好的分數),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傳統寫作學的訓練手段上,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傳統寫作學把寫作訓練聚焦于選詞煉句及章節架構,而不是創意思維(學生被要求大量背誦美詞佳句或者弘揚古典美的佳作,所有的典范作品都是以古典美的標準篩選出來的),這種形式訓練使得學生不由自主地產生了唯“美”是瞻的形式意識——傳統寫作學讓寫作形式本身就變得無法容納“丑”。
現代創意寫作學堅持寫作以創意思維訓練而不是形式訓練為核心,強調寫作是教孩子學會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在自己的身上發現真實,在周遭的環境中探究真相,現代創意寫作學把“說真話”“說自己的話”看作是第一位的,它把“說真話”“說自己的話”當作訓練方法也當作訓練目標。在現代創意寫作學看來,“真”是進入寫作內容的唯一門票,在這一點上,它和現代美學給予“審丑”以合法性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它反對人為拔高“思想”,也反對假大空的“辭藻”(這是很多學生作文說假話的原因)。筆者曾經這樣總結創意寫作的基本觀念:第一,個體性。“創意寫作首要出發點是培養個體性的人,它要求寫作者能獨立地而不是盲從于權威地進行思考,不人云亦云而是依靠自主判斷。第二,感受性。創意寫作教育教學思想的重要原則是要求寫作者把寫作建立在自己的個體感受之上,相信自己的個體感受是一切觀念判斷的前提,要求寫作者相信事物的內在隱秘,其真理和真相就隱藏在這些感受里,創意寫作不是主題先行的寫作、不是倫理性的寫作,而是讓寫作者忠于個體感性的寫作。第三,交流性。創意寫作學的基本歸結點是交流性,形成“讀者閱讀”的思維,形成寫作必須達成“傳達效果”意識。第四,創意性。創意寫作是從人的本體意義上來強調創意性的,創意寫作在根本上把人的本質看作是創造性地實踐著的人,把寫作提高到人的根本性實踐活動來看待,把寫作當作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實踐活動。在這一點上,創意寫作強調人人會寫作,是說,寫作是由人的生命的創意實踐本質決定的,它本源性地就是創造性的。現代創意寫作學以“個體”“唯真”來消解美、丑的對立,消解古典美學的局限,讓寫作更加貼近真實,這一點中國當代文論不可不察,當下的中國寫作學亟需一場自我革新,讓其從對古典美的單一崇拜中解放出來,走向以“個體”“唯真”為核心的現代創意寫作學。
余秀華的詩在專業評論者和大眾網民間造成輿論割裂,其誘因是多方面的,有當下社會的確存在的“身份”割裂、“階層”對峙的問題,更有當下的專業詩歌評論工作者缺乏理論武器,沒有理論工具來有說服力地評論和闡釋詩人及其詩歌創作的是基于天賦才情還是基于后天訓練的問題,拿底層身份說事兒,其實顯示的是當代中國寫作學沒有完成現代創意寫作學的轉型,導致大眾對普通人寫作者身份的不認可及寫作內容中審丑的合法性缺乏認知的問題。大眾及專業評論者在余秀華詩歌創作問題上的分歧,顯示的是中國文學理論的貧乏以及寫作學的貧困,中國需要一場由傳統寫作學而現代創意寫作學的寫作學革命。
①余秀華《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其實,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無非是/兩具肉體碰撞的力”。
②④《余秀華一個極具爭議的女人,究竟是詩人,還是文化流氓》(2020 年12 月22 日)的一篇匿名網文這樣寫道:“余秀華與詩友們交流的時候,色解唐詩《登鸛雀樓》,詩詞原文: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余秀華說:白日依山近,不就是白白地日嗎……并且公開發表她色解的內容,引起了輿論的嘩然。”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 6765098388905435&wfr=spider&for=pc(2021 年3月16 日)。
③孫桂榮:《鄉土中國的表述與被表述——農村婦女“在地”寫作與重建鄉土敘事倫理》,《當代作家評論》2020 年第1 期,
⑤孫健風:《〈文心雕龍〉“文才”思想研究》,南京師范大學2019 年碩士論文。
⑥陳小琳:《溫情的憂傷——余秀華詩歌再解讀》,《淮陰工學院學報》2020 年第6 期。
⑦周霞:《余秀華詩歌的審美張力》,《北方文學》2020 年第23 期。
⑧劉川鄂,汪亞琴:《以疼痛抵達心靈的“直覺”書寫——余秀華詩歌的藝術特質與價值辨析》,《南方文壇》2019 年第5 期。
⑨張祖群:《余秀華蕩婦體詩的一種“文化詩學”解讀》,《世界文學評論(高教版)》2016 年第1 期。
⑩ 這種情況其實不僅僅發生在詩歌界,也發生在小說界,小說理論界也始終沒有發展出一種科學的理性的解釋手段,來解釋和闡釋小說現象,筆者曾經帶隊進行小說類型理論研究,試圖通過將小說理論類型化而讓小說在解釋具體作品時更有效力。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筆者主編的“中國現代小說類型理論與批評叢書”(上海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
? 本來這種分野是在知識分子階層內部進行的,如今,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大眾參與文化問題討論范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深,我們看到,大眾常常持“精英主義”立場,而知識分子常常反而持“平民主義”立場,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曾經有過兩次重大的“平民主義”文論勃興,一是“五四”時期以胡適、周作人等為代表的文學革命論的興起,“五四”先賢以此解決了文學怎么寫和寫給誰看的問題;二是20 世紀中葉革命現實主義創作論的興起,曾經一度有“深入生活論”“專業作家和勞動大眾結合論”等深度討論和實踐嘗試。
? 刁克利:《作家可以培養,寫作人人可為》,《光明日報》2011 年11 月23 日14 版。
? 張法:《作為藝理基礎和核心的美學》,《藝術學研究》2020 年第3 期。
?? 潘道正:《丑學的三副面孔及其真容——從現代藝術到后現代藝術》,《文藝研究》2020 年第12 期。
?Friedrich Schlegel:On the Study of Greek Poetry,trans.Stuart Barnett,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p.18.
? 請參閱筆者《創意寫作問題三論》: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511/c404033-317039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