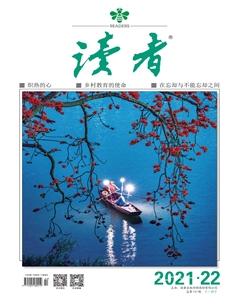姥姥的房間

陳沖姥姥史伊凡年輕時
姥姥冒著風險在閣樓保留了一只棕色的小皮箱,里面藏著她最喜歡的書。我第一次看皮箱里的“禁書”是在扁桃體手術之后。那時盛行割扁桃體,用一種新的方法,不打麻藥不用開刀,只用一塊壓舌板和一把特殊的鉗子就能將扁桃體摘除。母親告訴我,手術后醫院會給病人送冰激凌,聽她的語氣,這簡直是一項特權,因此我立刻同意去割扁桃體。手術結束后,護士把一小紙盒“紫雪糕”和一個小木勺遞到我手里,我卻疼得什么都不能吞咽。母親叫了一輛三輪車,我倚在她懷里,一路上眼巴巴地看著冰激凌一點點融化。回到家,我把化掉的“紫雪糕”給了哥哥。
姥姥看我可憐,去閣樓把那只皮箱拿了下來,從里面取出一本《哈姆雷特》的連環畫給我看。接著,我休了兩天病假,一遍遍地看那本連環畫,那是由英國演員勞倫斯·奧利弗飾演哈姆雷特的劇照組編成的。我被“哈姆雷特”眼睛里傳遞出來的瘋狂和痛苦深深吸引。劇中暴力和仁慈的共存、罪惡和恩典的交融,啟蒙了我潛意識里對人性的認知。
那次手術以后,我時刻期待著感冒發燒不能上學的日子,好讓書本領我走進自己內心世界那些陌生的角落。至今若有人提起契訶夫、狄更斯或者勃朗特,都會讓我聯想起發燒譫妄的感覺,而躺在床上讀書,仍具有治愈一切的魔力。
記得有一段時期,姥姥被停職停薪,她就干脆帶我坐火車出外旅行。那個年代沒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至今我都不知道她是從哪里弄來的錢,怎么拿到的介紹信,以什么理由為我請假的。那年我的語文課本里有一篇寫南京長江大橋的課文,當火車開過大橋的那一刻,我非常興奮和驕傲——不只因為橋很壯觀,而且因為全校只有我親眼見過它。在南京的時候,姥姥帶我去了一棟老房子,探望一位故人,她們兩個人低聲聊到深夜。那一晚我睡睡醒醒,直到曚昽的晨光從窗簾縫里鉆進來,我聽到她們仍然在竊竊私語。現在回想起來,那幽暗的光線、喃喃的低語如夢如幻。那時我還不知道,這座城市有姥姥的青春和曾經的夢想,也還不懂得她走在鼓樓區大街小巷中的悵惘。
旅途中,姥姥給我補習功課。我喜歡語文,讀了不少寫董存瑞、黃繼光、劉胡蘭英雄事跡的書,并抄寫了很多豪言壯語。我給姥姥看我的筆記本,還請她看到好的豪言壯語就幫我記錄下來。那時候的作文開頭都有一些豪言壯語。姥姥跟我說,你不需要寫這些豪言壯語,用一個字可以講清楚的事,不要用兩個字。
姥姥在她的房間時,經常有年輕人上門找她補習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閑聊。從英國回來的時候,她帶了一個手搖唱片機和教英語的唱片及課本,喜歡英語的人聚在她的房間里聽唱片,學講純正的英語。記得一個住在外交大樓里的男青年,常來陪姥姥聊天,讓姥姥給他看閣樓上的舊物,后來姥姥把一盒子我曾外祖父史蟄夫刻的圖章都送給了他。可惜那時我太小,還不懂得珍惜祖上留下的舊物,沒有阻止姥姥這樣做。
1977年,我主演了謝晉導演的《青春》。1979年,我因電影《小花》獲得百花獎最佳女主角獎。經常有男士上門想認識我,姥姥說,我們既不能得罪他們,也不能讓我出面。我總是躲在父母房間里看書,而姥姥在隔壁倒茶、遞煙,冬天點上炭爐,夏天遞把扇子,天南地北地跟人聊,頗有《天方夜譚》中舍赫拉查德的味道。來的人雖然不能滿足初衷,走時也不覺太失望,有的干脆忘記了初衷,日后還帶著禮物回來看她,與她成了忘年交。
我的朋友們也都喜歡她,前兩天我跟一個多年沒聯系的老同學通電話,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姥姥。他回憶道,在他人生不順利之時,姥姥手里拿根煙,笑瞇瞇地對他說:“小朋友,軍棋下下。”姥姥跟他講的是上海話,她的意思是人生一盤棋,有輸有贏。朋友還記得姥姥說:“棋子木頭做,輸了再來過。”
我留學美國的第四年,終于可以回家探親,別人從美國回家,總要帶一臺電視機或冰箱什么的,買那些所謂的“四大件”。我在信里問姥姥要買什么,她堅持不要任何大件,也許是不舍得我花錢,也許是真的對大件沒興趣。她讓我買一件有波浪的假發套、一件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筆和一塊羊奶芝士。當我把禮物一件件遞到姥姥手上的時候,她笑得眼睛瞇起來,好像所有的愿望都得到了滿足。也許沒有人能滿意地說出幸福的定義,但是,在那個冬日的下午,陽光從窗外照進來,火爐上燒著水,姥姥換了內衣,戴上發套,描好眉毛,就著蘇打餅干吃芝士的樣子,無疑就是幸福的樣子。
回頭看,姥姥雖然沒有太多物欲,但是她非常懂得享受。有一個朋友知道我在寫姥姥的故事,從網上幫我買了一本姥姥在20世紀50年代編的《吃的科學》。在第一章《怎樣吃飯》里,姥姥首先強調了享受:“我們的眼睛會看電影,耳朵會聽音樂,這些都是享受啊!為什么對好看、好聞又好吃的食品,竟不能欣賞一陣呢?”然后她又解釋:“如果他不帶著欣賞的態度來享受食物,那么他的口水就減少了分泌,胃液也減少了分泌……食物也因為不能充分和消化液接觸,而難以消化。”在姥姥看來,人不需要太多的東西,要懂得欣賞眼前的生活。

陳沖與姥姥史伊凡
我最后一次見姥姥,她已經患了胰頭癌。我陪她到醫院做檢查,其中一部分的過程很痛苦,而且缺乏尊嚴。姥姥多次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無力地安慰她說:“快查完了。”她拉住我的手,堅決地跟我說:“你讓他們停下來。”我沒能讓他們停下來。
檢查結束后,醫生說她得馬上住院開刀。黃昏,我跟姥姥回家拿生活用品,她呆立在房間的中央,似乎不知所措。我把她的牙刷、杯子和毛巾放在一個小臉盆里,再從抽屜里取出替換的內衣。我說我們走吧,她不動;我輕輕拽她,她說再想想還有什么東西忘記拿了。姥姥的房間很簡單,沒有一件多余的物件或裝飾,只有外公的遺像掛在掛鏡線下。光線漸暗,我催她說:“忘了什么我再回來幫你拿。”她還是不動,瘦弱的身體好像一幅剪影。那時我太年輕,哪里想得到,她不想忘記的東西,不是我可以替她帶去醫院的。她曾經在這里成家,在這里哺乳,在這里心碎,在這里療傷,在這里創作。她也曾經被關在這間房的門外,像一頭母獅一樣憤怒地徘徊和咆哮。
我非常喜歡弗吉尼亞·伍爾夫寫的一篇關于女性與小說的演講稿——《一間自己的房間》。姥姥的房間,讓我想到那篇文章里所講的房間,那是她可以關起門來天馬行空、自由自在的世界。
住院當晚,姥姥就動員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護士們只好把她的鞋藏起來。手術后,姥姥再也沒有恢復清醒,兩個月后就去世了。她死后的半年里,我幾乎每晚都夢見她。夢境總是那么生動,好像她還活著。
(海底飛花摘自《上海文學》2021年第9期,本刊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