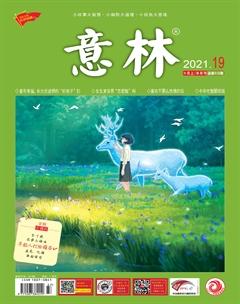分寸感
陳魯豫
有一天,我一個人從香港回京,沒有化妝、頭發蓬亂、戴著帽子,一路推著行李車低頭狂走。靠近出口的時候,我前面一個同樣推車的短發女生很不高興地轉身沖我嚷嚷:“你能慢點推嗎?你撞到我了!”我當時窘迫地愣在那兒,連忙道歉。那個女孩根本沒正眼看我,只是特不高興地沖我的方向翻了好幾個白眼,推車就走了。我漲紅了臉,心里一片愧疚。
其實多大點事啊,我居然臉紅心跳了半天。因為它觸及了我生活中的某個底線,關于邊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邊界,任何時候都保持分寸感。這是我為人的方式,也是我和這個世界發生交集時的生存法則,它讓我覺得安全、得體、愉悅。
2018年2月的《名利場》雜志,一篇署名莫尼卡·萊溫斯基的文章讓我唏噓不已,甚至有些震驚。萊溫斯基這個名字熟吧?文章開頭第一句話:我怎么認識這個人的?我在哪兒見過他?那個戴帽子的男人看起來特面熟。讀到后來,我才意識到這句話的分量——因為這個男人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幾乎一手毀了萊溫斯基和克林頓總統任期的肯尼思·斯塔爾。
換作是我,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我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做出過激的事,但我一定不會像萊溫斯基那樣,過去和他握手,還耐心地聽那個一手摧毀了自己的人不斷地詢問“你好嗎”。我好不好關你什么事?萊溫斯基居然淡定有禮地說:“我真希望當年的我做了其他選擇,當然,希望你們檢方也是。”萊溫斯基說她在給肯尼思·斯塔爾找一個臺階,讓他向自己道歉。但他沒有道歉,只是平靜地說:“我知道,可惜,很不幸。”

讀到這兒,我下巴都要驚掉了,他們也太有理有節了。這不是教養好、修養好、有分寸感,而是已經超越正常人的喜怒哀樂了。所以,有分寸到極致,常人的味道和溫度就會少很多。就像某國,幾年前經歷了海嘯,我看電視上每一個接受采訪的災民都隱忍、平靜,沒有一個人哭天搶地,那份克制,令我不知該肅然起敬還是渾身發冷。
分寸感,源于人們的邊界意識。我們在自己家中,總是感到無比自在、隨意,因為我們會假設沒有人不經許可隨意地沖進來。那扇房門,那道圍墻,院子四周的籬笆、柵欄,讓我們在各自的私人空間里有著最大的安全感。那道看得見、看不見的邊界線,就是我們對待他人,并且希望獲得相同對待的叫“分寸感”的東西。
所以,當半生不熟,甚至根本不認識的人當著我的面打著關心的旗號說“你太瘦了”;當女朋友把我跟她說的秘密轉述給別人;當飯桌上本來無傷大雅、賓主盡歡的閑聊扯到某個我認識或者采訪過的明星身上,并且話鋒迅速轉向八卦緋聞的時候;當聽到一個人有意無意地說出讓他人難堪的話語的時候……我的邊界,就被碰觸了。
我一直在嘗試,希望自己的邊界和四周的邊界盡可能同步,否則,我將永遠封閉在自己狹小的世界里。可是,擴大邊界,意味著也許我要降低自己的分寸感,這段過程并不愉悅,甚至有些痛苦。所以,在自己和世界的分寸感之間,永遠尋找最大公約數,是我們既保持體面、尊嚴,又能維系人情的唯一方法。